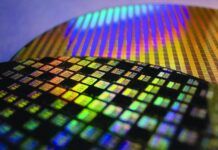關琥睜開眼睛,臥室很暗,厚重的窗簾隔斷了光線的透入,一瞬間他還以為是晚上,直到活動身體,身上傳來的痠痛提醒了他,這才想起昨晚發生的事….頭隱隱作痛,不是宿醉後的悶痛,而是另一種奇怪的感覺,他試探性地往旁邊探探手,張燕鐸不在,床上只有他一個人,他鬆了口氣,蜷起身,把自己埋進枕頭里。
酒果然不是什麼好東西,你看,如果他不是喝酒,還喝那麼多,就不會做……那種事平時想都不敢想的,他很清楚他跟張燕鐸的關係就差那層窗戶紙,一旦桶破,就再也回不了頭了。
就像現在這樣。
電子鐘發出滴答滴答的輕響,擾得人心煩意亂,不疾不徐的聲音像是在告訴他——他得面對現實,不管是對的還是錯的。關琥坐起來,身體的不適更增添了煩躁感,他的鬱悶達到了頂峰,順手抄起枕頭,泄憤似的丟了出去。
枕頭撞到了對面的小擺設,掉在地上發出響聲,聲音不大,但聽在關琥耳朵里,卻無異於炸雷,煩躁感被擔心占據了,他僵在那里一動不動,側耳傾聽房間外的動靜。
張燕鐸應該在外面,這是兄弟搭檔這麼久形成的瞭解,關琥坐在黑暗中,心驚膽顫地想如果他過來,會對自己說什麼、自己又該怎麼響應?是對昨晚的事一笑置之,還是趁此機會直接跟他劃清界限?
想了又想,關琥都沒想到合適的答案,回過神,他發現張燕鐸沒有過來,不由得鬆了口氣,在黑暗中呆坐了一會兒,探身把窗簾拉開,又隨便找了衣服穿好,走到門前,猶豫再猶豫,最後一咬牙打開了房門。
廚房那邊傳來響聲,張燕鐸在做飯,自從住到一起後,家里的三餐就都由他包了,以往關琥沒覺得怎樣,現在他深深體會到了吃人的嘴
軟這句話的含義。
他放輕腳步去了洗手間,洗漱的過程中一直在考慮是直接離開還是先去打個招呼,他很鄙夷這麼無能的自己,想到就算躲過初一也躲不過十五,他伸手狠狠拍打自己的臉,將想要溝通的話在腦子里過了一遍,又深吸了一口氣,硬著頭皮走到廚房。
張燕鐸背對著他在料理台前忙碌,他穿著白襯衫,圍裙扎在腰間,這讓他的腰看起來很纖細,他食量不小,體型卻很
削瘦,關琥無法想像他體內怎麼會蘊藏著那麼強大的爆發
力,張燕鐸沒有回頭,這讓關琥心里不舒服,以張燕鐸的耳力,他不信他會不知道自己過來了,他是故意的,不動聲色地逼迫自己主動開口。
但他不知道該說什麼,只好用咳嗽來代替,張燕鐸手上的
動作微微一頓,接著轉過身,問:「起來了?」
跟平時一樣,張燕鐸的臉上掛著微笑,頭髮打了髮蠟,無框眼鏡半掛在鼻樑上,襯衫最上面的兩個扣子沒系,整體看起來既清憤又性咸,這種類型的男人一直都受歡迎,端看酒吧的常客就知道了,她們都是衝著張燕鐸來的,喝酒還是其次。
所以張燕鐸是不缺女人的,可是他卻偏偏把心思打到自己弟弟身上,真是豈有此理,兔子還不吃窩邊草呢……
關琥胡思亂想著,就見張燕鐸將切好的火腿擺到盤子里,端上桌,說:「我做了早餐,想說你今天休息,難得的睡個懶覺,就沒叫你。」「喔……
關琥的目光掠過餐桌,麵包、煎蛋、洋蔥湯還有各類小碟配菜都擺到了桌上,豐盛得讓人懷疑這是晚餐,張燕鐸把他的椅子拉開,示意他就坐,說:「西式早點,你最喜歡的。」對於飲食,關琥沒有特別的需求,只要是好吃的他都來者不拒,看看眼前精緻的早餐,他差點就要點頭就坐了,但是想起昨晚的事,食慾就一秒消失了。
張燕鐸這樣做很明顯是在討好他,像是在說——弟弟不好意思,昨晚我把你吃掉了,作為補償,今天請你吃好吃的。用這麼顯而易見的小動作來溝通,當真是把他當低智商動物看了!
這麼一想,他就越發覺得不舒服,再看到張燕鐸那雲淡風輕的神態,他大腦一熱,脫口而出。
「昨晚……
張燕鐸臉上的微笑斂起,看過來,兩人目光相接,關琥首先看到了他嘴角上的瘀青,原本有一大堆話要說,臨時卻像是斷了弦,一句都想不起來,他的臉頰有些熱,不敢直視張燕鐸,飛快地把目光閃開了。
「昨晚……我們都喝多了。」
張燕鐸的聲音很溫柔,關琥琢磨不透他的想法,忍不住又看向他。張燕鐸摘下眼鏡,揉著眉心,說:「我要跟你道歉,這是我的問題,雖然喝了很多,但我…..
關琥的心猛地揪起來,再次看看他嘴角的瘀青,生怕舊事重提,他搶先反問:「昨晚發生過什麼嗎?」
張燕鐸的表情驚訝,關琥的眼神忽閃了一下,故作輕鬆地說:「你是要道歉,明知我酒量不好還灌我那麼多酒。」手機很合時宜地響起來,關琥掏出來看了看,臉色變得嚴肅,說:「局里有命案,我要先過去,早飯……你慢慢吃。」
他往前走了兩步,又轉回頭,追加,「快到年底了,事情很多,不知道忙到什麼時候,晚上你也別等我了…..謝謝你的早餐。」他生怕被張燕鐸叫住,說完後就快步跑了出去,張燕鐸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門後,視線轉向餐桌,無奈地笑了。
聽說警察都不善於撒謊,這句話用在關琥身上再合適不過了,弟弟白做了警察這麼多年,連撒謊的基本技巧都沒掌!握,真是個耿直boy啊。「看你能躲我多久。」他摸摸唇角,輕聲嘆道。
電梯剛巧停在關琥住的樓層,他一口氣衝進去,又迅速按關門鍵跟樓層鍵,直到看著電梯門關上,張燕鐸並沒有跟過來,他才鬆了口氣。慶幸過後,取而代之的是懊惱,關琥很想捶自己的腦袋,為什麼他的大腦總是不聽使喚,每次關鍵時刻都當機…..喔
不,是當逃兵。
—-你是不是傻?你不是要質問他嗎?不是要把一切都說明白嗎?你搞個鈴聲找藉口把自己弄走這算是怎麼一回事?
逃走能解決問題嗎?那只會把問題搞得更複雜,局里又不可能天天都有命案,讓他可以找藉口避開張燕鐸。
而且為什麼是他躲避張燕鐸?這明明就是兩個人的問題,昨晚……想起昨晚,關琥有點頭暈,畫面在腦海里一幕幕閃過,他向後一靠,仰頭看著亮得幾乎可以當鏡子照的電梯壁,心煩意亂..
重案組的同事們對關琥在休息日出現都表現得很驚奇,在他想找措辭解釋自己的行為之前,江開先開了口。
「你不是說好不容易才申請到長假,要跟老闆去山里野炊
釣魚嗎?還說訊號不好,讓我們不要打電話煩你。」他原本的確是那樣打算的,這不馬上就到聖誕節了,他跟
張燕鐸都計畫好了去山里過聖誕,享受幾天遠離塵囂的日子,誰想到計畫不如變化快,所以就…..「我哥突然有事去不了了,我一個人去也沒意
思,反正閒著也是閒著,就過來看看。」
「你哥去不了,你可以叫女朋友去啊……屋,抱歉,兄弟,我忘了你是單身狗。」
「廢話這麼多,趕緊去做事。」
關琥抄起活頁夾把江開拍走了,老馬跟蔣玎璫笑嘻嘻地看過來,他沒好氣地說:「剛出了命案,你們怎麼一點緊張勁兒都沒有?還沒查到新線索?」
「不是沒緊張勁,而是這次的案子比較複雜,又涉及到在校生,上頭叮囑我們要小心處理,免得那些新聞記者又到處說事。」
蔣玎璫走過來,把文件夾遞給關琥,說:「緝毒科的同事抓到了幾個嫌疑犯,還在那兒問呢,不過到現在都沒有問出個結果,我負責的那個孩子今天會來認嫌疑犯,希望有收穫。」
命案發生在三天前的晚上,被害人叫王槐山,是位鐵嘴律師,一同遇害的還有王槐山的妻子,他們的兒子王煜因回家較晚,儌倖逃脫。
王槐山負責刑事案多年,在這行有一定的名望,也得罪了不少人。前段時間某黑道組織涉及販毒案,委託他辯護,被他一口拒絕,那些人被定罪後,曾傳話說要給王槐山好看,所以這次的案子才會由重案組跟緝毒科合作連手調查,蔣玎璫說的孩子就是王煜,他是王家唯一的倖存者,也是見過兇手的人。
關琥把文件接了過來,說:「這個案子轉給我,我來跟。」
「呃。」蔣玎璫很驚訝,左右看看,關琥問:「有問題?」
「有,關琥你是不是發燒了?平時查案沒見你這麼積極。」
「讓妳休息妳還這麼多話,在辦公室處理文書作業不好嗎?」
關琥拿著文件夾走出去,蔣玎璫跟上,說:「你想辦也隨你,不過我要提醒下,王煜不是很配合,你跟他詢問時注意口氣。」
「怎麼個不配合法?」
「他剛上大一,這個年紀的孩子還能有什麼問題?不就是衝動、叛逆加矛盾的心態嗎?再加上他家里發生慘劇,精神不穩定也是可以理解的,已經有人安排他去看心理醫生了,免得心里的鬱悶抒解不開,精神狀況會更糟糕,希望他聽話。」
「我記住了。」
關琥說完就要走,蔣玎璫又叫住他,他以為還有什麼需要注意的,誰知蔣玎璫靠近他,壓低聲音笑著說:「關琥你老實交代,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
「瞎說什麼呢!」
「請不要小看女人的直覺,」蔣玎璫指指自己右邊的脖頸,提醒道:「這里。」
關琥轉過頭,透過玻璃窗,他看到頸下一塊很大的紅斑,驚嚇之餘,他啊的叫出了聲。「這麼明顯,也只有江開那笨蛋看不到了,真不夠意思,
什麼時候交的女朋友也不說,其實你是要跟女朋友上山過聖誕吧?」
生怕越描越黑,關琥乾脆把蔣玎璫趕走了,在去緝毒科的路上,他趁著沒人又看了一遍脖子跟手臂,居然發現了不少類似的紅斑,難怪剛才進警局這一路上一直被同事盯著看,原來大家都注意到了。其實同事們未必是注意到他身上的紅斑,就算是注意到了
大概也沒往深處想,但關琥作賊心虛,他越想越覺得尷尬,把襯衫袖子擼到底,再把衣領豎起來,等都整理完畢後他才留意到一件事——
靠,這件襯衫好像是張燕鐸買給他的!
緝毒科那邊已經斷定是販毒組織對王槐山下的手,所以他們把調查重點都放在這上面,這幾天陸續抓了不少嫌疑人,但最後都被王煜否定了。
關琥過去的時候,他們正在請王煜確認新抓到的幾個嫌疑人。關琥沒打擾他們,站在旁邊觀察。嫌疑人都戴著口罩,他們的共同特徵是長得很高大,ji精神狀態不好,目光無神,頭髮粗糙,看他們的神態就知道是長期吸毒者,這種人如果毒癮犯了,是會為了吸上一口毒粉不惜殺人的,販毒組織利用他們殺王律師夫婦的可能性很大。但是關琥看了審問記錄,幾個嫌疑對象都否定了他們曾買兇殺人,他們說的確是想給王槐山一點顏色看看,但最近被警察看得緊,沒精力理睬其他的事,結果他們還沒動手呢,
王槐山已經遇害了。關琥覺得黑道的人的話不能相信,不過從調查的情報來分析,他們的確不具備足夠的作案動機,最關鍵的一個地方是兇器手槍沒找到,沒有兇器,沒有行兇者的詳細情報,這給調查帶來了很多困難。
關琥看向少年,王煜比同齡人矮一些,身體還沒完全長開,看起來很瘦弱,他的精神狀況也不佳,科長讓他仔細看那些嫌疑犯,他眼神飄忽,看了一圈沒找到,又重新看了一圈,最後沖科長搖搖頭。科長一聽就急了,皺眉問:「你確定沒有嗎?這些人的外
形特徵跟你描述的很像,而且在案發前幾天,還有人在你家附近轉悠過。」
「是哪個?」科長看看玻璃窗對面,摸摸下巴沒說話,少年把目光收回來了,低聲說:「當時院子很黑,兇手又戴了口罩,我只看到他的眼睛跟個頭,還有手背上的刺青…..也也許不是刺青,是血跡,我當時很害怕,有可能看花了眼…..關琥看向那些嫌疑人,他們手臂上紋著各種刺青,有的一
直延伸到手背,紋絡各有不同,看來是王煜無法提供到更多的線索,緝毒科的科長急於破案,就把有嫌疑的人都一股腦抓回來審問了。
等王煜出去後,科長沖關琥一攤手,苦笑道:「又竹籃打水了。」
「至少抓了幾條小魚。」
「這些魚還不夠塞牙縫的,我想捉到海龍王。」
科長一拳頭砸在桌上,恨恨地說:「如果抓到兇手,說不定還能順藤摸瓜,抓住那幾個販毒首犯,打壓他們的氣焰,可這幫人太狡猾了,一點痕跡都沒留下。」
「你說的在王槐山家附近轉悠的人是哪個?說不定可以從他身上下手。」
「根本沒有那個人,我是隨口說的,本來想刺激下王煜的記憶,看能不能問出什麼,現在看來他是真的記不起來了,這也難怪,半大孩子遇到這種事早就嚇暈了,他至少還能報警,還能在事後配合協助我們,已經很不錯了。」
「我聽玎璫說他的精神狀態不太穩定。」
「是啊,這是最糟糕的地方,問多了他就煩躁,不問他更煩躁,說我們沒用心調查,不過這也可以理解,我那兩個上高中的兒子都跟他一個德行,這個歲數的孩子最難搞了,更何況他還是養子。」
「養子?」
關琥翻開文件夾,找了半天,才在一個不起眼的地方找到相關記錄。
原來王煜幼年父母因車禍過世,他一直住在福利機構,六歲的時候被王槐山夫婦領養,到現在已經有十幾年了。因為這部分跟兇案沒有直接關係,所以數據記錄不多。
科長在旁邊嘆氣說:「從一無所有到衣食無憂再到可能會失去一切的局面,他心里肯定很恐懼,我聽他的律師說他已經在看心理醫生了,我們本來還想通過他的醫生瞭解情況,但那醫生特別難說話,很變態的四眼雞,從頭到尾就是一副反正你們智商低,說了你們也不會懂的態度!」
「太差勁了,你沒懟他?」
「惹不了,他說的都是專業用語,還真的是聽不懂,他奶奶的,總之他說來說去,就是要保護病人的隱私,不能透露任何細節,還反過來責怪我們說病人的精神會極度緊張,都是因為我們逼得太緊造成的,我們逼得緊還不是想早點破案,王煜自己也是這樣想的吧。」
眼看著科長還要喋喋不休地抱怨下去,關琥及時打斷了,問:「這個案子會不會跟黑道組織沒關係?而是王律師的其他對頭在報復,畢竟他做這行的樹敵不少。」
「我們也想過這個可能性,但該查的都查了,暫時沒鎖定嫌疑人,兇器雖然是私槍,但也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弄到手的,而我們的名單里也找不到這樣的人。」
直覺告訴關琥,那個少年還有事情沒有講出來,不知是出於恐懼還是其他什麼因素,他說:「我去問問看。」
「祝你順利。」
「我會順利的。」
畢竟他跟少年的歲數沒有相差很大,同齡人還是好溝通的吧。
關琥一路跑出警局,王煜跟隨律師走到一輛車前,正要上車,他開口叫住了。王煜轉過頭,還沒等他開口,律師搶先走過去,攔住關琥,問:「什麼事,請跟我說。」
關琥偏頭看向王煜,說:「我叫關琥,是重案組警察,我想跟你聊一下兇殺案。」
王煜看了他一眼,馬上把眼神瞥開了,這讓關琥更加斷定自己的猜測—-王煜有事情隱瞞,他現在的反應就跟自己與張燕鐸說話時的反應一樣。於是他堆起笑臉,儘量提高自己的親和力,問:「可以嗎?」
王煜沒說話,律師代替他說:「有關那件案子,你們已經反反覆覆問過很多遍了,他還是個孩子,遭遇這種事,需要好好休息,而你們每問一次,就是往他傷口上撒一把鹽,如果你們警察可以把這份勁頭用在調查上,相信可以更快地找到兇手。」
他說完,讓王煜上了車,關琥還想懇求,律師已經把車門關上了,他在上車之前又對關琥說:「也許你該做的事是好好翻閱調查資料,而不是撒鹽。」
關琥站在原地看著轎車開走了,他有點理解蔣玎璫跟科長說的話了。看來這個案子的難度不光是尋找兇手,還有來自受害者方面的阻力。
好,那我就先去做其他調查。
被律師一番嘲諷,關琥的擰勁兒上來了,他回到警察局,拿著所有相關數據去了審訊室,把自己關在小屋子里看資料,做好重點,下午他又去了王煜的學校打聽他的情況。
王煜讀的是本地一所有名的私立大學,關琥不需要特意調查也知道這所學校的學費有多昂貴,看學生們的打扮也都是出身富庶之家,再聽他們聊天的內容,關琥懷疑自己的智商需要充值,這複雜程度大概只有張燕鐸能聽得懂。真見鬼,這麼忙他都能想到那個人,關琥晃晃腦袋,警告
自己集中精力查案,不要想那些有的沒的。
王煜沒有特別要好的同學,不過他跟大家的關係處得都不錯,同學對他的評價是功課好,有點內向但樂於助人,如果有人問問題,他也會熱心地解答,性格也很平和,沒有跟同
學鬧過矛盾。
問了一圈,王煜的老師說了件讓關琥在意的事。
在兇案發生的一個月前,王煜缺課的次數特別多,老師曾問過他原因,他說身體不好,一直跑醫院,問他是什麼病,他說是普通的感冒發燒,很明顯是在說謊,但因為他沒耽誤
課程,老師也不方便多說什麼,只是提醒注意了一下。
「你確定他在撒謊?」
「我們做老師的就跟你們當警察的一樣,學生是不是撒謊一眼就看出來了,不過那段時間他的精神狀態是有問題,上課老走神,他以前不抽菸的,也不知道被誰帶壞了,我沒收
後、本來準備跟他父親談談,誰知就出了那件事。」
「都大學了還不讓抽菸啊。」
「那也要看是什麼煙。」
老師從抽屜里拿出一個盒子,里面放了三支自製的捲菸,關琥接過來聞了聞,表情嚴肅起來。
「這所學校的校規非常嚴格,要是鬧大了,他可能會被勒令退學的,那就太可惜了,我一直想著怎麼處理,之前一直沒跟你們同事說,是怕影響到王煜的前途,但後來越想越擔心,我又不懂煙里都加了什麼料,說不定跟他父母被殺有關,所以想了想還是跟你說了吧,你來判斷怎麼處理。」
「謝謝。」關琥理解老師的心情,他道了謝,把煙盒收好,離開時,問:「王煜還沒有來上課?」
「沒有,打電話他也不接,你要是看到他,就勸勸他,別老跟一些不良青年來往,很容易學壞的。」
「什麼不良青年?」
「有一次有個穿龐克裝的男人來找他,我們學校是禁止那種不良社會青年進出的,我問過他,他不承認,說是我看錯人了。」
老師說完嘆了口氣,一副恨鐵不成鋼的表情,關琥理解他的心情,說:「放心吧,我會提醒他的。」關琥從學校出來,去了王煜的家。但他連門都沒得進去,按了好幾次門鈴,里面一直沒響應,他還以為家里沒人,聯絡上在附近負責暗中保護的同事後,才知道王煜在家。自從家里出了事,王煜除了去警察局配合調查跟看心理醫生外從不出門,大概是親眼看到血案現場,受到了驚訝,同事勸關琥不要緊追猛打,免得刺激到他,結果適得其反。看看時問不早了,關琥只好先返回警局。
他剛進辦公室,江開就迎面走過來,說:「你哥…..
關琥現在就像是驚弓之鳥,本能地左右看,問:「我哥來了?」
「沒有,我是說都這麼晚了,你哥怎麼還沒送飯來啊?」以往只要有案子,張燕鐸都會送飯過來慰勞大家,這都養成習慣了,今天他沒來,江開一臉的不可思議。
關琥沒好氣地把他推開,揚了揚手里的便利店袋子,說:「今天沒有,自己買去。」
他走去自己的座位,江開亦步亦趨地跟過來,問:「看你臉色不太好啊,是不是遇到什麼麻煩了?說出來,哥哥幫你處理。」
「別跟我提哥。」
現在一提到哥這個字他就胃痛,他絕對不會說這是因為一整天沒吃飯導致的。
江開看看他的臉色,點點頭,說:「跟你哥吵架了,跑不了。」
「你又知道。」
「那還用說,要是沒鬧彆扭,這個時間段他早送飯過來了,而且是全組都有份,你肯定是做了什麼沒腦子的事惹他生氣了,趕緊去賠禮道歉,兄弟沒有隔夜仇,你們和好了,我們才有美食吃。」
真沒出息,說來說去只為了一頓飯。
關琥衝他擺擺手,意思讓他趕緊消失,江開卻當看不見,還在旁邊嘰嘰歪歪地說,關琥忍不住了,拿起活頁夾就要拍他,就在這時,手機響了起來。他拿起來一看,果不其然,是張燕鐸的來電,他把手機放到桌上,辦公室其他三個人的目光也都落在手機上,老馬問:「不接?」
「喔,打錯電話了。」
「打錯了你也接下,跟人家說一聲嘛。」
「沒事,反正馬上就停了。」
關琥說完,手機鈴剛好停下,但他還沒來得及鬆口氣,鈴聲馬上又響了起來。
大家的目光還都緊盯著手機呢,關琥沒辦法再裝死了,他拿起手機想丟進抽屜,冷不防被江開搶過去接聽了。
「大哥好,我是江開啊,你什麼時候過來,我們都等著開飯呢……關琥?關琥在啊,你等等。」
手機塞到了關琥手里,他現在的心情簡直恨不得拿鞋底把江開拍死,拿著手機匆匆去了角落里,小聲說:「什麼
事?」
「飯做好了。我想送過去,你還在忙嗎?」
張燕鐸的語調跟平時一樣溫柔又平靜,像是什麼事都沒發生似的,單聽他說話,關琥幾乎懷疑自己昨晚的經歷是不是記錯了,有心拒絕,又覺得那太明顯了,可現在他又很怕跟
張燕鐸見面,猶豫了一下,說:「還好……
「那我馬上過去,你等我。」
「不用了,我已經買飯了…….
關琥的話還沒說完,手機已經掛斷了,他呆了三秒鐘,拿起桌上的塑料袋就想往外跑,但腿還沒邁出去,辦公室的門就被推開了,張燕鐸從外面走進來,手里還提了兩個大袋
子。隨著他的走近,披薩餅的香氣瀰漫了空間,江開跟蔣玎璫很狗腿地跑過去接下來,老馬跟在後面,說:「你看每次都吃你送的飯,太不好意思了,多少錢,我們付。」
「談錢多見外啊,這都是自家烤的,沒多少錢,而且不含任何色素跟添加劑,可放心食用。」
張燕鐸把塑料袋給了他們,轉頭看向關琥,關琥拿著塑料袋低聲說了句買飲料就跑了出去。
他一口氣跑到休息區,掏出零錢塞進自動販賣機,正猶豫著選哪個好,旁邊伸過一隻手按在了橙汁上。咣噹噹,飲料罐掉了下來,張燕鐸彎腰撿起,遞給他,說:「在選擇的時候過多猶豫的話,機會很可能就在你眼前
溜走了。」
關琥看過去,張燕鐸眼鏡片後的目光犀利,像是意有所指,他默默地把飲料接過來,坐到旁邊的桌上。張燕鐸陪著他一起坐下,將手里的盤子遞給他,里面放著兩大片披薩,說:「辦公室里一群狼,不先拿給你,回頭連
渣都不剩。」
「我買飯了。」
雞肉飯,我正好想吃。」張燕鐸把關琥放在椅子上的袋子打開,拿出里面的便當,袋子里有勺子,他打開盒蓋,開始吃起來。張燕鐸很少吃外賣,他總說外面賣的不如家里的好吃,所
以關琥想他現在這樣做是故意的,他總是把認為是最好的東西給自己,也不管自己是否需要。但是猶豫過後,他還是起身買了瓶礦泉水,放到張燕鐸身旁,張燕鐸抬頭看他,先是有些詫異,隨即便
笑了,說了聲謝
關琥沒回應,低頭默默地啃披薩。以前張燕鐸不會對他這麼客氣的,他從來都是把他這個弟弟當傭工來使喚,但昨晚之後一切都變了,不單單是兩人的關係,還有他們之間的某種默契。兩人並肩而坐,各自低頭吃飯,誰都不說話,關琥感覺很彆扭,跟張燕鐸在一起會讓他感到尷尬的這還是頭一次,他們靠得很近,他可以清楚聞到對方身上散發出的荷爾蒙氣
息,其中還混合了古龍水的清香,他不討厭,反而覺得那香氣很適合張燕鐸。
像是感覺出了他的走神,張燕鐸先開了口。「聽說這次的案子挺棘手的。」
「還好。」張燕鐸出現得太突然,關琥把原來打算跟他溝通的說辭又忘到了九霄雲外,他現在滿腦子里都是案子,匆匆把披薩吃完,站起身準備走人,張燕鐸叫住了他。
「你在外面跑了一整天,查到什麼沒有?」
「對不起,有關案子的內容我不能透露。」
關琥乾巴巴地說完,就見張燕鐸臉上堆起了笑容,他笑得很詭異,關琥猜想他心里應該在說——小樣兒,還敢跟我鬧這
種虛的,你根本就是不想說對不對?
所以他沒給張燕鐸響應的機會,又追加一句-—「我今晚可能要做到很晚,不用等我了。」
「那正巧了,我也要開店到很晚。」
張燕鐸站起身來,笑咪咪地說,關琥點點頭,掉頭就走一—
一直被這樣盯著,他很不舒服,彷彿魚在俎上待宰,他巴不得趕緊離開,至少逃出張燕鐸的視線範圍。他沒走出兩步就又被叫住了,張燕鐸在後面叮囑道:「關琥,這案子不是你們組負責的,別太拼了,你要是一天到晚
都這麼拼,就算交到女朋友也不會長久的。」
終於忍不住了,關琥轉過頭,大聲叫道:「有你在,我要是能交到女朋友那才叫奇怪!」
兩名同事從旁邊經過,驚訝地看他們,關琥覺察到失態,慌忙低下頭迅速逃離尷尬之地。張燕鐸託了托眼鏡框,笑著注視關琥跑遠了,他就喜歡逗弄弟弟,再欣賞他驚慌失措的模樣,比如今早,比如現在。要知道把鐵血刑警調教得跟小白兔似的,也不是件容易事啊。
昨晚的事算是突發事件,事情走向出乎他的意料,所以他其實現在心里也沒底,就比如他以為要完整的圈養小白兔需要很久的時間,卻沒想到三步投籃就這麼輕鬆地進了…..
原本今早關琥醒來會撕了他,現在看來狀況比他預想的要好很多,只是今後該怎麼處理他們的關係,他要好好斟酌才行,不要一手好牌最後卻打爛了。
關琥在警察局熬了一晚上,把案子的相關數據都看完了,做完記錄後,他又跑去值班室睡到天亮,中途還心驚膽顫地想要是張燕鐸打電話過來,他該怎麼應付,但直到他快睡著了,張燕鐸的電話也沒進來。
這很稀奇,以往他出任務或是留宿警察局,張燕鐸的電話都特別多,各種查崗,他今天會這麼安靜,肯定也是因為昨晚的事。現在回想起來,早上看到張燕鐸第一眼時,他就該一拳頭
打過去,可是悲劇的是首先他打不過張燕鐸,其次就是就算
打得過也改變不了已經發生了的事實,反而氣急敗壞的反應會更讓他顯得像是悲劇人物……
所以他只能表現得雲淡風輕,表現出那都是成年人的遊戲,——
這一覺睡得很不踏實,關琥閉上眼沒多久,就咸覺回到了那天晚上,他在張燕鐸的酒吧喝酒,那晚酒吧的人出奇的多,而且都是女性,有兩個常客還一直圍著張燕鐸說話,那虎視耽耽的模樣傻子都能猜出她們心里在打什麼算盤。所以關琥很不高興,因為那些礙事的人,他幾乎沒機會跟張燕鐸搭話,幾次過去提醒說明天還要早起去露營,不要玩太晚,張燕鐸都是嗯嗯嗯的敷衍他,最後還嫌他煩,讓他先回家,他一賭氣就先走了。
誰知他前腳到家剛坐下,張燕鐸後腳就回來了,說酒吧交給店員看著,他回來陪弟弟。
他當時心里正不高興著,藉著醉酒,嚷道:「你去陪你的環肥燕瘦唄,露營我一個人去。」
張燕鐸倒了杯水遞給他,笑道:「你吃醋啊?」
「開玩笑?我為什麼要吃你的醋?」
他最多是心里不太舒服而已。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很在意圍繞在張燕鐸身邊的那些鶯鶯燕燕,那些女人都是有目的的,要知道張燕鐸長得帥又有錢,而且對女性又很有禮貌,所以倒追他的人特別多。
但關琥覺得這些女人都不適合做張燕鐸的伴侶,沒有為什麼,就是覺得他們站在一起不般配,每次張燕鐸被邀請出去玩都會叫著他,他每次都覺得充當電燈泡很尷尬,但每次又拒絕不了。
因為他好奇張燕鐸會不會真的跟對方交往,交往的話會不會結婚。
他很不想面對這個問題,那會讓他感覺自己的親人被奪走了,他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覺得自己很變態,作為兄弟,他原本該希望哥哥在經歷了各種磨難後有個好的歸宿一—理智這樣教導他,但感情上他做不到。
所以這段時間他很爆躁,經常動不動就發脾氣,張燕鐸也不在意,笑他是不是到了更年期,他當然不是,他只是發現自己對張燕鐸抱有一些特殊的感情。
是那種想把最好的東西占為己有不願跟任何人分享的感情。他藉著張燕鐸的手把水喝了,接著繼續靠著沙發不說話,
張燕鐸在他旁邊坐下來,問:「關琥,問你個問題。」
「什麼??」
「如果要選擇結婚對象的話,你說哪種比較好?」
很震驚,坐起來,問:「你要結婚?是哪一個?」
「就是決定不了才讓你選,你覺得今晚在酒吧的那些,哪個最好?」
「我……他恍惚了一下,搖頭說:「我不知道,都很好
「那男性呢?也有男性跟我告白,我不在意同性問題,反而覺得同性更好,你也知道女人有時候很麻煩,對了,那個陳老闆你還記得嗎?他一直跟我表示好感,不過他太有錢
了,讓人感覺不踏實。」
關琥記得那個人,一個IT公司的老闆,他有一次遇到了搶劫,剛好他們兄弟路過,他就出手解決了,但過後陳老闆跟他們道謝的時候,眼神一直放在張燕鐸身上,還拉著張燕鐸
的手不放,直說要請客答謝才行,那眼神讓他當時就覺得不舒服。
所以聽說陳老闆追求張燕鐸,他一點都不奇怪,而且陳老闆有點見識,能說會道的,他們聚過幾次,他知道陳老闆跟張燕鐸挺聊得來的。這樣一想,他就更覺得不舒服,站起來走去吧檯隨便找了瓶酒,倒進酒杯,咕嘟咕嘟喝下肚,酸溜溜地說:「有錢還不好?難道你還想找沒錢的?」
「可是我自已就很有錢了,所以錢對我來說不是很重要,我還是想找有感覺的。」
關琥的第二杯酒也喝光了,喝得太急,他的腦子開始暈乎,恍惚著問:「那你覺得誰對你的口味?」
張燕鐸好像說了什麼,他沒聽清,越想越覺得心煩,索性拿起酒瓶直接往里灌。
他灌了好幾口,又氣沖沖地回到沙發上,質問:「你為什麼老跟我說這種事?炫耀嗎?你明知道以你的條件,公主都從娶到手,你在個單身狗面前說這些有意思嗎?」
「關琥你醉了。」
「我沒醉!我最討厭你們這種人,有錢的挨命說自己窮,瘦子整天說自己需要減肥,明明可以在感情上遊刃有餘,卻偏偏說自己沒自信,你說你沒自信張燕鐸,你讓地球百分之九十九的男人還怎麼活!?」
「我是沒自信啊,我沒自信可以忍住不揍你。」
帶著挑釁的散漫語調成功地挑起了關琥的怒火,他腦子一熱,撲過去揪住張燕鐸的衣領,想給他點顏色看看,他討厭張燕鐸這種不把一切放在心上的態度,在他認真說一件事的時候,有必要這麼戲弄他嗎!?
那一拳最後有沒有打過去,他竟然記不得了,但張燕鐸嘴角有瘀青,那大概是他出手了吧,都怪他喝得太多了,導致後面的記憶混亂,
關琥洗完澡,去食堂吃了早飯,把一切都搞定後,大家才陸續到齊,重案組最近沒有大案子,江開他們還是負責配合緝毒科的同事調查王家血案,他們化妝成道上的小混混,去一些有嫌疑的犯罪組織里打聽情報。負責調查王煜的工作就交給了關琥。
關琥把老師給他的加料香菸給了緝毒科的科長,檢驗後發現菸絲里混合了大麻,而且成分很雜,短期少量的服用,身體不會馬上出現不良反應,所以很多人都抱著從眾的心態去吸食。
科長說現在很多大學生都喜歡吸這些東西,美其名日是為了提神做功課,其實就是一種心理依賴,結果是惡性循環,精神狀態越來越糟糕,等發現戒不掉的時候已經太遲了,他們抓了很多私下販賣的小店,但還是屢禁不止,最終原因還是因為有市場,有人買才會有人賣。
「既然這條線索是你發現的,那就由你去查吧,不過小心點別太刺激王煜,他的律師是他父親的好友,又龜毛又護短,一個弄不好,又來投訴你侵犯人權。」
「放心吧,我知道該怎麼做。」
關琥出發時已經想到了對策,既然王煜抗拒直接溝通,那他可以去拜訪一下那位心理醫生,看看能不能在他身上找到突破口。科長說那位心理醫生很變態,關琥沒放在心上,他身邊就
隱藏著一隻大惡魔–論變態,在張燕鐸面前,誰敢出其右?
為了順利跟蹤到王煜,關琥早早就去了王家,他先試探性地敲門拜訪,不出所料,出來開門的是家傭,對他說王煜身體不舒服,無法招待客人,說完不等關琥響應,就直接把門關上了。
老實說幹警察這麼多年,他什麼樣的人沒見過,但這還是頭一次被個毛頭小子請吃閉門羹,關琥聳聳肩,放棄去糾結,老老實實回到自己的車里,心想比韌勁,誰怕誰,我就在這兒耗上了,我就不信你能一天都不出門!
王煜出門要比預料中早得多,關琥在車里待了還沒有一個小時,就見王家的門開了,王煜從里面出來,很快,一輛計程車開到了門前,他坐上車走遠了。關琥敵動車輛,在計程車後面不近不遠地跟著,一路跟到了商業樓區,計程車在一楝大廈前停下,關琥看著王煜走進大廈,他找了個地方停好車,也跟了進去。
大廈門口列著各樓層的公司名稱,他上下看了一遍,最後目光落在十樓上。
Dream心理諮詢中心。
跟調查資料里的名字一樣,看來受害人很相信這里的醫生,對外界跟警察那麼抗拒,卻主動來跟醫生溝通,難怪科長對無法從醫生這兒拿到情報耿耿於懷了,王煜跟醫生說的事情一定有助於他們追查兇手。所以接下來的任務就是看他要如何運用手段,從醫生口中問到情報了。
關琥搓搓手掌,在心里盤算著行動計畫,乘電梯來到十樓。諮詢中心的前台是個說話溫柔的小姐,當聽說關琥沒有預約,她委婉地請他先填表格再進行預約。
關琥聽她說最快也得一個星期才能約上,他沒耐心了,直接拿出自己的刑警證,遞到前台桌上,笑咪咪地說:「不知道這個通行證能不能幫我提前約到?」
看到警察證件,小姐的表情僵硬了幾秒鐘,隨即重新綻放笑臉,她把關琥請到休息區,說現在不方便打擾醫生,等病人離開後,她再進去詢問,請他在這里稍等。
休息區有免費的茶點享用,還有各種音樂選聽,連座椅都自帶按摩功能,關琥這兩天身體正痠痛呢,按摩椅剛好派上用場,他選了飲料,靠在椅子上享受按摩,再把耳機戴上聽著輕音樂,覺得這里比警察局的值班室舒服多了。
當心理醫生真好啊,上下嘴皮碰幾下,就能輕鬆賺大錢了,要是當初他也選擇這行就業,想必現在也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身邊美女層出不窮,早就沒張燕鐸什麼事了。
該死,莫名其妙的又想他了,有人說這世上最可怕的兩種感情就是依賴跟信任,關琥發現這兩條自己都占了,這真是件可怕的事,即使那個人曾經跟他搶過女朋友,還故意在他面前炫耀男性魅力,還對他……但即使有諸多不是,一遇到什麼事,他還是會忍不住地去掛記那個人。
在心里不斷地吐槽自己,關琥又習慣性地掏出手機看來電,平時接多了張燕鐸的來電,這兩天手機太安靜,他都有點不適應了。
張燕鐸沒有來電話,關琥自嘲地笑笑,把手機放回去,心里說不上什麼感覺,有點慶幸,又有點失落。想什麼呢真是,也許人家根本就沒把你放在心上,他有很多錢,你沒有,他有很多選擇,你也沒有,在發生過那種關係後,連把他們連接到一起的血緣關係都變得微妙了。
所以,拋開那層脆弱的血緣關係,他們之間還剩下什麼?
就在關琥陷人無限循環的自我厭惡時,王煜出來了,他急忙抽過旁邊的報紙遮住臉,但這個行為很多餘,王煜根本沒往他這邊看,低著頭匆匆走出去。關琥放下報紙看去,王煜抬手揉眼睛,像是在哭泣,這讓
他更加起了好奇心——到底這個心理醫生有多厲害,可以讓病人對自己推心置腹?
前台小姐走進去沒多久,出來告訴關琥說醫生答應見他,不過只有十分鐘的空閒時間,希望他不要介意。
關琥一點都不介意,先見了再說,到時候見招拆招唄,對付這種人他有經驗。
他跟著小姐走進診療室,里面很寬敞,整體白色設計,擺設不多,簡約而大氣,配合著樂曲聲,的確可以讓煩躁的心情得以紓解。
靠窗的地方擺放著沙發跟躺椅,對面是辦公桌,桌上只有一台計算機,顯得有點空,關琥想起自己的辦公桌,不由得汗顏了一下—-如果他的收納技巧有這醫生一半好的話,也不
會整天被蔣玎璫嘲笑桌子像豬圈了。
他在房間里轉了一圈,不見醫生出現,左右看看,沒找到監視鏡頭,便迅速走到計算機前想看看有什麼發現,可惜計算機鎖屏了,他看到旁邊半開的抽屜,猶豫著要不要打開看
一下,就在這時,耳旁傳來說話聲。
「在找什麼?」
「啊!」
關琥沒防備,下意識地往另一邊躲閃,男人及時伸過手來扶住了他,微笑說:「亂動別人的東西,很容易引起對方的反感,到時不管你想問什麼也問不到了。」
語調輕柔,帶著蠱惑人心的親近感,這樣的聲音很容易讓人放下戒心,然而關琥的反應卻恰恰相反,因為站在他面前的不是別人,正是張燕鐸!
大家能想像得出那種感覺嗎?一個完全意想不到的人在不可能的狀況下突然出現,讓人完全沒有防範,連反應的機會都沒有,更別說開口發問了。
看到關琥的樣子,張燕鐸噗哧笑了,笑聲像是解開催眠的
讓關琥回了神,問:「張…燕鐸?
來源:kknews絕對零度番外篇關琥張燕鐸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