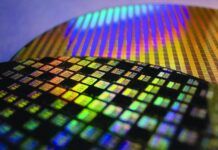(一)
「太宰治,一個喪人。」許多人始終擺脫不了這種偏見。雖然短短三十八年的人生中發生了五次付出行動的自殺,足以佐證這個觀點;《人間失格》,僅書名便充滿頹廢,被無數人視為經典;那句關於「為人」的愧疚,在網絡中處處可循。太宰治,又一次被世界捕獲,或者說,他自以為成功的出逃依舊沒能擺脫失敗的命運。
我對此很厭惡。
人在死後,便失去了辯解的機會。任人擺布、解讀。信徒們將自己與逝者勉強共鳴,哭喊著:只有他理解我。把自己一切的主張拋擲給憂愁的冥客,依賴他,就如生計依賴父母、感情依賴戀人、娛樂依賴網絡一樣,將自己與「我」隔開,為了不可視真實且普通的「我」,在「我」面前疊置無數片濾鏡。「太宰治」,是其中一片。與那些粉飾或華麗的濾鏡不同,這片濾鏡中的「我」楚楚可憐:委屈縈繞,眼泛淚光,獨自坐在高處,裝作落平陽的虎。「只有太宰治先生能理解我。」在遠處窺視「我」的自己想著,心安理得自我欺騙,再一次投身於靠依賴而活的現實。
我痛恨他們的行為,可又不得不直面頹廢。在空中有無數游離的「太宰治」,無一例外被剝奪了快樂。他們的崇拜者中,同樣有我的身影。渺小、一樣頻率的揮手,強顏歡笑。人們擁有憂郁與發泄的權利,擁有存在精神寄託的權利,卻丟失了自我改變的權利。將自己安放在世界洪流下,誤以為是個什麼了不起的人物,非要受世界影響不可。新的時尚流行,自己也必須流行;新的衝突發生,自己也必須跟進;新的八卦傳出,自己也必須窺視……與世共喜共悲,可無不在自私。對於苦難的同理心,美名曰「共情」,卻是陷於自我經歷與臆想中悲痛,一旦短暫被愛撫,他人所遭受的不公就會被拋之腦後,轉而投入下一件苦難中。什麼都沒有改變。
這或許就是我被安曇小太郎感動的第一個原因:他從未消費太宰治,相反,在那些喪氣話背後,他看見了希望,並靠此指引自己。遇到與現實相悖的語句,他會選擇質疑。透過太宰治,他僅僅注意到身邊的悲傷與附近的哭泣。通過這種關注,又讓他發現來自身邊的善良與愛。他沒有選擇融入世界。
由此,與其說小太郎因真實讓人感動,不如說是被我們理想中的真實所感動,同時也是被我們親手拋棄的真實。懷疑自我改變的價值,對世界、形勢、氛圍的無力逐漸演變成對自己的無力,轉而想去依賴某種理解——太宰治就這樣被捉住了。

(二)
我沒有那般幸福的初中生活,所以我清楚地明白,那不真實。
我的初中沒有情竇初開的場景,唯一忠誠的只有學業。在私立、衡水式教育下,情感被壓抑在黑匣子中,始終無法找到打開的缺口。學習並不是難事,只要循規蹈矩地完成作業,成績差不了。
問題是,我不會順從。一次自習後的班會上,老師忽然奚落起組員的成績,像是沖著情敵的孩子,口無遮攔地羞辱。看見他低頭默聲,忽然想起他每日最早到教室時,迎著朝陽學習的模樣。不知哪里來得勇氣,我第一次頂撞了老師。從此,我的初中便走向了另一個方向,與其說被孤立,不如說為自己的魯莽(或勇氣)付出了代價。在「不敬老師」的惡名傳開後,任何可愛的邂逅都與我無緣。沒有手機、沒有課外活動、沒有愛情,我迫不得已愛上了讀書。
這不是什麼高尚的選擇。喜歡一件事物,無非只有真心熱愛與被迫喜歡兩個理由。對人也是這樣。小太郎無疑是前者,也只有發自內心的喜歡,才不會消費太宰治,也不會對愛人放手。對於他那懵懂的思春,無關外表是否精緻,無關內在是否契合,只是「偷看她時很滿足」——相處時羞澀,在她難過時著急,聊天時快樂。怪事,在我身旁各式各樣的戀愛都有,卻唯獨沒有如此干淨的戀愛,或者說,這種在心底人們均認可、嚮往且視為正確的戀愛,從未出現過。
想起初中時的兩對戀人,一對女孩在依賴中不斷傷害男孩,一對在被發現後因家庭背景只勸退了女孩,其餘任何私藏的戀愛因懼怕校規而悄無聲息的了結。思春成為一種罪過,是必須跨過的坎,只有這樣未來才會坦盪。可從未有一種人生可被預測,沒有人敢對「未來坦盪」打包票,也沒有人敢說掉進坎內只有疼痛。在寒冷裹挾、狂風大作時,唯有在坎里的人感到溫暖。

大人們向來懼怕愛情與書的力量,因為它們傳授的都是「勇氣」。當一個人下定決心要用「勇氣」干什麼事時,就意味他不再順從。太宰治曾經說過,「人類是為了戀愛與革命而誕生的」。如果安於現狀會讓他失去愛人,那他必須打破現狀;如果按部就班會讓他失去權利,那他必須選擇反抗。只有這樣,才能將自己的心意告訴對方,才會有擁有與改變的機會。小太郎這樣做了,或許他的美滿結局僅代表一種可能,但如果不做,也不會有可能。
(三)
太宰治曾經說過:「即使知道有人喜歡自己,我也缺乏去愛別人的能力。」可他也同時也說過:「盡管在過往的人生中,我曾無數次希望有人能殺了我,但我從未想過要殺人。因為面對可怕的對手,我反而只想著要如何讓對方幸福。」
對於他來說,即便是面對心口不一的愛人,也會在無數次暗示要恨她後,希望她能得到幸福。這種畸形的溫柔伴隨他一生,或許殉情是他能想到唯一共享痛苦的辦法。
我常常想,如果在太宰治兒時遇到過像小太郎一樣的初戀,他的人生會發生怎樣的改變。女人們常常對男人的初戀情結不解,有時就連作為男人的我來說,也含糊不清。我只能說,不像父母每天施肥除草,初戀是貧瘠中第一場春雨。在彼此的世界里,都有了存在的價值。第一次從「理所當然」地愛中走出,第一次願意盡責,第一次感到悲痛。愛,也不再作為絕對的褒義詞出現,以一種現實的擬物陪伴著彼此,直到最終的結局。

在太宰治不間斷的自艾中,只有少數像小太郎一樣的人看出了他痛苦背後的祈求。男孩從中汲取力量,又溫柔地拍打著作家,為他的跌宕起伏蓋上被子,遮住脆弱的一面。你說自己缺乏愛人的能力,那我替你好好愛一個人;你說不願讓任何人受傷,那我替你做出解開心結的決定。在男孩的故事里,誰都不願留有遺憾,大膽袒露自己的愛意。一群稚子,在哭過、喪過後繼續熱愛生活,他們純粹地不可方物。稚嫩為人最後的優點。
太宰治一生不過都在寫小說式的日記罷了。
(四)
「月色真美」,很唯美的典故。

看完《月色真美》後,我下載了《殘陽》與《奔跑吧梅洛斯》兩本太宰治的小說。慚愧,我並沒有看完《人間失格》,唯一讀過的是《女生徒》。我不是太宰治任何形式的崇拜者,甚至一段時間對他的自暴自棄而感到厭煩。或許正如他所說:「我裝出一副早熟的樣子,人們就謠傳我早熟。我假裝懶漢的模樣,人們就謠傳我是懶漢。我裝作不會寫小說,人們就謠傳我不會寫小說。我假裝愛撒謊,人們就謠傳我是說謊的人。我假裝有錢的樣子,人們就謠傳我是富翁。我假裝冷漠,人們就謠傳我是個冷漠的傢伙。可是當我真的痛苦呻吟時,人們卻指責我無病呻吟。」可我免不了想去證明太宰治也是個充滿希望的傢伙。
在凌晨五點的宿舍抱著棉被痛哭後,我模模糊糊地度過了一個上午。下了網課,爬上床繼續半夢半醒,不知多久,舍友忽然叫我的名字,把我驚醒,看著被我踢皺的床褥與亂掉的衣物,寫下了這樣一段小記:
by 佐也.
來源:機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