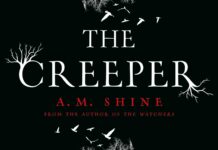趙稀方學術答問錄
趙稀方《趙稀方學術答問錄》,《學術評論》2019年第2期

作者簡介
趙教授是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現代文學研究室主任,「20世紀海內外中文文學」重點學科負責人,中國比較文學翻譯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學術工作委員會主任,論著有《小說香港》《後殖民理論》《歷史與理論》《翻譯與新時期話語實踐》《翻譯現代性》《翻譯與現代中國》《二十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新時期卷)等,為劍橋大學、哈佛大學訪問學人,台灣成功大學、東華大學、波蘭羅茲大學等校客座教授,曾應邀在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波蘭等地高校和研究機構進行學術演講。
2018年10月19日上午,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珠江人文講壇」系列報告第四十二講:跨界創意文化系列講座之五在文一棟五樓講學廳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趙稀方先生以「後殖民主義與當代西方理論」為題,為文學院師生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學術報告。
此次活動由文學院凌逾教授主持,外地遠道而來的學者有龍其林教授、劉秀麗主任、陸傑副教授、陳慶妃副教授、湯俏博士等,本校的申雲同博士、徐詩穎博士後以及現當代文學專業、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專業的研究生、本科生參加了此次活動。
學生:我是華師比較文學的研究生。前段時間我看到有一個批評,說傑姆遜(Fredric Jameson)有關於第三世界文學的理論本身也有東方主義之嫌,對此我沒有把握,不知道老師怎麼看這個問題?
趙稀方:傑姆遜曾在中國社科院做了一次演講,我當面和他提出了一個有關於National Allegory(民族寓言)的問題。他在《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文學》一文中有一個引起爭議的觀點是,他認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學都是一種民族寓言。傑姆遜通過對於魯迅的分析,認為西方的現代主義是個人力比多的昇華,而第三世界文學,像中國文學,只是一個民族寓言,也就是說,是民族集體性的反抗和鬥爭的結果,他的原話是:「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來好像是關於個人與力比多趨和的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關於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眾和社會受到沖擊的寓言。」這是一種東、西二分的觀點,意思是說中國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還沒有上升到西方現代主義的程度。對這個問題最有力的批評,來自於印度馬克思主義批評家阿吉茲·阿哈默德(Aijaz Ahmad),他的文章的題目叫《詹姆遜的他性修辭和「民族寓言」》。在阿吉茲·阿赫默德看來,這是一種本質主義的概括,顯然不能成立。為避免本質化的立場,詹姆遜解釋說他是在「本質上是描述的態度來使用『第三世界』這個名詞」的,這更讓後殖民理論家們感到不可思議。阿赫默德說:二元對抗必然導致本質主義,而本質主義卻又必然要推導出民族主義。大家可以直接參閱他的《詹姆遜的他性修辭和「民族寓言」》一文,這里就不多說了。

傑姆遜(Fredric Jameson)
如果說,傑姆遜1985年來中國帶來後現代主義,1989年又帶來了第三世界文化理論,這種「第三世界文化理論」給中國學界帶來了對於後殖民主義的誤導。我們的學術界非常崇拜他,沒有人敢提出質疑。
與此相關的問題,是少數話語。德勒茲寫了一篇文章,叫做《走向少數話語》,他討論卡夫卡的德語寫作,得出一個結論,少數裔的寫作跟西方是不一樣的,第一個是他的集體性,第二是他的政治性,也就是說,在被壓迫的地區出現的是反抗性的文學,而西方的文學是比較側重於個人力比多的體驗、反映個人與社會焦慮的現代文學。這里無論是傑姆遜還是德勒茲,都做了一個西方和東方的區別,東方的文學和西方的文學是不一樣的,這里面的確有東方主義的觀念。
龍其林:我覺得任何一個理論都有它的適用范圍,後殖民主義作為理解當代的一種重要方法,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視角,但是也會不會形成一種先入為主的見解?有了一種理論的視角,然後再來找來一個對應的現象來套用,所以我很想知道趙老師您是怎麼理解它的使用限度的問題的?
趙稀方:好,現在我就後殖民理論與中國的關系為例,來回答這個問題。後殖民理論——特別是進入中國以後——也受到很多批評,說中國並沒有殖民地的經歷。其實也不是完全沒有,我們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像滿洲國、香港、上海租界等都有殖民經歷。的確,從整體來說,中國沒有殖民地的經歷,所以他們覺得後殖民理論在中國是不適用的。
我特別喜歡周蕾(Rey Chow)的回應,她有一本書翻譯為《寫在家國之外》,里面專門有一段論述這個問題。在她看來,後殖民理論的獨特之處,恰恰在於揭示了沒有經歷過殖民主義統治的國家和地區,也仍然在文化上受到了西方主導和操控,它滲透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價值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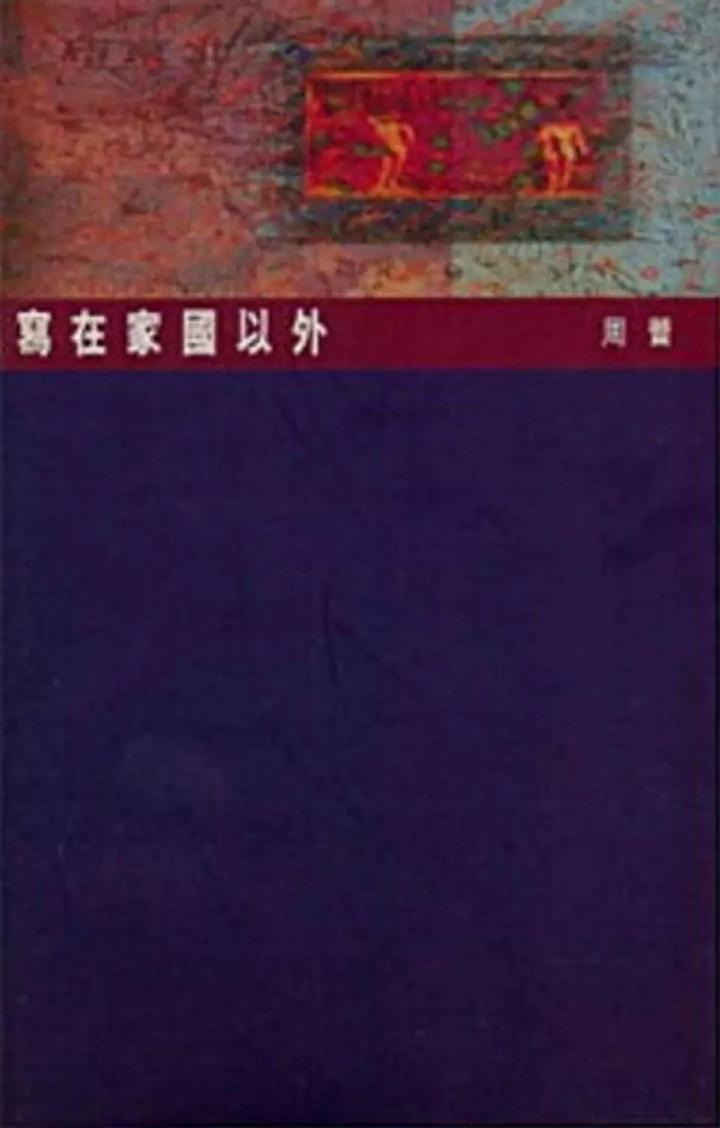
周蕾(Rey Chow)《寫在家國之外》
薩義德談到,當代阿拉伯世界的學術界,已經完全被西方所主導,各種理論都來自西方,整個社會科學評價系統都來自西方,甚至於他們看待阿拉伯人的方式,也受到了來自好萊塢的影響。他談到的現象,我感覺到和中國非常相像。中國在新時期以前是社會主義系統,比較自主,但新時期以後,在我們的學術界,社會科學理論基本上是被西方二戰以後的社會科學系統所主導的,我們的論文必須要發表到西方的比較高級的刊物上,有人提出中國花錢生產出來的自然科學最新成果首先要送給美國。薩義德說,阿拉伯世界最厲害的學者都是西方的,最厲害的阿拉伯本地學者也必須是從美國回來的,最好是某某大家如德里達、哈貝馬斯的弟子。我覺得中國情況也是這樣。斯皮瓦克在這方面是有自覺的,她認為這些學者在西方的學者面前實際上是東方材料的提供者,而回到本國之後,又變成了西方話語的權威,她將其稱為後殖民知識者。
當然,後殖民理論是有其使用限度。每種理論,都是從某種特定視角觀察事物,如階級理論側重於社會階層,女性主義側重於性別,而後殖民理論側重於種族,不能互相取代。使用泛化的問題的確存在。台灣的陳芳明認為,在男女關系中,女性是被殖民,男性是殖民者,我覺得這個理論就僭越了,本來是女性主義理論要處理的問題,結果他拿後殖民理論來進行處理。他還說,對於台灣本地人來說,國民黨政府是殖民主義,這也是一種混淆,這里面其實有一個民族主義與殖民主義的關系問題。在殖民地獨立後,統治者從殖民者變成了一個本地的民族資產階級,兩者在邏輯上是同構的,所以法儂(Franz Fanon)強調,在獨立後要把民族意識轉變成社會意識,但這並不等於把民族主義混同於殖民主義。從這一點上來說,我覺得確實是不能把它泛化了。
徐詩穎:趙老師您好,我有兩個問題想請教一下您。我寫博士論文運用那些理論都是以前沿用得比較多的,像「混雜性」「第三空間」都是後殖民理論的延伸。老師們評價文章時認為,我的理論話語都是談得比較多的。因為趙老師您在香港文學這一塊已經研究得非常高深了,那麼針對這個環境,香港文學研究如何可以開拓出新的研究領域呢?如果不按照西方那套話語,可否形成適合香港的後殖民或者新殖民的理論?
趙稀方:我覺得不是理論新舊的問題,而是理論與歷史的關系問題。我們之所以很容易用理論來套用歷史,是因為我們對於歷史的研究還不夠。
我在做歷史研究的時候,極少用到理論的詞匯,除非是我自己純粹地做理論,才會運用理論術語。我覺得理論給我們的助力,其實是給你的一個眼光,你不需要把這些理論的詞匯放進去。
我覺得首先要做歷史研究,從歷史上可以驗證理論,然而更多的是修正和發展理論,因為多數理論都來自於西方,和我們的歷史未必一致。就後殖民理論而言,這個後殖民理論跟香港的情況是我覺得相差很大。我們用有關於後殖民敘述的這些東西來看香港文學,其實並不一致,這恰恰是你可以發展理論的地方。香港和一般的殖民地還是不太一樣的,比如說香港跟台灣就不一樣,台灣基本上比較符合殖民主義的論述,台灣在日據時期,它的漢語文化都被壓制了,基本上要使用日語的文化,但在香港並不是這樣。還有,按照新殖民主義和依附理論,殖民地經濟很難獨立發展,但香港則不然,發展得很好。香港是殖民地一個很大的成功,其實它是一個例外。香港的問題很復雜,我們不要用西方的理論來套用。後殖民主義是世界性的,從南非到澳大利亞到加拿大,各地的歷史情形都不一樣,因此也有不同的後殖民主義。
《後殖民理論》

通常的殖民地,就是被占領的這個地方,由於它本身就擁有本地文化,那麼就會存在一個文化衝突的問題。通常來說,殖民者要用殖民地的文化來主導和消滅本地文化,可香港它並不是這樣的。香港島的特殊性在於,它本來沒多少居民,這里的居民是後來自願來的,是逃難到香港的。香港提供了一種跟中國內地不一樣的制度,我們看到,每每內地有戰亂等情形,都會有人逃到香港來。西方學者的看法是,香港本身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共同建立起來的,叫「cooperation」。不是說殖民者壓迫被殖民者,然後才發展起來,這兩者是一個合作的關系,就是香港的被殖民者是自覺自願地和殖民者合作起來,共同來建設香港的。那麼這在後殖民理論里面,是非常例外的情況。我們看歷史材料就能看得很清楚,英國殖民者占領香港,跟通常的殖民地策略不太一樣,占領香港並不是要改變這地方的文化,而是要找一個貿易港口。它的目的並不是要占領中國的領土,然後擴大它的盎格魯-撒克遜的文化。香港的羅永生教授,就試圖以此為對象,發展一種特殊的後殖民主義。你到國外去開會,談後殖民理論,談薩義德、斯皮瓦克,人家比你還要熟悉,但是你談中國的經驗,談香港的特殊性,談滿洲國,談台灣,人家就很有興趣。歷史和理論的關系,其實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關系,我自己後來出自選集就叫《歷史與理論》,覺得這里面關系挺復雜的。

《歷史與理論》
陸傑:我在看您的《小說香港》的時候,就是您有一個特別重要的關鍵詞就是香港意識(本土意識)的問題。然後現在您是在重新改版、再版,現在經過香港回歸之後這麼多年,那麼您再看香港歷史的話,您對原來的中心觀點會有修正或者豐富嗎?

趙稀方《小說香港》
趙稀方:新的發現還是有的。以前我們在談香港本土意識的時候,主要提西西、也斯這一派,所謂「我城」派,其實香港本土性還有另一種形式,那就是《詩風》一派。70年代後香港的新生代作家群,並不僅僅限於「《大拇指》-《素葉文學》」一派,與此同時,還有另外一個甚至於更早的「《詩風》-《詩網絡》」派。《詩風》早在1972年6月就成立了,較也斯同年創辦的《四季》第1期(1972年11月)還早幾個月。
也斯登上文壇是在60年代後期,他回憶當時存在兩大潮流,一是大陸左派文藝圈中流行的批判寫實主義,二是台灣式的現代詩。他概括這兩種方法,一是以文字作為反映現實的工具,題材多涉貧民區、工廠、工農兵等等;二是心靈的超越、扭曲的意象,詩人不太想與現實有直接的關系。對於這兩種路徑,也斯都不太認同,他的想法是表現香港,「和現實生活對話」。這種想法,就是他後來在主編《週報·詩之頁》以至《大拇指》時所提倡的詩歌的「生活化」。
黃國彬年齡與也斯相仿,出道時面臨的是相同的香港詩壇。黃國彬同樣反對左派和台灣現代詩,他回應的主要是晦澀的台灣現代詩。針對現代詩的洋化,《詩風》首先提出來的是回歸傳統。當然,回歸傳統僅僅是對於當下過於洋化的糾正,《詩風》最終的目標,是融合古今中外。
可以說,西西、也斯與黃國彬兩派都是立足香港的,然而他們對於香港現代詩歌的建立卻有着不同的理解。也斯、西西陣營傾向於藉助於香港本土建構「生活化」的香港詩歌,黃國彬等人則認為香港的長處恰恰在於它的文化開放性,能夠匯聚融合古今中外。之所以存在這種差異,與他們的身份的不同有關。大致而言,《詩風》同人基本上都是港大的學院派,而也斯、西西同人差不多是以民間自居的。
1972年的《四季》《詩風》和《海洋文藝》這三種報刊,被視為香港的民間派、古典派與寫實派的三足鼎立。在這三分天下中,前兩者都可視為廣義本土派,他們分明已經占據大半江山。
學生:老師的理論很深厚,給我很多啟發。我有一個疑惑的地方,就是劉禾對魯迅的批評,認為他的國民性概念來自於傳教士,這些地方會讓我產生疑惑,魯迅先生乃至一些現代文學作家,是否真正的陷入了後殖民所批評的殖民主義的圈套?

《阿Q正傳》
趙稀方:我覺得你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其實對劉禾的觀點也有很多的批評。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劉禾的文章?很有意思,《阿Q正傳》我們都覺得是國民性的批判,但劉禾提出了一個疑問,她說《阿Q正傳》受到波蘭作家顯克微支的影響,那麼這到底是波蘭的國民性,還是中國的國民性?如果是普遍的話,那就不能稱為中國的國民性。然後,她又提出來說,作者魯迅本身也是中國人,但作者可以暴露國民性,批判國民性,顯然說明他自己並不具有這種國民性,並且可以跳出來評判它,這說明中國人的國民性並不都是這樣。
當然,我們不能從劉禾的觀點來推定魯迅上了一個殖民主義的圈套,因為她把觀點拿過來,又進行了轉化,用來進行自我批判。在我看來,魯迅的重點實際上是對於中國的批判,他的批判必須要找一個「他者」進行對照,這個他者就是整體性肯定西方,因此在這里,亞當·斯密斯(Arthur Smith)論述到底是否正確與否其實並不重要。我們要批評一個東西,會找一個他者來進行對照,至於他者本身到底是不是這樣,並不是他的重點。這有點像家長所說的「人家的孩子」,家長在批評自己家孩子的時候,很容易說人家小孩多好多好,事實上他並不關心別人的孩子,我們不需要追究別人的孩子的真相,因為家長關心的是自己家的孩子。
昨天我在中大其實說到另外一個問題,劉禾探討國民性問題給我們最大的啟發是什麼?不是說魯迅是不是上了圈套?國民性到底是不是這樣的?而是對於「國民性」的想象和建構。也就是說,我們對於中國國民性敘述,其實是有歷史主導和建構的性質。比如說批判國民性思想,是五四啟蒙主義的視角,我們覺得中國很落後,要用西方的現代性來提升中國。在這個前提下,當然是中國本身是落後的。「五四」時期多鄉土文學,都寫中國鄉土非常黑暗,種種的封建習俗,戕害人性,文學的視角是批判性的。但是,在40年代解放區文學中,就完全變了。在延安文學中,群眾雖然也有落後的地方,但他們變成了歷史的主體,形象完全變成了正面的,啟蒙者知識分子反而成了被改造的對象。也就是說,我們需要關注的,不是中國的國民性到底是什麼樣的?而是我們為什麼這樣敘述?
學生:馬爾克斯逝世的那段時間,整個中國對拉美文學產生了研究熱潮,我自己也讀過馬爾克斯、博爾赫斯等,他們好像是在西方文化跟當地本土文化之間找到了一個融合點。那麼我想問的是,我們目前的現代主義文學運用的大多數的寫作技巧,其實都是來自於西方,那麼如何在本土傳統文化跟西方的寫作技巧上做很好的溝通?
趙稀方:西方的現代主義基本上被認為是第三世界要學習的東西,但是我們看後殖民理論的討論,會發現西方的現代主義恰恰並不是西方一個內在的東西,而是在西方與東方相遇的時候產生的,這是一個後殖民的研究成果。我們看博爾默(Elleke Boehmer)的書,叫《殖民與後殖民文學》。他指出,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出現,正是殖民地與宗主國家作家互為作用的結果。20 世紀初,在帝國遭受質疑的時候,歐洲作家對自己社會的真實性越來越缺乏自信,遭遇了意義危機,並開始對於殖民地「他者」的文化發生興趣,這成了現代主義的緣起。博爾默談到,在殖民主義日益敗落的時候,反諷成了占主導地位的文學形式,黑色幽默、戲謔模仿、反史詩等都是對於西方主流價值的背叛。在晚期帝國主義的語境中,反諷既是一種鞭笞,也是自我懷疑和批判,它不提供新的選擇。紀念在印度去世的吉卜林式的英雄帕西瓦爾的伍爾夫的著名作品《海浪》,就是這樣一曲反諷的絕望的輓歌。艾略特為了學習印度哲學,專門學習了梵文和巴利文。他在《荒原》中將不同的宗教文化拼湊起來,為混亂的當代西方提供意義。關於殖民地「他者」對於歐洲現代主義的作用,薩義德和阿希克洛夫特在其著作中已經有所提及,博爾默的新穎之處在於,他認為殖民地不僅僅為歐洲現代主義提供了參照和刺激,而且殖民地作家本身就是現代主義的組成部分,甚至他們就是最早的現代主義先驅。
博爾默《殖民與後殖民文學》

拉美文學之所以在中國引起這麼強烈的影響,它的吸引力主要在什麼地方?80年代我們有一個對於西方的模仿和超越的焦慮,馬爾克斯1982年獲得諾貝爾獎,這對中國作家產生了刺激,讓中國當代作家覺得找到了一個趕超之外的途徑,因為拉美本身也不是西方國家,而是第三世界國家,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直接超越了現代主義,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成功,並被認為是後現代主義的一個典範,所以薩義德說,後殖民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唯一可以交叉的地方就是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中國作家就是被這種成功所吸引,博爾赫斯的小說實驗比馬爾克斯更加先鋒,所以他在中國引起了更大的熱潮。
不過,80年代中後期以後,實驗小說基本上中落,這個時候影響比較大的是米蘭·昆德拉。米蘭·昆德拉是捷克人,捷克是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後來米蘭·昆德拉因為批判蘇聯被驅逐,現在變成了法國籍。這次在紹興我們召開中法論壇,我專門談了米蘭·昆德拉。我覺得我們在90年代以後,我們的注意力有所轉變,這個轉變的原因其實是從這種追逐西方、追逐拉美魔幻現實主義,變到對於中國內在歷史的反省。80年代以來,我們對於中國文革實踐的反省是很不夠的,米蘭昆德拉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參照。
凌逾:我想問的問題就是,趙老師既有扎實的理論基礎,又有寬廣的研究領域,研究到後來就可能越來越有貫通感。趙老師您能給我們講講學術研究的方法問題嗎?謝謝。
趙稀方:這個問題很大,也涉及到很多問題。我覺得導師指導學生,要找一個中小型題目,一定要有限度,這里面的對像是可以窮盡的。論文做出來以後,即使沒有一種新的理論闡述,至少有新的材料和歷史整理。我覺得學術比較高的境界,是做歷史研究,然後有一個理論上升。如果做不到理論上升的話,在有限度的范圍內,把材料全部給做出來,這個論文也就有價值了。所以我讓學生做翻譯研究,如做「孤島」的翻譯,「上海淪陷區」的翻譯,「滿洲國」的翻譯,我要求他們把這段時間所有的報刊有關翻譯的材料全部要找出來,就這一點,論文就自有其價值,別人以後做研究,繞不過你。如果做一個很大的題目,窮不盡對象,只會越來越吃力,越搞越糊塗。
另一個方面,就是要具有較為開闊的研究視野。我自己本身並沒有什麼學科意識,我自己是中國現代文學出身,讀碩士的前一兩年都在讀報刊,就從《新青年》開始一直讀下來了。後來做新時期翻譯研究,1949年以後的報刊、新時期的報刊也都看,做晚清翻譯研究,又往前追溯到傳教士和晚清報刊。這幾個過程下來,從1807年開始一直到當代,基本上所有的報刊差不多都看過。
《新青年》

侷限在某一時段的學者,視野不太開闊,不太瞭解前後的東西,這就是一個學科的限制。我們社科院學者,因為不在大學里教書,不必非得按照現代文學來上課,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學科的限制。但我們跟其他學科的學者一聊起來,就發現學科的隔膜非常大。每一個學科都有自己的前提和慣例,看起來和別的對象相近的學科差異很大。我們的閱讀是應該打開的,這樣就會在很多問題上融會貫通起來。
知識視野的大小,決定了看問題的角度與方法。如果讀的東西很少,看了半天材料也看不出問題來。有學生專門給我打電話問:「為什麼我看《蕉風》,以及相關的報刊材料,就是沒有問題,而你看了一遍,為什麼就能發現問題?」這問題從哪里來呢?我覺得這與自己視野的寬闊有關系。馬華是東南亞文學的一部分,但除了馬華文學之外,我還瞭解香港,也瞭解台灣,也瞭解其它海外華文學。我一看東南亞的這些東西,就立馬想到香港和台灣。在五六十年代,香港、台灣跟東南亞之間的交流很多,但各個地方的情況又不一樣。如當時台灣的是比較封閉的,因為有政治化環境的限制,但他們還可以在香港和東南亞發表文章,這些往往是不敢在台灣發表的文字,這些東西做台灣文學研究的人往往沒有注意到。香港其實是一個集散地,有很多香港報刊的發行量,在東南亞比在香港還大。如果有台灣、香港與東南亞這樣一個整體性視角,這樣比孤立地做這些地區的研究,更加容易發現平常發現不了的問題。我覺得地域之間的溝通、文本和理論的溝通,都會給我們帶來新的視野。
凌逾:今天的訪談對話很有深度。第一場的講座比較容易,因為有備而來,但第二場的對話訪談難度很大,要隨機應變組織語言,將所有知識儲備轉化出來,深入淺出地講明白,這非常考驗講者的功底。我每次遇到這環節就開始冒汗,但是趙老師娓娓道來,講得詳盡豐富,實在讓人羨慕。這次來的聽眾都是對學術研究很有興趣的人,這從你們聽講的態度,從你們的提問,可以看得出來。今天由講座進入到論壇,變成了高端對話,是由發送者和接受者共同完成的。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非常感謝趙老師精彩的演講和對話!
錄音整理:劉春芬、陳麗妃、丁一、鄧媛、夏婉琦、謝慧清、李婉薇、何春桃、肖小娟、蔣迪、李雯苑
來源:跨界太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