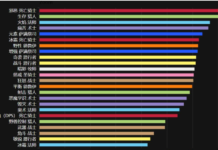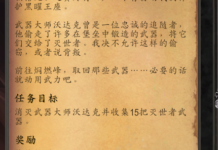「來一杯?」
王簡接過李師傅遞來的一杯液體。櫻紅色。湊在鼻口聞了聞,粗烈的酒精味兒中夾雜著絲絲腥甜,像這只油膩的不銹鋼杯中泡進了無毛的小鼠。但杯底確實有些東西,薄薄一層白色的沉澱,王簡慢慢搖晃,粉狀物開始在液體中游盪。被厚厚的機修手套裹滿的小杯中,像是某種東西浸泡在有機液體里恆溫孵化。這樣的聯想讓他的心中不免生出幾絲忌憚,即便這遠不是李師傅的貨船私酒中最奇怪的產物,有次嘗酒他竟喝出了一股髒器味兒,氣氛像是回到他童年生活的屠宰場。
遲疑地,看著老李的堆笑以及裂出的一口齲壞的牙,王簡還是吞服了下去。
「咳!咳!」一股子濃重的糖精味兒裹著高濃度的酒精,像一隻蛞蝓撓進了他的喉嚨,黏液與軟體箍緊他的氣管和胸腔。
「……你該少放點兒糖漿。」
據老李追述,他是從那堆貨櫃中扒出了一批不明的外星蘿狀莖,澱粉含量雖然較低,但足以充當為私酒增添風味的「合理消耗」。為了方便發酵,他還加了包合成糖漿。
王簡往嘴里灌了一口循環水稀釋刺激,塑料瓶身都被捏扁。用手套拭了拭清鼻涕,酒精刷新了鼻腔的感覺,他又聞到貨倉內滿滿的機油味兒。
「再來杯?」
「啊?不必了。」
走進甬道,他向背後的李師傅擺了擺手。即使他試圖用嘴唇過濾,舌頭上還是有股沙沙的感覺。
翌日,標准時七點。葡萄串號上,底層船工艙室的照明燈集體通電,一曲嗡嗡沙啞的《春天奏鳴曲》從老舊的播放器中傳出,之後合成女聲空洞而優雅地預祝「我們擁有美麗的一天」。她昨天也是這麼說的。
白熾燈照得王簡腦門發汗,他用枕頭捂住面部,想再多睡一會兒。可嘴唇乾澀,鼻腔里那股私酒味兒仍揮之不去,枕頭上的發油和消毒水殘留也不好聞。
昏昏沉沉地,像脖子上擎著一顆生蟲的橡子,他從床上疲憊地爬了起來。
擠了點無水清潔泡沫,鏡子里細脆的發間點綴著白色的枯草,酸澀的胡茬,臉色更是一副蠟黃肌瘦的船工苦相。當然,這些都不是他最嚴重的健康問題。
要知道,遠航船工是抑鬱症多發的職業,但貨運飛船上的隨船醫師可不多見,一艘船往往只有一名負責大事小情,甚至一些資金緊張的貨運公司會讓船工接受幾個月的醫療培訓後應付差事。
「咳!咳!」
摳開錫箔紙,王簡服下了一粒常用的感冒藥,希望止痛藥和興奮劑的成分會讓他神清氣爽起來。
「嗡,嗡——」
變壓器的響聲回繞在暗光的甬道中,只有三四條牆腳的檢修燈尚在維持運作。四十七攝氏度的氣溫烘烤線纜的絕緣膠皮,空氣中有一股仿佛橡膠燃燒的臭味(混合其他各種角落的垃圾被烤乾的味道),當然電線短路燃燒也並不罕見。葡萄串號是一艘老貨船,且易主多次,維修層的恆溫系統早已失靈。在某部試圖管理廣袤銀河的《航船管理法》的字句里,這艘老船多年前就:要麼該在拆船廠里被熔化為新的標准件,要麼乾脆墜入一顆荒蕪行星的大氣。當然,《管理法》更嚴禁走私。
王簡坐在通風口旁,脖子上貼著冷貼,盯著他的小型電視。電視機的電源線插頭早被拔去,電線赤裸地接著檢修專用的插座。錄像帶的畫面已經泛綠,播放著不知道看過多少遍的《異形1》。打發時間是遠航船工的日常難題。相比零頭般的有效工作時長,仿佛這座「太空卡車」中一眾精神的日漸擠窄,才是對僱主最有益的消耗。
「Bring back life form. Priority One. All other priorities rescinded」
「the damn company. What about our lives, you son of a bitch?」
雖然熒幕被眼膜反光,但瞳孔並不聚焦於電晶體的色彩變化。王簡的思維逸散在過去人類對太空運輸業的想像中,對他來說最為吸引的是夢幻般的冷凍技術——夢中略過引擎經年的喧囂,醒來時便抵達港灣。這種設想約在百年前的地球上火過一陣子,甚至還有科學家用財產和遺體進行投資。當然,現在嘛,被普遍視為舊時代包裹技術理想的熱門騙局之一。沒有一具屍體在一輪又一輪的技術爆炸後死而復生。
片刻,他忽然站起。轉過頭,甬道仍舊沉悶,但王簡好像聽到什麼聲音,像是——「leng!leng!」
——老鼠的細爪匆匆爬過金屬柵板,又或是頂上的夾縫塞著一隻節肢動物。
可,這兒連蟑螂也不會有。
片刻之後,仍是寧靜。
他剛想要坐下——
「王簡?」(軟舌緊湊耳語)
「wuen!」王簡的身體驚得直起,忙用烘熱的手套擦了擦右耳,仿佛毛孔還殘留呼吸的濕度。
變壓器的響聲安靜得不計,仿佛整個甬道都被他洶涌的心跳灌滿。嘴唇乾澀,沉重到可以致於靜止的呼吸……
「太空型精神分裂」
隨著兩股蒸汽呲出,檢修甬道的氣閘被關閉。王簡滿腦子琢磨著這個曾在員工手冊里出現的概念,據說發病率與航行時長正相關。但迎面的冷空氣仍給他墊了些快意,何況醫師的處理也不過是鎮靜劑了事。當然嚴重失常的話,會被關進漆黑的窄倉,日復一日鼻飼流食,直到停靠後隨床被送進某個占地龐大的醫療建築群的某個窄室。
可他還需要薪資,需要精神抗壓能力的再生產。也許——他需要來杯老李的那種私酒?對,他舔了舔乾裂的嘴皮,像在安撫一種對於甘霖的急切欲望。
對,再來一杯。
「喲!小王,你來啦?」
即使隔著幾十步的距離,他都能感覺到老李的神色中帶著一股莫名的興奮,他老化發麻的神經元似乎重啟活躍,瞳孔里不斷放射異常的生物電能。也許是貨倉的循環製冷管道中補充的氟利昂,降下的幾攝氏度產卵出克服沉悶空氣的活力。
油跡的不銹鋼器皿被換成清洗得透亮的玻璃杯,能看見浸泡著脫水果乾的淡紅與泡泡,果味汽水般液體明顯更為純粹,煞有其事地。他還切了兩片薄薄的外星蘿卷在杯口,沒有氣味的殷紅果汁匯在杯沿。說是想帶來一點含水的清香。
老李聲稱配方已經做了近乎完美的改良,「老實說,我從來沒喝過這麼棒的酒」。
即使王簡半信半疑,但鼻子湊近杯口所探查到的清水香,不免讓他產生嘴唇更進一步的欲望。
「呼!」
汗毛豎起。仿佛周圍層層高聳的貨櫃被變形的空廊壓細,擁擠的金屬感在一陣貼近他皮膚的冷後似乎可以概略——細細地爬過衣襟、身體。仿佛機油味兒也成為一種風味,變得好聞起來。
甚至,有點……興奮?
「再來一杯?」
……
「再來一杯?」
「再來一杯?」
杯杯酌飲。口與鼻間,帶有濁氣的呼吸不斷循環,酒精味兒不斷被酌吸進氣管的最細端。牙齒間還保留有對於根莖片咀嚼感——沁入酒精的軟脆。血液中仿佛不斷循環提高的醉度,讓王簡的眼前蒙上一層淡粉色。視距拉大、加深,仿佛一雙魚眼浸入粉色蛋白液污染的一湯,在水底朦朧地看見另一個世界的細節。
狹長的甬道變成晃動射線的背景,好像自己面朝自己地漫遊。點線的兩條燈光蟲眼般閃爍,一條條葉網縫隙拱起甬道內壁。頭上,一樁線纜在扎帶崩斷後散成低頂。應該是有人在抽菸?卷制的菸葉上火星退行,有一股沖味兒。聞得頭暈,鬍髭、衣襟的深黃體垢,讓我發酸,想嘔吐——「媽的!」、重拳、醉中的暈眩、眼眶的腫痛,方向感再次顛抖、跌倒,最後螺釘湊近鼻子的鐵銹味兒。鋼葉細細的一縫里,仿佛舷窗中無光的宇穹。
舷窗外,白色涌溢、一道強光襲眼——
耳邊傳來呼嘯的風。
漆黑的鉚接鋼板,冰冷,冰冷與痛,將他的耳朵與裸體粘死上面,不得動彈。頭朝黑郁的海面,他大字趴在沖向海底的鐵灘。目光可及,一座燈塔緩慢移動它垂敗無用的燈光,除了偶爾讓王簡感到刺眼。海風里有一股腥味兒,令人窒息,仿佛滿灘擱淺的鯨群,脂肪正在腐爛——死寂。
天空正在沉沒,把把黑色的颶風剌過穹頂邊緣,殘燒的重雨,淋下天際線。
此時,他的雙眼死魚般看向眼前的另一個人,和他姿勢一樣,赤裸地趴在鋼板上。一半的臉、手掌、胸脯和肌肉沒入鐵中。
「簡?」
嗯?
「王簡!」
(激動)
「王簡!!!」
(皮膚撕扯,肌肉暴露,流血。憤怒)
王簡感到一大團蠕蟲正在自己胃里蠕動,細密的體壁順著食管爬上咽喉。
「唔!」
他,在迷朦中,自己看見自己爬回熟悉的房間陳設。止不住嘔吐起來,酒腥、胃酸、燒喉感,隨即跌倒在地板上。
燈光閃爍,眼前是他的一攤嘔吐物。在陰明不定間,王簡似乎看見嘔吐物中不斷發生細小的蠕動。一根線蟲從灘糊中直立,裂出細小的尖牙。
「嘶——!!!」
「********一天」
王簡疼痛地睜開雙眼。耳里的暴鳴只讓他聽清末尾的兩個字,但詞匯細小得仿佛尖指,勾下他喉嚨里的兩條肉,撕出血痕,讓他不禁懷疑咳嗽里會不會帶有血絲。
前額昏脹。扶住椅子,他從地板上搖晃地站起,占去視野一邊的黃色收小為粘稠地平攤,滲線聚乙烯板材的細縫,在空氣循環系統的作用下逐漸乾燥。他擰開飲用水口,雙手捧起往喉嚨吸溜。又將寶貴的循環水潑在臉上,濕淋淋的手抹在後頸。消毒水的氣味混入那股酸敗氣,變成一股奇怪但在船中並不明顯的味道。
回到鏡前,穢物還在臉頰一側殘留幾塊黃色的干膜。但右眼周的瘀青與浮腫更加明顯,火辣辣的疼痛讓他想用沖冷的手指去觸碰。
「嘶!」
嘗試進行回憶,讓他的頭有些暈眩沉重。爬回來的路上,究竟誰是給他一記沖拳的面孔,實在模糊不清。邋遢的鬍子幾乎是船上人人的標配。
他抽出一條新抹布,試圖處理那灘穢物。只是擦開發干發深的表層,更新鮮的、黃色與嘔吐物中濃縮的酒精腥酸味兒,黏性地附著在更大的表面。一種瘤胃腐爛的氣息,王簡一臉厭煩的慌忙。捏緊鼻子。白色的細小毛圈已經刮住一片,還具有滴狀的流動性。雙指將毛巾擲向垃圾桶口,似乎他就此無關。
「物資緊張,先生」,右眼部簡單被蒙上冷貼。處理完瘀傷,窄桌對面的醫師對他的請求只是沒有表情地回應,「你也知道,鎮靜劑不屬於必須保障供應的日用品」。
吊扇吹動著房間中懸掛的塑料簾,響聲有些清脆。抵著牆角,濾過白色的床單,一張整潔的檢查床籠罩在淡黃色的半透明里。窄小密集的診室里,有一股整潔味兒。
「或者」,醫師話鋒一轉,「要不要我給你做一次感染檢查?」
「感染?」
「你該知道的,現在貿易眾多,多少會夾帶一些不明的入侵物種。比如說——」,說到這里,醫師頓了一頓,轉了兩圈太空筆,笑意難以揣測,「寄生蟲」。
醫師站起身來,似乎是要從身側的藥架上取下某瓶檢測試劑。
他的大褂明顯過度清洗,下擺毛邊發硬。顯得舊黃。
「現在對貨船來說,相比寄生蟲,精神分裂能帶來的麻煩還算常見和可控。」
「……不必了……」
王簡忙從座椅和診室離開,掀開塑料簾布。即使走進甬道深處,但仍有目光落在他的後背,仿佛醫師始終站在診室門口注視著他。他的後背冒出疙瘩,有如熱芒刺進毛孔。
(深吸)
這讓他肺葉顫栗。
冷汗,困難地吞咽口水。
即使在逼仄的房間,他仍感覺自己被不明處投來的目光凝視。
十幾張藥殼板散在洗漱台上。手掌捂住嘴巴,一大把的藥片被堵在嘴里。
「草!」
他回頭抓起椅子,扔向房間的陰暗處,仿佛那里蹲著一雙直勾勾的眼睛。
嘴里的藥片抖落地板,還有一些粘連在口腔黏膜。後背緊貼著牆——滑落,抱著雙膝,他崩潰地躲在牆角。
在過量的精神壓力中,王簡思維過度的電流地錮住了某種渴望。
「酒,對!酒!」
指間薅住頭發,王簡暗自呢喃。
酗酒在船運業並不是一種可悲的現象。他如此勸服自己,即使……這讓他與自己糟糕的父親,事實趨同。
「王簡?」
「李師傅?」
「過來。」
我好像在流淚?有液體流了出來。為什麼這麼昏?這麼黃?我的眼睛,好脹。
(聲音夢囈般地恍惚)
穿過一棟棟的貨櫃,看見一個貨櫃打開著,貨物滾了出來,堆成一個小斜坡。是那種蘿。
王簡走了過去。
一個個麻袋被他撕開,漏出來的蘿上還掛著干黃的土粉。他的嘴角也有土,還有血。更精準地描述:他齒崩唇裂,嘴上、下巴上淌著混有汁液的血。幾顆牙齒斷在在被撕開的蘿肉里,他就躺在這些被撕開的肉上,後背沾滿顏色。
——遇刺的君王。那就應該是紅色的,但在王簡的眼前,卻是近黑的褐色。
「過來。」
李師傅的聲色近乎將死,但根本上是一種喜悅。這種喜悅在他的臉上清清楚楚。
「咳咳,過來。」
王簡爬了過去,在恰當的位置李師傅抓起一隻撕開的蘿,流血的指尖扎進韌性十足的皮。王簡跪在下面,用嘴去接和著血的汁液。他看見逐漸擰爛的果肉里有蠕動的肉線。
眼角的液體黏稠地流到了嘴邊,但觸碰到的,不是淚水。
(耳鳴)
(鳴叫——)
鳴叫逐漸清晰,是蟬的聲音。他好像背靠在樹蔭下假寐,陽光暖和,空氣清涼。
眼前的模糊中有個悅動的白影,湊近他的耳畔,悄悄許下稚嫩的承諾。
這一切,隱隱,似乎他十歲的氛圍。
只是一個呼吸,他睜開雙眼,但看見母親坐在沒有開燈的沙發上,背對站在門口的他。電視機的光亮離母親很近,照亮她側頰的銀發,透明。
房間里一切都很安靜,似乎吹進屋里的沙暴聲都按下靜音。只有熒幕上的人,通過喇叭沙沙地講話。
「在某種意義上,這些青年成為了我們時代最腐敗的產物」。
淀川 真(企業行會代表),如此意志。
而這便是,哥哥死亡的最後通牒。
那個喜歡穿皮夾克,站在秸稈上,對被內髒吸引來的大頭蒼蠅揮動球棒的青年,他曾經瘋狂崇拜那些濫用致幻劑的朋克,崇拜那些反抗。而離開馬來亞的屠宰場,往大都會闖盪的他,最後的下落是郵來一封死亡報告和幾紙補助:他在參加反公司的大規模遊行時,被公司安保用一米長的生銹撬棍打斷了脊椎,死於嚴重內出血。
母親的失語便是從那時起,直到下葬。
哥哥死訊後的第三年,他在公司收購屠宰場的土地合同上替母親簽了字。病床上的母親被蓋上白布的三年後,他在船運公司的「賣身契」上簽了字。
離開地球的那天,他第一次親眼見證這顆行星:從南極洲到曾經的亞馬孫雨林,上面擠滿了燈光。
他眼前一黑。
(「hu——en——」)
似乎耳邊有什麼在呼吸。
像是肉牛鼻息的濕潤、
像是母親哄睡的溫柔、
像是——
床上,王簡頓時睜開了眼。看著白色牆板。
(「hu——en——」)
他只是自然地鼻息。
「李,死亡。死因:飲酒過量…………」,一陣鍵盤聲後,黑色的螢幕顯出幾個綠字。
老化的白色塑料殼中,密集型的列印元件「嘶嘶」幾聲後吐出了一張發熱的A4紙,上面是幾張現場照片和簡要說明。
船工們都聚集在貨艙里,一條貨櫃間的過道擠滿了人,大都穿著工裝、皮圍裙、厚手套、馬丁靴並頂著護目鏡。但似乎,他們都在對他小聲議議,打量著這個平時最容易忽略的人,用一種奇怪的眼神。忌憚?這讓王簡有些惴惴不安。
穿著白襯衫的管理層站在前面,但與大家平齊。只有船長站在高處向大家訓話,但也基本是些安全手冊里的固有詞匯。一刻鍾後,他跨下台。船工們逐漸分列,好讓屍體被抬出。
當擔架抬到王簡面前時,白布突然被拉開,露出李師傅鼻孔放大的遺容。臉上僵住幾絲笑意,顯得猙獰。但更明顯的,是濁黃的雙眼,在發青的臉上幾乎分辨不出瞳仁的輪廓。
但。恍惚間,王簡看到眼睛在蠕動。眼膜頂破,沿著裂痕長出尖牙的喙。
(嘯叫)
他急忙用雙手用力撫下眼皮。待一睜眼,白布安然地遮在李師傅的面上。
寒意陡然。
這時,船長走到王簡面前,「對了王簡,你等會兒來下我辦公室,昨晚有人看見你進貨艙」,有些不滿道,「你們多少該收斂下吧」。
他停在王簡身邊片刻,又面露難色,「你身上是什麼味道?還有你要不去處理下你眼睛?這包紮上都黃了」。
也許是幻覺。李師傅渾濁而不再生動的眼睛,像挖取自一條招蒼蠅的死魚。但他始終覺得那是在盯著自己。
去到衛生間,看著鏡子他撕下冷貼。棉質地的中心聚攏了一股黏液,還有,味道。像是死魚。
他看著鏡中的自己,右眼沒有感覺地流淚。
不……不是淚,是黃色的膿液。
右眼突然睜開!開始夸張地轉動,眼皮與黏液顫抖,它快速地巡視了十幾個漩渦。
「啊!唔!!!!!!」
不受控制地,他的雙手捂住了自己的嘴。
」唔!!!!!!」
他的右眼凝止在鏡中的臉上。他的右眼,正死死地盯著他的左眼。
幾只線蟲從眼瞼鑽出,裹著粘液在角膜上扭曲。耳膜邊出現了蠕動的聲響。
「王簡?」
抄起扳手。
哞!嗚——(被屠宰時,肉牛的驚懼)。
貨艙的一盪中只存在著幾聲呻吟聲。
扯下籠罩蘿莖的帆布,王簡的喉嚨中發出幾聲非人的喜悅(牙齒密集地敲擊)。
撕開蘿莖,用牙咬,咬得牙齒松動、脫落,流血。
貨艙中,紅色警報燈回響時,它黏血的雙指從一顆黃色發紅的蘿中夾出一顆卵。半透明的白,仿佛能看見成千上萬的小蟲在其中隨紅色的細光浮動。閃過遇水融化的印象。
他吞下了卵泡,內果皮般的鞘膜在唾液浸濕下溶解。
耳膜蠕動的悶響,清晰,耳膜中蟑螂窩爬行的窸窣,蜂群。
蠕動——蠕動——
眼前的一切都開始劇烈顫抖,不再真實。
恍惚間,仿佛做了一個漫長的夢,混淆了時間與空間。記憶粘著在金色樹脂中的飛蟲。
古老種族精神的歷史,持續億萬年的蠕動和寄生。
母親的童謠,雨林深處最古老神明的贊歌,鼓聲,煙的水味,癲狂的祭司,惡魔狩獵般地收緊肢體。蛇的貼地游動,能聽見三角的細鱗摩擦葉片的沙沙聲
一個最古老種群的生存形態,寄生精神,滲透漫長記憶的生活方式。
跌落低重力環境的微塵。
一雙散著魚腥氣的眼光跌倒在地。
漆黑的艦船,掠過上方行星的大氣風暴。
無人聽到,它恐懼風聲般地呼吸。
「hu——en——」
來源:機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