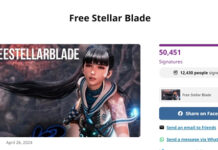「食堂的飯菜不算可口,」她回到教師宿舍時,還在回味最後一碗粥的甜味,「但這甜味還不錯。」
宿舍里沒人,明天是元旦,老師們基本都回家了。她與丈夫年中時離異了,在城里已沒有歸處。她沒有脫外套直接躺在床上,甩掉鞋子盯著天花板。暖氣開得很足,不一會就覺得與腦袋接觸的被子燥熱難耐。她想再出去走一走。於是又彎下腰穿剛甩掉的鞋子。
穿鞋時,手指提鞋的觸感讓她微微一愣。她沒有細想,關門時她在心里決定,就把這觸感激起的回憶當做今天散步的配菜。
走出林立的宿舍樓群,她直接走向學校里的人工湖邊。樹枝與葉子變成了天空下黑色的影子。天色漸暗,但還只是將要黑天,夜晚還沒到來。
從哪里開始呢?她懷著一絲猶疑與期待開始思考剛剛的既視感的來處。她立刻想到自己大學時跟前夫的第一次約會。出門時,她一直提不上自己的板鞋的後跟,她很使勁地提了好幾次,手指都痛了。她提鞋時一直低頭聞著自己圍巾的味道,那味道今天回想起來也令人滿意。當時也是年末來著。是否那遲遲提不起來的鞋子已是她婚姻失敗的一個預兆了呢?她閃過這樣的想法。但立刻果決地將它掐滅了。她最厭惡自己身上莫名迷信的傾向。
當時他騎著一輛淑女單車帶她出門。那輛車應當是他借的。她還記得,他騎起來很笨拙,一直不停地搖晃。她並不怕摔車,所以搖晃時,她只是更加用力地抱緊他,沒有說什麼,也沒有慌亂。
那是一次成功的約會,從結果上來看。最後回宿舍時,要騎上大上坡,她明顯感覺到他已沒有力氣,蹬不動了,但還是帶著一絲狡黠的喜悅,坐在後座觀察著他。「他要怎麼辦呢?」她在心里問。她的思緒飛遠了。她想,「我當時不知道,我往後的人生要問多少次這種問題,這個問題是多麼令人討厭,但我當時竟感到津津有味!」他一直努力地蹬,車子都不動了,直到車子將要歪倒,她才輕巧地跳下來,並因此快活地笑了。
她想到自己好幾年沒有對他笑過了。他們會因為她關後備箱時太用力而吵起來。她覺得真是不可理喻。蘋果洗的不干淨也要吵。房子裝修也要吵。她姐姐去年病死了,那段時間,有很多原因,她覺得再也無法忍受他倆之間的溝壑,於是就離婚了。
她經常罵自己大學時期的盲目。「我到底長沒長眼睛,看上了一個什麼東西呀?」他幾乎天天喝酒,搞得自己一身臭味,頭腦都麻痹變成漿糊。沒有話可以說,沒有任何快樂可言。「如果不是為了兒子,」她嘆了一口氣,「如果不是為了兒子,早就不跟他過了。」她這一口氣是嘆自己把兒子當做懦弱的擋箭牌,她警告過自己好多次不要再這麼做了,於是立馬把想法轉到別處。
與兒子的相處也不愉快。「我似乎給他太多壓力了,不只是推動他學習之類的壓力,我的疼愛也是他的壓力。他是我唯一的出口,他不喜歡,我明白,他承受不住。」
「多談一談,多談一談!」不管是哪段關系遭逢瓶頸,她總想先對自己這麼說。但她幾乎是立刻就會泄氣。她早已預感到自己經營的關系全部都走向下坡。
「理解萬歲!理解萬歲!」
但要說「理解」還是「不理解」,那大概最後還是「不理解」。理解不會萬歲,不理解才萬歲。理解只是茫茫不理解中的一點星光罷了。有多少自認為相互理解的人,有多少自認為互相的感情超越了理解的人,最後走向了不理解、相互憎恨的結局。她想,真是一群傻瓜。她又想到,自己也是這群傻瓜中的一員。
每段關系開始時,她總是信誓旦旦地對自己講,鐵定要理解別人,要愛護別人,鐵定要把這段關系培養成最好最穩固的。她的父母同學前夫兒子,現在看來,全部都是失敗,沒有哪段關系是她還有心力整理的,沒有哪個人是她還真心想要面對的,全是破碎。不過話說回來,她並非徹頭徹尾的悲觀主義者。意思是,她還不認為理解是不可能的,她還未完全否定這一切。說她是「不理解主義者」有點過火,她不是其中一員。也許,不理解主義者有集會的話她會去看一看,就在會場周圍逛一逛。她想,沒有比不理解主義者的集會更矛盾更有趣的集會了。
一方面,她認為自己生活的失敗、一切關系經營的「破產」歸因於自己。她總覺得自己努力得不夠。爭吵爭吵爭吵,分歧分歧分歧,每一次她都受夠了。但是,「如果下一次,」她在自己心里說,「如果下一次我再溫柔些,我再體諒一下,那麼不要說爭吵會消失,一切不幸都會遠離我。」
另一方面,她心里很明白,沒法再溫柔了,沒法再多體諒一下了。「憑什麼,憑什麼總是我要多犧牲一下。」她會立馬產生這樣的想法反駁自己。「憑什麼?」她就這麼一直嘟囔著,憤怒不滿的小小火苗又被點燃。她又會覺得自己太軟弱。就這樣翻來覆去地想,一會這樣一會又那樣,搞得自己累了。
她精疲力盡了,什麼都不願想,什麼都不想做了。所以,前面形容她的關系的經營,她覺得「破產」這一用詞是令人滿意的。她累了,破產了,再也沒有一滴愛,也再沒有一滴憤怒了,完蛋了。再要她去愛、去生氣,也不是不行,她也許會,但那對她都是折磨。她想,就像打桌球球,打過去打回來,而現在,她累了,不想打了,想回家了。
「不理解萬歲!不理解萬歲!」如果她最後這樣說,也只是因為累了,不是因為別的。
她走到湖邊,湖邊有長椅。天完全黑了,湖水黑洞洞,細小的波紋反射點點燈光。她坐下來,周圍往來行人很少,安靜極了。
「跳下去,跳下去怎麼樣?就這麼淹死好了。會有幾個人感到悲傷呢?我的兒子,我知道他會哭。他一定會很傷心,就算他在人前不落淚,晚上他一定會在床上哭的。啊,孩子們都是哭著降世的,這多麼悲慘啊。就這麼淹死好了。」
她又想到自己的童年時光。「我上小學的時候,我還記得禮堂里大家一起唱歌,贊頌這個贊頌那個,唯獨我沒張口。我不摘帽子,也不出聲。我記得老師把我拉出隊伍,我還雙手捂著頭哭。我為什麼不唱呢?」
那已是久遠的不能再久遠的時光,但是心里的委屈和悲傷就像剛剛來到一樣,她一下子又想哭。不過風吹在臉上,把這想哭的一口氣吹回去了,結果她只是吸了吸鼻子。禮堂的木地板的印象依然清晰,有的地方光滑,有的地方光滑的部分脫落了,露出一道道木板的紋路。但是,她覺得不再能理解那個自己了。那個小學生是誰呀?她為什麼就是不唱呢?她已回想不起原因,甚至想要那時的自己停下哭泣,開口唱出來。
學校的湖邊是一圈橡膠步道,有一個男人看來已經沿著步道跑了很久,正氣喘吁吁地跑過來。大冬天的,他還只穿著短褲和薄薄的背心。他經過她身邊時,她感受到那人身上散發的汗濕和熱氣。她不禁一直看著他跑遠的背影,那人腳步已然很不穩,腿都軟了,跑起來實在難看。她看著看著,就想到了法國電影《精疲力盡》里最後男主角中槍的場景。那人也像是後腰中了一槍。
她突然感到一陣輕松。因為這個跑步姿態醜陋的人,也因為想到《精疲力盡》。她想:「要是我有一把手槍就好了。我要手槍不是為了打誰,不是為了發泄什麼,只是想要手里有一把槍可以握著。」她想著,手里握住一把槍,槍比想像中重很多,握把冰涼,扳機細小,像一段小小的象牙。她看著這一段小小的扳機,想它可以射出多大力的子彈啊,因為這個想法她感到欣喜。手里有一把槍,她感到輕鬆了。她大口地呼吸,感覺著涼涼的空氣充滿肺部。它會是一把什麼槍呢?應當是一把左輪手槍,要槍管細長的,就像電影里的一樣。她把左手比成一把槍的樣子,抵住太陽穴。手指頭軟軟地碰到自己的頭,冰涼的觸感讓她一下子想笑。
她克制住自己的笑意,慌忙站起來往回走。她想,自己為何對這突然到來的笑意有羞愧感呢?不可克制地,她的人際交往的圖景又一次浮現眼前,她的友人們家人們學生們,拼貼的臉龐形成了一張壓力的網。但是這一次她帶著剛剛的輕松感審視起這張模糊的網,不知為何不快消散了。
她仍然很累,不想行動,但她突然覺得好簡單。不知道具體是什麼簡單,也不知道為何簡單,只是好簡單。她什麼都不再需要了。她加快腳步。路燈亮起。她還是左手比成槍的形狀,然後去想那些關系。她回想起的幾乎都是不快,源源不斷的問題,沉重痛苦的折磨,各式各樣令她頭疼的不理解,不過這些似乎都不可怕了。她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任何問題,沒有鏟除任何問題的根源,但她覺得輕松。「為什麼?為什麼呀?」她想知道自己怎麼會這麼想,但沒有人能回答。
她感到自己獲得了喜悅,就好像在自己的人生獲得巨大的成功時,一切人際交往給她帶來的只有幸福時,才會產生的喜悅。但不是的,現在她的人生如果可以找到詞語來形容的話,也絕對不是「成功」「幸福」,而是「失敗」「破碎」,然而她不覺得應該為此羞愧,她發自內心地覺得無所謂了。
行人紅彤彤的臉頰,呼出的白氣,這些在路燈下顯得格外可愛了。每個人都是那麼不同。她帶著好奇打量他們,從這打量里找到快樂,但她沒有任何企圖,她不關心他們的事,不關心他們有怎樣的人生,這方面她感到完全自暴自棄了。
福克納在《野棕櫚》的最後寫道:「記憶要是存在於肉體之外就不再是記憶,因為它不知道自己記住的是什麼;因此,當她不在了,一半的記憶也就喪失,而要是我也不在了,整個記憶都得終止。是的,他想,在痛苦與虛無之間,我選擇痛苦。」她讀這本書的時候感到自己完全理解了這段話,從那個故事出發,最後一句話「在痛苦與虛無之間,我選擇痛苦。」她感覺百分百有道理,她深受感動。現在那個感動的心境還在,卻完全影響不到她了。「真是一幫徹頭徹尾的傻瓜!」她想。現在,她贊同《精疲力盡》里米歇爾對帕特麗夏說的話。「在痛苦與虛無之間,如果要我選的話,我選擇虛無。」她笑出聲來,「不過,這也好不到哪去。」
後記:新的一年了,祝願各位新年快樂。本文獻給我的媽媽。
來源:機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