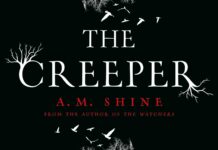01
天壓抑得很,烏雲幾乎蓋到了頭頂,密不透風,將太陽完全遮蓋了起來。明明是中午,卻如同深夜一樣。這樣的明暗改變是在極短促的時間內迅速完成了,無論怎樣的人身處其中,面對這種災厄般的劇變,也免不得心悸。爾薩·海雷丁帕夏便是這樣,望著遠處鋪天蓋地的烏雲,它們滾滾地堆積在地平線上,將那里糊成迷迷茫茫的一團,像極了《古蘭經》中所描繪的魔鬼的家園。
從海雷丁緊縮的眉頭中就能看出內心的不快。奧斯曼人有崇信天象的傳統,他們認為天氣變化、星象以及種種新奇的「意象」與人的命運和國祚緊密相關。海雷丁作為蘇丹親命巡視帝國北方邊境的大臣,初到任就遇上這種情況,不快是理所當然的。
空氣濕度越來越重了,海雷丁所在的小山包上遍佈高大的闊葉樹,墨綠色的樹葉上不知不覺間已掛滿了露珠。雖是早春,寒冷仍籠罩在這片土地上,不捨退去。可在這種天氣下,海雷丁一行人卻感到了相當的悶熱,但他們還需要趕路。雨沒有任何預兆地下來了,伴隨著岑岑的涼風。「帕夏,您的袍子。」副官阿里·穆拉德貝伊遞給海雷丁一領長袍。
「這是天降甘露啊!」海雷丁披上長袍,用以遮雨。他轉過身,對自己的隨從們說:「前面不遠處就是盧斯卡納城,抓緊趕路!」
雨越下越大了,風亦愈來愈疾,狂風捲著暴雨,使它們橫斜著劈砍到人們臉上。雷鳴滾滾,電閃白耀,交錯發威,它們逐漸地交融在一起,一道劃過天邊,似是都要把天撕裂開了。海雷丁的戰馬驚得放滿了腳步,在戰場上闖過千萬道的戰馬終究也抵不住安拉的怒火。一道通天的閃電劈下,這道雷柱徹底將天空照白了,大地也被轟震地顫抖不已。當那驚人的白晝消逝之後,大地仍震顫不止,且愈加劇烈起來。
「安拉!是大地動。」海雷丁慌忙揮起了馬鞭,馬鞭在空中舞繞三週後,馬才緩過神,飛奔起來。在大地崩裂的轟鳴巨響中,海雷丁聲嘶力竭吼道:「快走,前面就是平原,現在待在林子里不安全!」
馬隊疾馳,週遭的樹木不斷倒下,樹枝相掛,樹干傾倒,野獸驚吼,鳥雀慌飛,各種荒蠻之聲混雜在一起,雜亂無章且驚心動魄,恍如滅世絕罰之日,又如創世重組之時。深幽狹長的裂紋從山腳蜿蜒又決絕地延伸到曠野上,仿佛世界已經走到了盡頭。海雷丁一行人剛抵達曠野,就係數翻身下馬,倒伏在地上,蜷在自己的馬匹旁。隊伍中的艾里奇毛拉不斷地背誦《古蘭經》中的詩句,一刻不停。眾人的祈禱聲漸漸變為哀鳴,他們喊著真主的名諱,發自內心,歇斯底里地喊著,懇求真主平息自己的怒火。
真主最終還是放過了他們,沒有繼續蹂躪這群可憐的奧斯曼人。大地重歸平靜,可雨仍在下,風仍不停地怒吼,撕扯著週遭的一切。海雷丁從地上爬起來,向四周望去。這里簡直是一片狼藉,無數土塊石礫被翻了出來,盤虯的樹根暴露在空氣中,樹木東倒西歪的,所幸他們的人員並無大礙。海雷丁嘆了口氣,策馬揚鞭,頂著暴雨繼續趕路去了。
海雷丁到達盧斯卡納城下時已經幾近傍晚了,路上的泥濘嚴重影響了他們的速度。他們在這里看到了更為淒慘的景象——城牆已塌成土堆了,城內沒有一棟房屋是完好的。他們到達時正趕上餘震。此時,城中最高大的建築物——城主的官邸坍毀成了瓦礫。海雷丁抬頭凝視著,大地晃動得越來越厲害,各種大小不一的碎塊從官邸的外牆上震了下來,外牆完全剝落後,僅剩下的骨架也沒能支撐多久,在接連的晃動下轟然倒塌了。這一過程是在極短的時間內發生的,官邸倒下後粉碎成的齏粉彌漫成的塵埃瞬間籠罩住了整座城。也不知是猛烈的地震導致了它的坍塌,還是它的坍塌才是誘發地震的原因。但不論如何,這場面都太震撼了,海雷丁的隨從們都被嚇得癱坐到了地上,盯著那本該被宏偉建築遮蔽的天空。海雷丁還能站著,只不過徹底懵住了,在他眼中,剛才那一幕有如奧林匹斯山崩塌於面前般震撼。
「帕夏,海雷丁帕夏!」海雷丁被這突如其來的聲音拉回了現實,他環顧四周,卻不知是誰在喊他。
02
盧斯卡納城城門口有塊不小的石頭,有個衛兵模樣的人盤坐在上面。他身著滿是塵泥的布袍,頭上軟帽垂下,同一道而下的頭發遮住了半邊臉,另半邊臉則深藏在陰影中。他左手環抱著一根長矛,右臂上紮著一段繃帶,血跡斑斑。烏雲終被撕開了,卻只有昏沉的殘陽涌進來。落日餘暉照在那名衛兵身上,照在他身後本是盧斯卡納城的廢墟上,照在他週遭的瓦礫水窪上,水映照著殘陽,像極了鮮血。
海雷丁半張著嘴,想說些什麼,卻什麼也說不出來。
穆拉德也緩過了神來,他走向那衛兵,臉上帶著些復雜不清的表情。那衛兵抬起頭來,好像是聽到了腳步聲。他看上去只有十幾歲。穆拉德艱難擠出點笑容來,說:「小衛兵,我是帝國第五維奇海雷丁帕夏,麻煩你去……」
「是的,我就去……」小衛兵的聲音有些沙啞,虛弱且不清,但從他的動作來看,他還有些力氣。衛兵一下子從石頭上蹦下來,轉眼就不見了。
不一會兒,一位衣著像是長官的人跑了出來,他身上遍是灰塵,看起來很是狼狽。
那人看到了海雷丁眾人,心里卻泛起了嘀咕。說實話,這是很正常的形象。就看為首的海雷丁,外袍上沾滿了污泥,頭巾上已看不出白來,還在不斷地淌著水,實在是不像一位炙手可熱的維奇。海雷丁笑了笑,脫下外套,露出一身整潔的綠衣。綠衣本沒有什麼,但海雷丁腰上還別了一張金弓,上面雕滿了真主箴言。那長官看到這弓便慌了神,緊忙跪下道:「下官盧斯卡納城城主奧爾汗·花剌子模,恭候大人多時!」
海雷丁笑了笑,將花剌子模從地上扶了起來,然後向他的隨從們招了招手,示意他們一道過來。在最後一抹霞光從地平線上消逝之前,海雷丁眾人踏進了這座曾是盧斯卡納城的土丘中。
進城後,海雷丁只是從侍從那里換了卷干頭巾,還沒去換衣服,就問起了受災情況。
「這很顯而易見,」花剌子模舉著火把,四周照了照,「糟糕透了。」
正如花剌子模所說的,情況不容樂觀。即使是在主街道上,也積了一大層厚厚的塵土,大小不一的碎石塊、碎磚塊半埋於其中,兩旁盡是廢墟,不時有呻吟聲從中傳出,然後搜救隊就會循聲下鏟,把里面半死不活的人刨出來。塵土味與血腥味混在一起,籠罩在這片狼藉之上。夜晚並沒有使這片土地歸於寂靜,相反喧囂充斥了黑夜。不管是官員還是市民,士兵還是僧侶,但凡還是有力氣的,都在其所能翻開一層又一層倒塌的牆體,試圖盡快救出更多人。
「城里還有完整的建築嗎?」海雷丁從懷里抽出一根蠟燭遞給穆拉德,穆拉德接過,裝進燈具里,邊點燃著邊說。
「有,城里的清真寺還算完整,那地方曾是個天主教堂,有相當好的抗震結構,聽說以前還是羅馬人的神殿。」
「對了,」海雷丁岔開穆拉德與花剌子模的話題,轉而說道,「城門口那位是個衛兵吧?」
「是啊,但他還沒到入伍年齡,只是臨時徵召應對災禍的。」
「看來情況不是一般地糟糕。」
「是的,帕夏,大部分士兵都被派去搶救市民了,但仍舊有很多人被埋在瓦礫之下。」
海雷丁聽到這兒,皺了下眉,緊接著問道:「你的哨兵有沒有從對面帶來什麼消息?」
「哨兵?」花剌子模疑惑地看了海雷丁一眼,卻看到海雷丁的眼里充滿了焦慮,並透出不少令人怖懼的慍怒來。海雷丁沒有擺出任何表情,但在淒冷白暇的月光下,他毫無表情的臉顯示出了異常的肅穆,比任何其他的表情更能震碎人心。花剌子模低下頭,不敢看海雷丁的臉,更不敢與海雷丁對視。
「花剌子模貝伊,你作為盧斯卡納城的城主,應該比我更清楚,這里是——前線!十里之外就是奧地利的邊城!帝國為什麼派你來做城主?對面那群虎視眈眈的奧地利人,你就如此視而不見嗎?身居此位,你就從沒有考慮過帝國的安全嗎?」海雷丁的聲音聽起來有些奇怪,好像聲音被堵在嗓子里,就如同泉水被堵塞在泉眼之下,翻騰不出的感覺。實際上,海雷丁是在極力掩飾壓制自己的聲音,免得它們與自己的怒火一同噴湧出來。在現在這種境況下,怒火對形式沒有任何助力,甚至會有反作用,只有保持理智才是上策,海雷丁也深諳其中道理。
「下……下官這就去……這就去辦……」花剌子模的聲音震顫起來。
「慢著,」海雷丁從懷里掏出三卷羊皮卷軸來,遞給花剌子模,說,「你把它們交給最近的三個內地要塞。」
03
海雷丁從穆拉德貝伊手中接過煤油燈,燈光很暗,但勉強也能照亮道路。夜色愈來愈濃,海雷丁卻感不到絲毫疲憊,一點兒睏意都沒有。晚風愈發凜冽,從潮濕的衣服上滑過,海雷丁也不禁打了個寒戰。
「該休息了,帕夏。」穆拉德提醒他說。
海雷丁停下了腳步,回過頭來看著穆拉德,怔了一小會兒,說:「走,咱去清真寺看看,興許還能趕上最後一次禮拜。」
清真寺的情況確實比其他地方要好很多,但也不容樂觀。海雷丁到的時候發現清真寺周圍的四根伊斯蘭樣式的塔柱倒在地上,摔成了好幾段,週遭也盡是碎磚爛瓦。「這兒的情況也沒有多好。」說著,海雷丁從門口碎石堆上跳進了清真寺里,幾顆帶著火星的油滴從油燈中灑了出來,落在地上,發出滋滋的響聲。但這沒有引起什麼人的注意,因為清真寺里實在是太嘈雜了,幾乎所有的傷員都被安置到了清真寺。毛拉們跑來跑去,救治傷員,忙得不可開交,自然也沒有意識有什麼人進來了。
海雷丁從牆邊拿起一卷波斯絲織毯,展開,平鋪到地面上。他簡單地朝聖地麥加的方向做了個禮拜。當海雷丁做完禮拜,將絲毯重又捲起來時,之前一直與他隨行的艾里奇毛拉才發現他。「哦,帕夏,您怎麼來了?」艾里奇驚叫道。海雷丁沒說話,只朝他做了個手勢,示意他不要驚擾到其他人。然而事與願違,人們的目光都向他聚攏過來了。
艾里奇毛拉朝其他人拜了拜手,讓其他毛拉們安心工作。「這麼晚了,您還不休息嗎?」艾里奇問道。
「你不也還沒休息嗎,毛拉?」海雷丁捋著鬍子,微笑著反問道。
「也是,主要是傷員實在太多了,根本忙不過來,還不斷有傷員被送進來,很多毛拉都是負傷上陣——您有什麼指示嗎?」
「我准備找個地方休息一下,天這麼晚了,我本不願去去打擾你們。」
艾里奇朝大殿深處指了一下,說道:「大殿後面有些空房間還可用,不妨我帶您過去。」
「哈哈,不再添麻煩了,你先去忙吧。」他拍了拍艾里奇的肩膀,「別給首都的毛拉們丟臉。」
大殿里側的甬道狹長昏暗,牆上的燈都滅干淨了,地上積了一層薄塵土,大概是大地動發生時從天花板或牆壁上脫落下來的。海雷丁在甬道盡頭停下了腳步,推開一扇老舊的木門,提著油燈向房內照了照。這房間看起來還不錯,只是坍了一個屋角,牆上的水漬還清晰可見,月光從那個屋角投射進來,跟著進來的還有一角兒繁星。這屋子足夠遠離住滿了傷員的大殿,頗為寧靜。海雷丁對這里很滿意,只有在僻靜的環境里,他才能潛心處理公務——喧囂只適合作為料理戰事的作料。海雷丁拂去桌上的灰塵,鋪展開一張羊皮紙。鵝毛筆插在墨水瓶里,擺在桌角,也不知道是誰落在這里的。
「我從首都帶來的咖啡豆。」穆拉德貝伊提著油燈進來,遞給海雷丁一杯咖啡。
「這可是好東西,」兩人碰了杯,「我總覺得少帶了點什麼。應該帶些咖啡的。」
就如同歐洲人習慣於在戰前飲酒,奧斯曼人更鍾情於咖啡。作為帝國邊境戰場的常客,海雷丁自然清楚咖啡的好處。通宵已是尋常事,他習慣於用咖啡來提神。
「夜很深了,帕夏,您應該注意休息。」
「這時節可容不得我休息,穆拉德。」
穆拉德聳了下肩,在桌案一角輕放一小包咖啡豆,然後把自己借來的提燈提走了。
太陽總喜歡出人意料地跳出來——當海雷丁吹滅了自己的油燈,才發現天已經亮了。他伸了個懶腰,將杯底兒的一小層咖啡飲盡。出門時,他發現水已經有人幫他打好,盛了一盆放到了門口的架子上。他撩起水來,擦了下臉,使自己看起來精神些。
比起昨晚,清真寺正殿里很安靜,大多數人還沒有醒來。海雷丁在寺外轉了轉,在陽光下,這座城更狼狽了。城中幾乎沒有什麼建築物了,全是一座又一座的小土丘,隨處可見倚靠這土丘沉入睡夢中的士兵。
「海雷丁帕夏!
海雷丁聽到有人叫他,他剛一回頭,就看見一匹高頭大馬赫然衝向他的眼前。
馬背上那人一手緊勒著韁繩,一手遞給海雷丁三張羊皮紙,說:「帕夏,您的信。」
海雷丁接過信,翻看了兩眼,但信里的消息並不怎麼樣。海雷丁抬起頭來,才發覺騎在馬上那人原來是花剌子模貝伊——他已下了馬。
「沒什麼好消息,」說著,海雷丁隨手將三張信捲了起來,揣進懷里,「最快也要三天才能到。」
「真的會有戰爭嗎,帕夏?到現在都還沒有哨騎傳來消息。」
「防人之心不可無,貝伊!」
海雷丁向東遙望,他看不見聖索菲亞清真寺的穹頂,只能看到那地平線上,浮在樹梢、山巔與天壤交接之處的層層金黃。
04
喧鬧、歡騰!無論如何窮盡言語,塗盡油彩,都無法描繪此時的盛況。帝國第七維奇爾薩·海雷丁身著金袍,頭上插著一根孔雀尾羽。他引著加尼沙里軍團進入首都伊斯坦堡,一展碧綠大旗開道。剛進迪穆里埃門,一陣低沉的號角聲升了起來,民眾的歡呼聲瞬時爆發了出來。明晃的彎刀、齊整的火槍,潔白的禁軍制服反射著刺眼的陽光。要是擱在前幾年,海雷丁還會興奮一下,但帝國年年都贏,他也年年都在這條道上走,年年都看這樣的儀式,興奮勁兒也就快要減沒了。他臉上幾乎一點表情都沒有,但也會不時掛上微笑,伴著民眾一陣又一陣的興奮的呼喊聲,他也會朝兩旁的人招招手。只不過他的笑容所包含的大多是應付,僅單單浮於臉上,而非發自內心。
海雷丁的副官帕蒂瑪貝伊穿著孔雀石般翠綠的外衣,軟帽徽上別著一根鸚鵡翅羽。他跟在隊伍的側翼,警惕地提防著人群,排查著可能會引發惡性事件的微小誘因,錙銖必較。從人群里突然朝他伸出一隻手,好像拿著什麼東西。他下意識手摸刀柄,剛要拔刀,才看出來那手里的東西是一封信封潔白閃光的信。他接過來查看,信封上沒蓋火漆印,看筆墨像是剛剛寫就的。帕蒂瑪向人群中望瞭望,卻已經看不見那雙手,更無法找出遞給他這封信的人是誰了。他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一手把它塞進囊橐里,一手揚起馬鞭,直奔回海雷丁的身旁。
「帕夏。」穆拉德對海雷丁耳語道。
海雷丁停止了向人群回禮,恢復了一臉嚴肅,反問道:「什麼事?」
「不好的消息。遠征俄羅斯的軍隊敗了,第三維奇被貶為迪穆里埃總督。」
「艾哈邁特老師?」他緊皺起眉來,面色顯然變得更壞了。
「嗯,而且大維奇作為遠征軍的總指揮,即日論罪問斬。」
海雷丁脊背一陣發涼。他與大維奇倒是沒什麼交情,但他在還不是維奇時,在第三維奇艾哈邁特帕夏手下做過事。艾哈邁特在老蘇丹時代就身處高位,征戰四方,未嘗一敗,自然威望頗高。但新蘇丹上任後幾年,他就受到了不少冷遇,而海雷丁則成了蘇丹身邊炙手可熱的人物。但海雷丁與艾哈邁特的私交依舊不錯,這位軍政新星的一身本領有不少是從這位戎馬一生的老將軍手里學來的。
當他從心事里回過神來的時候,他早已不知不覺地走進了蘇丹的大殿門前。自然光沿著大殿牆壁邊緣的窗戶投射進來,卻止步在窗沿,對潮濕昏暗的大殿無甚裨益。蘇丹坐在黃金雕飾的寶座之上,把玩著一把鑲嵌著華貴寶石的短劍。敞開的殿門投射進刺眼的陽光,打破了大殿中光暗的平衡。
蘇丹下意識抬起頭來,看見海雷丁走了進來。他掛上一臉的笑容,將那把短劍朝海雷丁伸了過去。「按照約定,這柄羅馬短劍就歸你了!」
海雷丁在蘇丹的寶座前,單膝跪下,雙手捧過短劍。
蘇丹站起身來,撫摸著他的黃金寶座,看著上面鐫刻著的箴言,說:「土地、金錢、榮譽、戰馬、寶劍、舞女,世間之人所一生渴求之物你早已擁有,我甚至已不知何種賞賜配得上你的功績了,」蘇丹沒有等待海雷丁回應他,接著說道,「但朕又轉念一想,如今你依舊位卑,朕以為汝之功勛應當……」
「陛下聖意,臣心已領之,」海雷丁打斷了蘇丹,「然臣以為,臣威望低微,難以服眾;臣資歷尚淺,德不配位,萬不敢妄攀高位。」
「帕夏,你我同年同輩,我可即蘇丹之位,統千里沃土,你何不能高任……」
「陛下承接祖輩神聖之血脈,宣揚真主之道,橫溢之才華,萬不是我等所能比肩的。」
「唉,」蘇丹嘆了口氣,坐回到他的寶座上,「你厭倦了?政治與殺戮也確實令人身心俱疲。」他看著海雷丁——他的摯友、帝國最年輕的將軍,說:「那你又要朕怎麼辦?難道要朕去迪穆里埃,將老艾哈邁特請回來嗎?除了你,除了你……」
海雷丁感覺蘇丹高傲的內心一片又一片地碎而剝落。他已經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走出大殿的了,只記得第二天是慶功宴。在這一天,海雷丁還是被提拔為了第五維奇,並被賜予馬尾旗,代蘇丹巡視帝國北疆。夜晚,他躺在床上。慶功宴上的一切在他腦海中僅剩下易碎的環境——天籟的歌喉、婀娜的舞姿、甘美的羊排已化為泡影。他閉上雙眼,在黑暗中靜聽著門外噴泉不停歇的水聲。
嘩啦——嘩啦——
05
噼里啪啦的水聲愈來愈大。海雷丁從黑暗中起來——他不小心在大帳中打起了瞌睡。即使是他,也支撐不住如此長時間的熬夜。案頭的燭火略有些刺眼,海雷丁皺著眉,起身撩開幕布,一道從天而降的水瀑映入眼簾。穆拉德貝伊正直挺挺地站在帳外,全身都濕透了。
「你站在外面幹什麼?快進來!」海雷丁大喊起來——雨聲實在是太大了。
穆拉德站在外面把軟帽擰干,才走進來。海雷丁遞給了他一張毛毯。
「果然如您所料,奧地利的軍隊早就到了,只不過他們僅是在那邊扎了營,還沒有其它的動作。」
海雷丁拿出望遠鏡,朝奧地利人的營地望瞭望,道:「那是群農民啊!」他望到了奧地利衣冠不整的士兵手握著鋥亮的草叉。但他並未因此有所鬆懈,一是因為在戰場上輕敵是最愚蠢的行為——人的潛力在戰場上的爆發力是無窮的,哪怕只有一個人,他對生存的渴望所迸發出的力量,是普通人所無法相抗衡的,正所謂是置死地而後生;而是因為他手里的也是一群新兵蛋子,最趁手的武器不是干農活用的草叉鋤頭,也就是屋後劈柴用的早就捲了刃的柴刀,以及不知從哪里翻出來的銹跡斑斑的鐵錘。盧斯卡納城里的士兵在忙著四處搶救傷員,而其它要塞里的援軍也還在日夜不停地奔襲而來。對海雷丁來說,如此捉襟見肘的形勢就如同帳外的瓢潑大雨一般,不停地衝撞著防洪大堤,在不堪重負之刻,龐然巨物也會頃刻倒塌,已化作洪水的江河奔流席捲大堤,將城市撕開一道狹長幽深的裂口,使生靈塗炭。但海雷丁手里僅有的底牌卻只是一群貨真價實的民兵,甚至沒有獲得過一天的正經軍事訓練。這群人是海雷丁讓花剌子模臨時徵集來的。帝國是一台延續了上百年的高效的戰爭機器,已將民眾的好戰情緒激發到了令人難以想像的瘋狂的成都。就是由此,花剌子模才能在短短數小時以內就給海雷丁召集到一支頗具規模——雖說粗製濫造——的軍隊。
在看到對面的軍陣後,海雷丁愈加厭煩。帳外雨聲漸漸停歇了下來,曾被遮掩的戰歌聲逐漸響亮了起來,也不知道是誰開的第一嗓,但聲音在他的指引下愈加高亢。這場突如其來的大雨並未沖散士兵們高昂的鬥志,卻徹底將海雷丁心里僅剩的幾個火苗又澆滅了幾個。
「會很慘烈嗎?」穆拉德邊裹起幹頭巾,邊問道。
「先把你的袍子換下來,軍隊生活最怕生病。」海雷丁瞟了一眼穆拉德,這位貝伊在代替帕蒂瑪貝伊之前,一直在首都做書記官之類的文員工作,從未見過戰場。他在穆拉德的眼神中讀出了恐懼,繼而說道:「你不瞭解戰爭,貝伊。戰爭就是流血受傷與死亡,沒有任何一場戰爭能逃過此種宿命。然而,我們的士兵能在戰前握起刀,卻不一定能在戰時握緊它。他們看似士氣高昂,其實是帝國蒸蒸日上罷了。他們將帝國的功績妄自加在自己身上,誤認為自己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所向披靡,百戰不殆。但若要期待他們——從未見過戰場,從未學過殺人的人——在短兵相接之時,拿出應有的勇氣,根本就是虛妄之事。面對死亡,他們若能落荒而逃,便是餘勇可賈之人,但大多數人只是兩股戰戰,動彈不得,以一種絕望之情面對它,連逃跑的勇氣都沒有。」
穆拉德聽著,把衣服換好了,臉色也愈加干癟混亂,在深深的絕望之上,還有喜悅與心安流於其上。
海雷丁捋著胡須,眼睛快眯成了縫,看著一張帝國的地圖嘆氣。
雨徹底停了,嘈雜的雨聲已無蹤跡,混亂而吵鬧的歌聲占了主場。
06
沒有戰旗,沒有號角,戰爭便這樣匆匆忙忙、毫無榮譽可言地爆發了。兩方打頭陣的是一排「重步兵」,他們握著柴刀,舉著盾牌——一塊塊粗陋的木板,天知道它們之前是哪家的門板,哪家水缸上的木蓋——列成凹凸不平的陣線,組成兩道斑駁破敗的盾牆。長矛手的草叉尖從盾牌之上伸出來,而兩三排之後的士兵便只有木棒防身了,也許誰口袋里還放著一把小刀,但能不能准確地刺進對手的喉嚨里,並保證自己五指具存,就只能看天意了。這些「輕步兵」們的作用也就剩下充充場面,壯壯聲勢,比比誰嗓門更大,罵人更狠了——只是奧斯曼人不懂德語,奧地利人也不懂土耳其語罷了。
兩軍相對,正若仇人相見,分外眼紅,互相唾罵,卻沒人想第一個動手。伴隨著直上雲霄的原始怒吼,兩邊的陣線開始慢吞吞地挪動起來,如同兩頭衰老的大駱駝在做爭搶配偶的決鬥。每個人都更想要表現得像一隻兇猛的、只為撕開對手的喉嚨、暢飲其動脈中汩汩血流的蒼狼,但也僅僅是表現而已,誰都清楚在這層狼皮之下的是怎樣的一隻羊。
兩軍已經相當接近了,而他們挪動的速度也越來越慢了。
砰!——一聲巨響突如其來,兩邊的「重步兵」同時停下了腳步,並一齊蹲下,齊刷刷地將自己蜷縮在「盾牌」之後。一名奧地利士兵戰戰兢兢地盯著自己腳下的土地,一顆鐵丸嵌在泥土中,還在滋滋地發著聲響,散著白煙,那是高溫物體急速冷卻下來時產生的現象。
奧斯曼人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一個「輕步兵」探出頭來,想要搞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他剛一抬頭,就正瞧見海雷丁端著一把火繩槍,瞄著奧地利人的軍陣,槍口正冒著一縷淡灰的煙。瞬時,所有人都向海雷丁望去,整個奧斯曼軍陣都沸騰了起來。海雷丁的馬被突如其來的震天高喊所驚,打攪到了海雷丁欣賞自己的槍彈在樹上劃出的軌跡,不得不去分心安撫它。
奧地利的卡爾·馮·皮爾森將軍也騎在高頭大馬上,身著閃閃發亮的哥德式全身板甲,與參差不齊、殘破不堪的奧地利軍陣格格不入。皮爾森將軍趁著奧斯曼人鬆懈之機,抬起一張十字弩,瞄著奧斯曼的軍陣就是一箭。弩箭正中奧斯曼人的盾牌,箭頭嵌進一寸,從盾牌內面探出尖頭來。舉著盾牌的奧斯曼士兵被嚇得癱倒到了地上。奧地利的軍陣也就同樣沸騰起來了。「將軍!國王!上帝!」他們開始朝對面高喊,拿草叉杵著地,就像執著長戟一般。
「帕夏!蘇丹!安拉!」奧斯曼人怒吼了回去。
於是兩邊你來我往,鋒芒畢露,卻沒人再前進一步,直到傍晚,各自收兵。
之後幾天,大致也是這樣,都是連續的罵戰,一場比一場激烈,卻從沒有進一步升級為流血的衝突。戰爭女神恐怕從未有如此溫柔過。恐怕這也是所有人都喜愛的戰爭女神下凡的形式,既能表明自己的忠心與勇武,又能維護自身性命之無憂。
突有一天夜深,這天的夜漆黑得異常,只有月光灑下,繁星們都隱起了身,不由得令人忖度是不是有個頑皮的天使打翻了天上的黑漆桶。
海雷丁剛吹滅了燈,躺在床上。他沒心情睡,卻並不擔心第二天的戰局,他在等,估摸著時間也差不多了。
帳外漸漸喧鬧了起來。海雷丁撩開帳門,向外看去。外面有一張熟悉的臉,套在一頂鐵頭盔里。「帕蒂瑪!」他走了出來,向帕蒂瑪貝伊招了招手。
帕蒂瑪恭敬地摘下頭盔來,向海雷丁走過去。「許久未見了,帕夏。」
「許久未見了,你還好嗎?」
「好得很。我收到了您的信後,就星夜兼程地趕來了。」
「就你一支部隊來了?」
「我和另兩位貝伊在盧斯卡納城回合後,就一起馬不停蹄地奔到這兒來了。」
「好了,但那都是些軍需品啊,您要拿來做什麼?」
「搬上東西,現在就出發。」
串串火光在山坡上閃爍,道道火舌從兩側聚攏過來。奧斯曼的火映出來銀亮的騎士板甲,奧地利的火光照出來深灰的長袍鎖子。相對而視,無人與言,只在心中暗驚。遵守命令,沒人拔出腰間的利刃,而都在默默做著手頭的事——把一箱箱的麵包、醃肉、咖啡、面餅、香料、蜂蜜、工兵鏟和鎯頭齊齊碼在地上。海雷丁與皮爾森見了面,在火光中相互握了手,兩人的雙眼都佈滿了血絲,板著臉,什麼話都沒說,各自收軍,匆匆離開了。
清晨,半輪太陽伏在地平線上,投下暗紅色的光來,漫蓋了大地。在奧斯曼與奧地利兩大帝國的邊境線上,一道血紅的長牆立了起來。從盧斯卡納山上望下去,那長牆頗似一位年邁的聖人,佝僂著腰,敞開雙臂,等待著他中意的、眾多的、平凡的門徒們靜靜走來。
註:
來源:機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