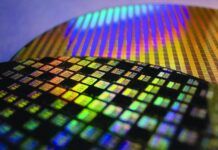01
我實在是跑不動了。
我雙手撐著大腿,彎著腰大口的喘息。寒冷乾燥的空氣,讓我的喉嚨與氣管像撕裂一般的疼痛,忍不住一陣陣的咳嗽和干嘔。
不遠處的女人看起來絲毫沒有收手的意思。白色的職場正裝髒亂不堪,頭發在頻繁的廝打過程中變的猶如一堆雜草。通紅的眼睛布滿血絲,晃著步子一步一步朝我走來。
「別……別追了,林老師……停……」我的左半邊袖子被徹底扯掉,右邊的脖子被撓出三道駭人的傷口,不停被汗水的鹽分所侵染,持續刺痛著我的神經。估計她的手指甲里還留著我好些皮肉。
我略微瞟了眼四周,好像已經到了郊外鹽廠的河堤附近。四下已經沒了人影,一旁的小河溝大概匯聚了整個城市的下游污穢,散發著濃烈的氨水氣味。
恍惚之間,眼下的場景就像是一個夢魘。我依舊盼望著什麼時候自己能夠重新醒過來。
現在是什麼時候?我抬起左手腕看了看時間,星期五,晚上八點過一刻。今天是月底的雙周末假期,按理說這時候我應該已經吃過晚飯,攤在家里的沙發上閒散地放空著。
本該如此。
事情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出岔子的?從學校的山腳下開始,路邊的行人瘋了一樣攻擊我?不,快要走出學校門口,身邊的學生看我的眼神就已經不太對勁了。
就像是看待臭蟲一樣,充滿了敵意,還有那種強烈的距離感。
有那麼一瞬間,空氣就好像忽然凝結了起來。接著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佛焊接在了我身上。
我略顯詫異地查看自己的身上是不是糊上什麼髒東西,朝著門衛室方向的藍色玻璃窗的反射影子反復查看。而後門衛室的年輕保安重重地拉開了窗子,充滿警惕地瞪著我,就像發現了一個怪物。
不遠處樹蔭下,剛剛還微笑著道別的一個同班住校生,也停下腳步愣愣地看著我。
門口一些正准備出門的自行車全部都停了下來,統統伸出左腳單足斜踏在地上佇立著。旁邊的小車也全部搖下車窗,撇過頭,里面的任課老師和教導主任的臉上表現出十足的驚訝。
如同列方陣一樣,所有人的目光都整齊劃一的瞄準了我。
冷靜。冷靜。
進入這所高中近兩年,我應該是盡可能的貫徹了低調與和諧的處事之道。不惹事,不出頭,不掉隊,不拔尖,不十分惹人喜歡,也一點不令人討厭。
可眼下的陣仗多少有些超出自己的常識,在這樣的場景之下我甚至不知道該如何擺動自己的四肢,或者怎樣展現自己的和善表情,來表達自己的歉意。或者說,能不能暫時給我一個地縫,讓我悄悄離開。
但長久的沉默讓這些祈禱顯得好像是不可能的,於是我叮囑了眾目睽睽的壓力,加快了腳步朝外面走去。
之後不懷好意的推攘就開始了。
事實上的擁擠讓我不得不從人堆里經過,從縫隙中找尋出路,更不要提幾乎所有人都駐足不前的情況。但是一旦稍微接近,像是本能防禦一般,對方的一隻手就將我用力的推開。力道之重,差點讓我摔倒。然後因為推攘,我被推到了其他人的身邊,於是又是另一次的用力推攘。
要是在平常,這已經足以激起我的本能反應,會很快的展開自衛式的憤怒和反擊。可是如今的場景難免有些過於詭異,或者短期內的驚愕之中,逃走和遠離當下的不合理,才是自己認為唯一合適的做法。
在歷經幾次近乎桌面彈球般的待遇之後,我迅速站穩了腳跟,同時藉助推攘的力量,試著往人群之外的地方快步走出去。
之後好像有過一段時間的緊張性盲視,大概因為專心的找尋著人少的岔道和出路,忽略掉了大部分的細節。我記得是慢慢地出了校門口,可一抬頭,就發現自己的噩夢遠沒有結束。街道上的人不會為何,也開始「注意」到了自己。
死一樣的寂靜與凝視就像剛才一樣,迅速蔓延了開來。而且「輻射」的范圍還在擴大,正前方20米外開始駐足和停止說話的人開始越來越多。我回過頭,發現校門口附近的人,其注意力也依然沒有轉移。我依然是後方所有視線的核心。
如果人群的視線能在此時構成一個旋渦,那我就變成了圓心。
我停下腳步,大氣也不敢出一口。強烈的焦慮感開始讓我的理智趨於崩潰。
接著,所有人開始向我慢慢靠攏過來。我喊出一句「艹!」立馬撒開腿向著山腳下全力奔跑。
學校是建在半山腰上的,我幾乎是沿著公路的正中央進行著狂奔。路上的行人不斷「發現」著我,接著再迅速安靜下來。似乎我是一個急速移動的消聲器。
讓人不安的是,他們似乎開始產生出一種類似好奇的「熱忱」,向我不斷緩慢靠近。有些人甚至試著伸出了手,想要觸摸和牽拉。
在逃離的過程中,我本能地回過頭看了幾眼,發現遠去的人並沒有追上來。而正前方,這種「輻射」的范圍大概在20米左右。
前面的人在「醒過來」之後,面對我的狂奔與快速避讓,也沒有太多的反應時間。所以我算是躲過了大多數對我產生興趣的人群。
只有中途一次因為前面一輛轎車的急速停止,我被迫要靠近和繞過一個中年婦女,經過的時刻被忽然用力拉扯住,像蟄伏已久的捕獸夾子等來了獵物。
驚愕之餘,我短袖襯衫的袖肩立馬被撕開了一個小口子。我用盡全力撕扯,試著脫開了她的手。四周的人也開始瞪著我,朝我伸過手來。
「哇!!!」我叫出聲的時候,聲音就已經嘶啞了,大機率是聲帶的急性損傷。
後面和前面的小車,不約而同地搖下窗,里面的家長和副駕駛的女學生同時直愣愣地看著我。
在所有人的手都要攀附上我的軀乾的前一刻,我掙脫了束縛,撕開了袖子,也翹翻了女人的兩個指甲蓋。可是食指和中指的血淋淋似乎並沒有讓她感到痛苦,看著我的逃離,眼神充滿著疑惑。
幾次回過頭,我發現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或者說是唯一「正常」的事情。
我注意到後面有一輛白色的大眾POLO車,似乎一直沒有停下來過,成了後方斜坡公路上唯一正在緩緩向下行駛的車輛。
我一邊奔跑,一邊向後好奇的繼續打量它幾眼。好像只要它將經過的地方,行人和車輛都會紛紛避讓,給它讓出一條恰到好處的寬度。以至於它的行駛速度幾乎沒有收到任何的影響。
這原本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場景。可,當下閃耀的星星不是我嗎?後方近乎150米內的人群視野依舊全部都匯集在我的身上,甚至是身體的朝向。他們究竟是如何做到一邊背對著,一邊感知著後面的車輛,並且給出剛剛好的避讓距離?
在汽車完全沒有鳴喇叭,連看都不看一眼的情況下。
我的詫異像是瘋狂旋渦中的唯一理智,是溺水之人的稻草,收束著持續增長的瘋狂。
但這樣的關注好像觸怒了某種機制,我再次回過頭來時,前方的人群開始快速構建起一道大壩和人牆。大家的眼里好像開始有了明顯的憤怒?!
我全身的汗毛開始倒立,照這個速度沖下去,接下來的幾秒內,我幾乎會毫無懸念直接扎進前方由無盡人手組成的「荊棘叢」。
我依然處在半山腰,一旁垂直陡峭的老舊石階樓梯已經被封了有十幾年,並且修起了簡單醜陋的矮小磚牆進行阻隔,靠近公路的接口還被挖斷填埋了十幾米的長度。新時代的路徑,一直是傾斜盤山的盤山泊油路。
或許是潛意識里的抉擇,也或者是慌不擇路,在極短時間的糾結與四處觀察後,我朝著右側的山崖跳了下去。
事後想起來,這樣的舉動難免有些欠缺考慮。路面和下面的土地幾乎相當於一個近三層樓高的平台,是一個接觸地面之後,無法再度完好起身的高度。
但腳下迎接我的卻是柔軟疏鬆的泥土。
我意識到這是剛剛翻完的土,應該哪家阿婆自己私自圈出來的小菜園,還未播種,或者說已經播種,但是並未生長。
那這樣路邊的灰塵會不會太大?這樣子的蔬菜吃起來真的健康嗎?現在已經是春天了嗎?對,油菜花,不遠處有一片小油菜花,是陽春三月,三月底,這學期的第一個月假雙休。
我用力甩了甩頭,腳下因為沖擊力,踩出了兩個膝蓋一樣深的大坑。我一前一後用力把腿扯了出來,發現前方不遠處是一條窄窄的住宅石階。
不知是不是錯覺,有那麼一瞬間我確實是感覺到了某種被注視感的消散,上方的人群甚至於不再保持寂靜,開始「漏」出些許聲音。
不過隨著的我向著石階下面的大步狂奔,下方的視野被再次暴露出來。上方幾乎擠滿了路面的人群,渙散的視線再次重新「校準」在我的身上。稀疏的話音像是再次被按下了靜音鍵。
我甚至隱約能夠感覺到背部的燒灼。
前方是一個階梯拐角,進去之前,我回過頭,發現白色的POLO車稍微加快了行駛的速度。
向下的石階上有許多綠色的落葉,它們大多都還油亮有光澤,似乎生命力依舊。在向下快速跳躍式奔走之前,我恍惚地看著兩旁的樹木。是一種在家鄉很常見,但我從來叫不出名字的一種小葉榕。枝條上鼓起了大大小小的黃綠色的嫩芽小包,新生的嫩芽把老舊的葉片頂了下來。
奔走,下降。持續的緊張和劇烈運動,已經讓我的注意力變得像藤蔓一樣,想要攀附周圍的一切。
一路上並沒有其他人影,這多少讓我有些安心下來。未經打掃的石階,灰塵讓腳底的觸感有些打滑,好在這條下山的路坡度非常小,樓梯薄且寬闊。
自己被泥土包邊的白色球鞋,一邊向下「噠噠」踏著步子,一邊掉落下紅褐色的土渣。
樓梯轉過一個大彎,迎面而來的是一個領著菜籃子向上爬的一個阿婆。距離還很遠的時候,我們倆就不自覺四目相對了。
我的心頓時又提到了嗓子眼。
但她迅速的把目光又避開了,繼續低著頭,一邊唉聲嘆氣般地喘氣,一邊向上爬著梯子。
我心中頓時閃過一絲清明,放鬆下來的同時又升起了十足的疑惑。
前方不遠處是一個竹林叢的豁口,露出的水泥公路反射著橘黃色的夕陽光,一閃而過的幾輛車像是和剛才我經歷的世界毫無關聯。前面應該就是下山的出口,出去應該就是學校正下方的臨江公路。
路口前有一棟二層小居民樓,我在它的一扇玻璃窗前停下來,對著反光仔細查看著自己。
我並沒有變成一個怪物。不胖不瘦,稜角分明,眉毛像野草一樣濃厚。除了滿頭的汗水和疲乏的神情,我實在看不出自己身上的異樣。
難道剛才的一切只是錯覺?
汗水還未完全乾涸,體溫開始下降,氣溫也隨著時間開始回落,山間的風吹的我有點冷。在恍惚間,我走出短暫的避風港,繞過竹林叢,走出了山道。
02
不遠處是一個公交站牌,沒有站台,全靠稀稀拉拉站立等候的人圍出了一片區域。
我壯著膽子朝公交站牌下面走去,試圖慢慢靠近等車的人群。
最近的商鋪門面大約在200米開外,靠近斜坡泊油路的轉彎處。視野的最左邊是一顆橘黃色的太陽,把開闊的上遊河面照的波光粼粼。一座跨河大橋平直的立在上面,一頭連接著學校山坡的尾根,一頭連著這座城市的老城區。
車輛和步行的學生,從山腳持續地輸送到大橋上,似乎生活的節奏放鬆且平和。
站牌下的人好像沒有把注意力過多放在我的身上,其中一兩個還好心地側過身,給我讓出位置,大概是以為我要去看公交站牌的路線圖。
兩個交談甚歡的小學低年級學生,一個提著菜的大媽,幾個通勤模樣的成年人,有男有女。沒什麼不妥。
我狀起膽子向站牌底下的一個成年男子開口問話,「請問到南站能坐這路車嗎?」我指著站牌上的紅色數字5,問了一個我早已知曉多年的信息。
男子身穿黑色西裝,挎著黑色公文包,正低頭看著自己的手機,注意到我在向他發問之後,迅速答道:「對對對。」邊點頭邊指了指上面的文字。
「哦謝謝。」我長出一口氣,終於放鬆了下來。
我站在人群里開始放空。一時間不知道接下來該幹嘛。一種熟悉的現世之感短暫的驅散了緊繃的氛圍,空氣也顯得清新涼爽起來。
就在這時候,我左邊眼角好像涌進了什麼新的東西。只見那輛白色的POLO車重新駛進了我的視線。
我的右邊臉頰感覺到了些許的風,眼角瞥過時,發現一隻黑色公文包向我掄了過來。
我驚愕地朝後邊小幅度地閃避,頭部躲過了一波強有力的撞擊。然後才聽到了「嗡」的一聲,穿西裝的男子把包掄滿了一個圓弧,他站穩腳跟之後,轉過頭來盯著我的是一雙血紅的雙眼。
「我…艹NM的……」他的嘴巴打著哆嗦,面部扭曲著咒罵著我。似乎不可抑制的怒氣,從半分鍾以前還對我和善以待的陌生人身體里,開始噴湧出來。
他立馬拉開了架勢,毫不猶豫地准備進行下一輪的攻勢。我小步朝後退去,正打算逃跑,沒想到下一秒頭就被一團裝滿蔬菜菜葉的帆布包捶了個結實。
「狗雜種……」頭發花白的大媽,咬著牙說話時嘴角濺射出幾滴唾沫星子。我看著四周,全是充滿著「惡意」的血紅雙眼,每個人似乎都准備在下一秒鍾,直接朝我撲過來。
恐懼如潮水一般席捲了我。像一隻受驚的兔子,連逃命的呼喊都沒有,我朝遠離人群的方向拚命跑去。
拉開一定距離之後,不經思考,我朝後方無人的沿江公路跑去,試著拉出一條弧線繞過發狂的眾人。
但仿佛是「嗅」到了我的目的,跑在最前面的幾個男女,速度在短時間內被提升到了有違常理的地步。像是拚死要完成一項重要的指標一樣,他們的身體用一種極盡古怪的方式「奔跑」著,似乎為了盡可能夠到前方的「目標」,姿勢已經開始像橡皮筋一樣開始振盪和扭曲。
我的前方像是被迅速拉上的閘門,幾個人三步並作兩步,幾乎立即堵住了我的前方路線。他們隨即停止了奔跑,和後面繼續跟上的人,在我的前方圍成了一個扇形。
沒辦法,我只好朝背後的路折返過去。
過於詭異的場景,助長了越來越強烈的絕望和無助。我發現自己已經不再用力跑了,速度明顯降下來了很多。
後面的人也似乎收斂了一些憤怒和瘋狂,在後面用比剛才慢的多的速度朝我追趕。那幾個剛剛極速移動的男人和女人,姿勢開始有些一瘸一拐,像是腿部某部分出現了痙攣。不變的是和剛才一致的怨毒眼神。
我開始不受控制地開始小聲哭出來,崩潰的情緒開始侵蝕心智。
前面不遠處,在大橋路口對岸,白色的POLO車穩穩的停靠著。離白色小車和路口越近,我就越是隱約知道,將會發生些什麼事情。
白色小車的前擋風玻璃微妙地反著光,始終看不清駕駛位的人臉。它就像是一個事不關己的存在,冰冷而又疏離地看著我。我卻擰著眉毛,隨著吐氣,喉嚨發出求救無望般的嗚咽聲。
靠近大橋路口的時候,山腳下陸續走出的人群洪流也映入了我的眼簾。
如同預期的那樣,死一般的寂靜又開始重新鋪陳開來,一雙雙眼睛如同對焦一樣,再次把注意力放在了我身上。而與剛才不同的,是他們臉上開始泛起明顯的嗔怒。
我轉過身朝右邊的橋上跑去,有氣無力的向前拐動著身子,也不明白自己這麼做還有沒有意義。因為兩分鍾以內,這一干人一定會追上我。
我的手腳有些發麻,自暴自棄的情緒已經誘發了生理性的絕望體感。
別追了。
別追了。
別追了。
別追了。
「別追了!!!!!」一句大聲的吼叫從一片寂靜的背後傳來。
我轉過頭,只見一輛布滿灰塵的暗紅色大貨車從右邊的公路上,按著高亮轟鳴的喇叭沖了出來,迎頭直接撞在了橋上左邊的大理石圍欄。
圍欄被立刻撞碎成了白色的石頭花,石頭像下雨一般落在橋下的河面上,接連傳來「噗通」的落水聲。
貨車的頭部被欄杆暴露出來的鋼筋所攔住,輪胎在橋面留下筆直的漆黑剎車印,整個車身徹底橫在了大橋的路口,堵住了後面所有的人群和車輛。
我抬起頭,呆呆地看著一個年輕的貨車司機,在駕駛位上不住的抽泣,一邊甩著頭,一邊小聲重復著「別追了別追了」。
那種熟悉的松動感,又開始出現在了對面的人群里。透過大貨車左右兩邊的視角,我明顯看見了人群重新開始吵雜起來,注意力開始轉而集中在撞斷橋欄的大貨車身上。
我立馬開始重新奔跑起來,肌肉開始強有力的扭結起來,新生的機會讓腎上腺素如汪洋一樣湧起。我大概這輩子從來沒跑這麼快過,越跑越快,耳旁只剩下「呼呼」的風聲和「噠噠」的膠底鞋聲。
橋面上這時已經沒有了車輛,左右兩邊的人行道上只有零星的幾個人,但我並不怕他們。我好像知道我把什麼東西給擋在了身後。
學校山腳下,附近只有這一座大橋,那東西想過來,得左右各自繞10分鍾以上的車程。
期間我只會過頭看過一眼。白色的小車被擋在大貨車身後,暫時沒有重新起動。圍在一旁的人越來越多,他們的生活發現了新的熱忱。
03
逃跑的過程我已經記不清楚了,只是逐漸力竭時,才發現天色早已邁入藍黑色的昏暗。回過神來時,我發現自己已經跑到了市區西邊的一個,廢棄的商業樓盤區。
我記得這應該是快十年前的熱炒項目,但似乎大部分期待逐漸成為了尷尬。四周就像是一個被遺棄的荒蕪生態,人煙極其稀少。透過一閃閃冷清髒亂的玻璃門,隱約只能找到流浪漢借住生活過的痕跡。
總得來說,有人的地方就是不安全的。這是我目前最質朴的個體感受。一路上我試圖遠離人群,似乎害怕他們與橋那邊的某種東西重新取得聯系。
但不可避免的,一路上也始終和零星的人有著交匯。絕對無人的地方難以實現,這是大多數小孩還在戶外隨地小便的時期就明白的道理。
我走到一個類似於中庭的地方,找了一張背靠樹乾的黑色鐵質長椅坐下。身後的移栽樹木似乎從來不曾開出過新葉,也並沒有人真的關心它是否真的存活。長椅的黑色油漆已經銹蝕了大半,應該長時間並沒有人使用過,坐在上面有著大量細碎的觸感。
天色離白天顯得很晚,離開點亮路燈又顯得略早。盡管我不知道這附近的路燈是否還能正常通電。
我能回家嗎?不,就算是人稍微密集一點的地方都不能靠近。接下來該怎麼辦?我今晚上該睡哪兒?明天怎麼辦?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我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極度的疲乏,被無法有效抑制和轉移的焦躁所裹挾,我無法真的放鬆,也無法真的能靜下來想一些問題。
我的注意力開始分散,逐漸被大腿左邊鼓起的褲子包所吸引。
我掏出這個只有基本電話和簡訊功能的黑色塑料合約手機,卻發現早已沒電並自動關機。我才意識到最近的一次充電好像是在三天以前。
我仰起頭打算表演出一個無語嘆氣的姿態,卻突然感到一陣窒息的感覺。自己的意識仿佛被某種東西使勁擠壓成了一條直線。
就在我皺起眉頭,閉著眼打算仔細探尋這個感覺的源頭的時候,一陣難以忍受的疼痛,粗暴而且劇烈地席捲了我的大腦。
自己好像變成了一塊極其柔軟而且十分敏感的嫩肉,而有人正在用一根粗糲帶刺的木頭,貼合在上面卯足了勁的快速摩擦。我剛站起身,就瞬間跪坐了下來,痛苦讓我立馬嚎哭了出來,並迅速伴隨著噴射狀的劇烈嘔吐。
我幾乎能夠感覺到那種血肉模糊的「受損」程度,並非皮肉,而是更深層次的精神感知層面。劇烈的痛苦讓我失去了對身體的控制能力,隨之側身癱倒在了一旁,身體蜷縮著不住顫抖。
灰塵和泥巴的土腥味,和冰涼的瓷磚觸感,我的臉抑制不住的扭動和摩擦著地面。湧上來嘔吐物和胃酸,刺激著我的上呼吸道,試圖誘發出一定程度的哮喘。我感到自己馬上快要窒息了。
有人,在試圖殺了我。
不知道為何,此刻這份「惡意」正清晰無誤的傳達給我。我的腦海中開始浮現出之前發生的所有片段,發現似乎都能找到屬於這種「惡意」的一些味道。原來我一直都能察覺到那東西的存在,只是沒有任何經驗和敘述工具,能夠把它完完整整的勾勒出來。
太遲了……
可就在我以為自己就要死去時,一陣輕松,卻意外的從痛苦的間隙傳了過來。
在如同銼刀般瘋狂摩擦的木頭,與嫩肉的間隙之間,此時仿佛被鋪上了一片金屬的薄片,從而大大降低了它的摩擦力和粗糲質感。
金屬薄片?
不,金屬開始變得厚實,逐漸開始變成一塊有分量的鋼板。而且越來越光滑,上面甚至開始出現了塗滿均勻的潤滑油。
我睜開眼睛,疼痛的感覺立即消失殆盡。從極度的痛苦中解放,短時間以內給我帶了極大的愉悅與舒適的情緒。我知道這是腦子里的阿片類受體,和血清素在起作用。
我坐起身,吐出嘴里剩餘的嘔吐物,用衣服擦了擦嘴角。喘氣之餘,我發現那塊木頭依然在用力工作,頻率甚至比剛才還要快。
我默默用心感受著這個「意象」,試圖提防著它的下一輪變換進攻。
可是良久,它也只是在反復摩擦著那塊已經被墊了厚厚鋼板的地方,絲毫沒有改動位置的意思。是啊,為什麼只有一塊地方能有鋼板呢?隨後,那一塊鋼板如同生長一般,迅速包裹住了整個嫩肉,嚴絲合縫。我不用再害怕那條木頭了。
我的心情得到了莫名的放鬆,甚至直起了腰板,開始打量起四周,發現周邊似乎並沒有其他可疑的東西。
木頭還在賣力的工作,它和鋼盔的摩擦表面升起了一絲溫熱,再沒有傷害與痛苦,甚至有一絲絲的舒適和溫暖。有那麼一瞬間,我甚至覺得它有些過於木訥和愚蠢。
我開始有了一些不耐煩,試圖阻止它無意義而又鍥而不舍的惱人行徑。那怎麼樣才能讓它停下來?思考的下一秒鍾,我好像就碰到了這根木頭。
我有了手。
我順著木頭的輪廓迅速握緊了這根木頭,它好像被突然嚇到了一般,開始試圖掙扎。但它的力量好像有點過於孱弱,與其說是掙扎,不如說像是意思一下的輕柔蠕動。它先前粗糲的表面,在「手」里也像是變成了貓毛一樣柔軟。
我順著這根木頭向前探索,在末端的位置似乎有什麼東西在輕柔的推動和控制著它。
我一把將其抓住,卻發現那是另一隻「手」。
柔軟無力,比我細的多的一隻手。我甚至覺得它似乎有些病病殃殃的。它對我的折磨,它的掙扎,似乎都給人一種慵懶疲乏之感。但它與剛才的表現其實並無二致。
我稍微用力捏了捏它的手腕,發現軟得可以,里面的骨頭仿佛沒有鈣質,感覺下一秒就能像被煮的軟爛的蹄髈一樣,被捏的細碎。
它應該是感覺到了疼痛,開始進一步「升級」的掙扎。手里的木頭也隨之擺動,但是我隱約知道,它就是丟不開這根木頭。
怎麼能這麼笨呢?
沒有絲毫猶豫,我像個絕情的大人一樣,輕易把這條手臂捏成了碎肉渣。在它的剩餘部分離我遠去時,我能夠感覺的到它因為痛苦而持續的顫抖。
世界好像一下子清淨了許多。
我站起身,繞開自己的嘔吐物,朝著門面中庭的狹口走去,打算重新回到馬路上。
剛出狹口,一個白色的人影就從左邊悄然的浮現了出來。
「同學?」在感到驚悚詫異之前,一個輕量柔和的女聲把我叫住了。
「林老師?」我認出了這個穿成套白色西服的女人,她是上個學期給我們上心理健康教育的年輕女老師。應該是大學畢業剛不久,才被分配到我們高中。
「你是我們學校的學生吧?你剛剛沒事吧?我好像看到你倒在地上。」她的臉上透露出些許緊張和關切的神情。
「哦……沒什麼。」那門課本來就被打成形式主義,從六節課壓縮成了四節,所以嚴格意義上來說,我也只是上過她一個月的課,她居然能記住我這個普通學生,這似乎有點不可思議。
「林老師,你在這個地方做什麼啊?」我向林老師的方向走去,熟悉的、能和我正常對話的大人現在就是自己溫暖的避風港。
「我家住這附近,下來買東西,剛好路過。」她也向我走來,步伐有些加快。
「哦……」我剛想納悶說這麼個地方,附近居然也有超市,緊接著就發現,繞過林老師的肩膀,在狹口大門處的部分遮掩下,露出半截來,停靠的在公路邊的,那輛熟悉的白色POLO車。
洶涌而來的惶恐瞬間把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面前的女人離我只有一個手臂的距離。像舞台的打光一樣,我也瞬間看清了女人臉上的全貌。猶如鐵青一樣的面容,嘴角因為憤怒而急速的抽動。
下一秒鍾,她像張開爪子的野獸,向我撲了過來。並發出了我迄今為止聽過的最淒厲的嚎叫。
「哇!!!!!!!!!!」猶如砂石和禽類一般的嘶啞。
04
我實在是跑不動了。
我雙手撐著大腿,彎著腰大口的喘息。寒冷乾燥的空氣,讓我的喉嚨與氣管像撕裂一般的疼痛,忍不住一陣陣的咳嗽和干嘔。
不遠處的女人看起來絲毫沒有收手的意思。白色的職場正裝髒亂不堪,頭發在頻繁的廝打過程中變的猶如一堆雜草。通紅的眼睛布滿血絲,晃著步子一步一步朝我走來。
「別……別追了,林老師……停……」我的左半邊袖子被徹底扯掉,右邊的脖子被撓出三道粗糲駭人的傷口,不停被汗水的鹽分所侵染,持續刺痛著我的神經。估計她的手指甲里還留著我好些皮肉。
我也不記得一路上具體是怎麼,一邊逃避這個瘋女人的廝打,一邊慌不擇路的走到這片區域的。
從一開始的驚懼,特別是她如同女鬼一樣的抓撓和撕咬,帶給了我無與倫比的驚懼體驗,以及身體上的駭人的抓痕。可後來當我發現,這個女人似乎准備用類似撒潑打諢、孩童打架的招式,將我置於死地的時候,事情的某些方面開始出現了一些滑稽的色彩。
與其說是想殺掉我,這個女人更像是在自暴自棄。將自己的怒火與仇恨,用最直接的方式宣洩出來。
最初我擺脫掉她,與她拉開一定的距離之後,她曾試圖開著那輛白色的POLO車來追我,或者說是打算碾死我。但是在開出不到十米的距離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憤怒的失去了分寸,方向盤打過了度,直接卡進了路旁的寬闊排水溝。好在她人沒出什麼大礙。
接下來就是這場,我說不清到底算什麼的追逐拉鋸戰。
我並不清楚她和我之間,到底有什麼樣的仇恨與過節,就如同今天放學以後遇見的所有人一樣。
我甚至一度也懷疑她是不是和那群人一樣,是中了什麼邪,才變得如此暴力焦躁。
但是,她明顯更有自主性,更軟弱,更靈活,看起來更加具有自我意志。比起那一撥人,顯得毫無信念和約束力。累了就歇,一歇就罵,邊罵還邊哭。甚至能和我進行一定程度上的語言交流,盡管都是咒罵和怨毒的話。但至少我感覺上是有來有回的,沒有如同山腳下的那群人一樣的銅牆鐵壁之感。
現在是什麼時候?我抬起左手腕看了看時間,星期五,晚上八點過一刻。今天是月底的雙周末假期,按理說這時候我應該已經吃過晚飯,攤在家里的沙發上閒散地放空著。
我不打算跑了。
「林老師,我不跑了。」我看著對面的女人說道,「你也別過來了,就……暫時別過來了……咱們把話說清楚好嗎?」
女人只是直愣愣地瞪著我,說實話經過這半個多小時的接觸,有時間我甚至懷疑她是個聾子。
就在這時,我似乎又感覺到了那雙孱弱的「手」向我伸了過來。殘肢斷臂,輕輕的在我的鋼盔之上,用血肉塗抹擾動著。
我充滿嫌棄地輕輕將其拍打開,它再次消失在「意象」之中。
對面的女人忽然變得異常悲憤,看樣子已經拉開架勢,准備向我進行新一輪的「撲食」。
「你他媽還有完沒完!!」我有了些混不吝的情緒,這次試圖伸出手直接把她給用力推出去。
但在碰到她之前,她就已經迅速的彈開了。只見她向著後面的方向急速地扭動而去。似乎為了追求速度,她開始手腳並用,像只扭動前進的人形蜘蛛,急速的朝遠處「攀爬」著。嘴里還不受控制的傳來「咿咿呀呀」的叫喚聲。
我還未能對這詭異離奇的場景做出反應,她忽然朝左邊拐了一個彎,左腳絆住了右腳,像一個風滾草一樣,轉了一兩圈,撞在了堤壩旁的水泥牆上。
然後她便攤在那里,一動不動了。
我蒙在原地,沒搞明白剛剛發生了什麼。或者說,我不明白今天所發生的任何事情。
過了好一會兒,我才慢慢靠過去,想看看她是否有個好歹。還未等我走近,便聽見她開始「嗚嗚」的小聲哭起來。
我停下腳步,鬆了口氣。
逐漸地,她的嗚咽聲開始演變成放聲大哭。我一時之間也不知道作何反應。
「寶兒……寶兒啊……嗚嗚嗚嗚……」她好像開始在含糊的喊著什麼,「寶兒啊……嗚嗚……媽媽殺不了他……嗚……殺不了啊……」
寶兒?媽媽?我怎麼記得她好像還沒有結婚啊。
她癱在一旁持續的嚎哭著,「他提前出來了……嗚嗚……我又讓他出來了……」
我理解不了她話語之間的含義,也沒有過多的深究。精神分裂?或者被迫害妄想症?我也說不准。不過聽她聲音里的生命力,身體應該沒有什麼大礙。
隱約間,我感覺到某種讓人畏懼的東西已經消散的差不多了。於是我轉過身,向反方向走回去。
我現在只有一個念頭。
我要休息。我要回家。
未完待續
來源:機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