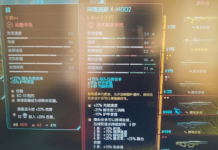譯者的話
《威廉·吉布森和當代文化的未來》(William Gibson and the Future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出版於2020年,編者為默里(Mitch R. Murray)和尼爾格斯(Mathias Nilges),主要內容為吉布森作品與現代性之關聯。因譯者無力獨自翻譯全文,故而採用導讀(3000字)+注釋(14000字)的形式對此書進行譯介,這也就是欄目名【注·譯】的由來。注釋中對原文大致內容的概述難免有所疏漏與詞不達意,感興趣的讀者可查閱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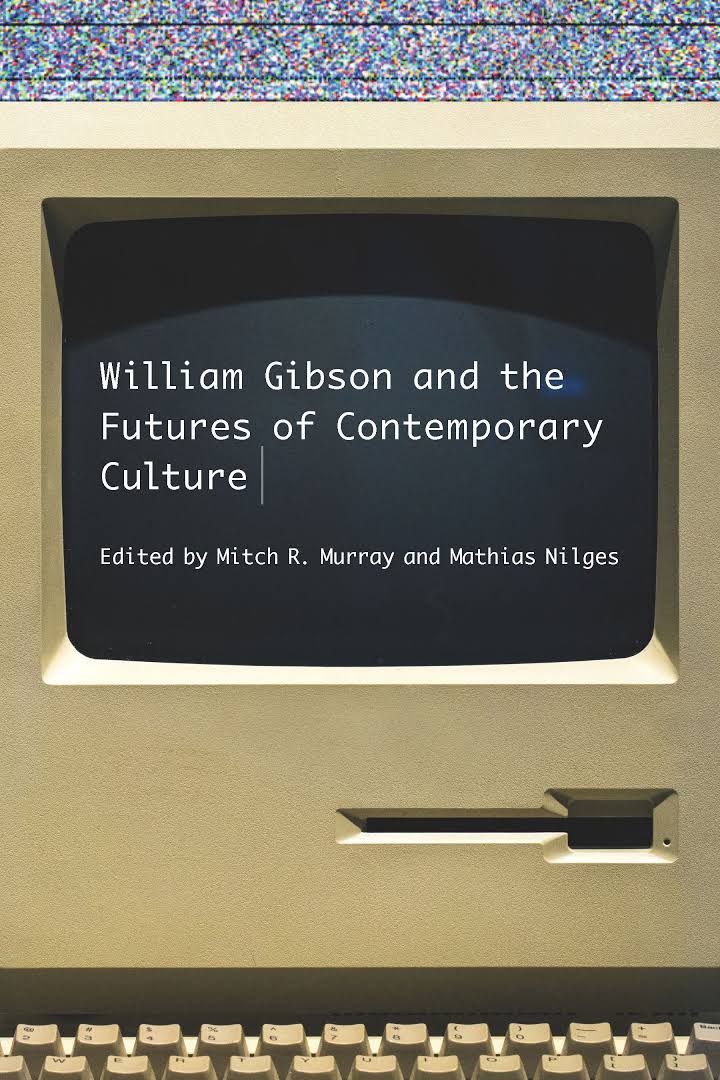
導讀
導讀部分譯自 Esko Suoranta 在《科幻研究》(Science Fiction Studies)2021年第3期上發表的書評《總是分布不均》(Always Already Unevenly Distributed)[1]
每隔幾年,就會出現一本關於威廉·吉布森的看似權威的評論著述。湯姆·亨索恩 (Tom Henthorne) 的《威廉·吉布森:文學指南》(William Gibson: A Literary Companion,2011) 緊隨其後的是加里·韋斯特法爾 (Gary Westfahl) 的《威廉·吉布森》 (William Gibson,2013) 和傑拉爾德·阿爾瓦·米勒 (Gerald Alva Miller) 的《理解威廉·吉布森》(Understanding William Gibson,2016)。我研究吉布森在進入21世紀後所寫小說已經有一段時間了,目前還沒有著述可以將整體性地研究他的「藍色螞蟻」三部曲(Blue Ant Trilogy,2003-2010)、可以深入地而非淺嘗輒止地分析他的《外圍》(The Peripheral,2014),我為此感到遺憾。
在這方面,《威廉·吉布森和當代文化的未來》(William Gibson and the Future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致力於填補這一學術空白。它收錄了11篇文章,外加作家馬爾卡·奧爾德(Malka Older)的前言[2]、默里(Mitch R. Murray)和尼爾格斯(Mathias Nilges)的引言以及作家、《西部世界》編劇游朝凱(Charles Yu)的後記。作為一個經過編輯的合集,而非某一單獨的學者的研究,本書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廣度和深度,這點尤其體現在對吉布森近二十年的作品的研究之中。
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側重文學史背景下的吉布森,第二部分關注媒介問題,第三部分的關鍵在於吉布森與難以捉摸的當下之間的聯系。令人欣慰的是,本書繞過了大多數缺乏新意的關於吉布森作品在各文學流派中的位置的討論,比如,「蔓生都會」三部曲(Sprawl Trilogy,1984-1988)的後現代主義-現代主義和《模式識別》(Pattern Recognition,2003)的科幻現實主義。正如本書的引言和第一部分中幾篇文章所明確指出的那樣,繞過這些討論意味著一種對吉布森的作品的共同的、根本性的理解,即吉布森總是在瀏覽、借鑒各種文學領域的成果,諸如「現代主義」等流派的硬性劃分並不能涵蓋吉布森作品的全部面貌。奧爾德的前言也很出色,他通過「植根於社會學的觀察」以及其中的犯罪和錯位主題來分析吉布森的作品。
總體而言,這些文章提供了對許多研究較少的吉布森作品的引人入勝的解讀,例如尼爾格斯對《根斯巴克連續體》(1981)的解讀[3]、科斯納克(Korsnack)對《冬季市場》(1986)的研究[4]。此外,還有些研究採用了有趣的分析方法,比如羅傑·惠特森(Roger Whitson)對媒介考古學的使用[5],以及阿爾貝托(Alberto)和斯旺斯特羅(Swanstro)的吉布森的數字人文閱讀與數字人文的吉布森閱讀[6]。書中有兩篇文章主要關注「藍色螞蟻」三部曲、三篇文章關注《外圍》,科斯納克關於時間多重性的文章中更是同時討論了兩者,這都說明這一集子是何等的強調吉布森21世紀後作品。
最好的幾篇文章可謂是巧妙絕倫。巴特勒(Butler)對吉布森作品的影視改編和他的編劇寫作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概述[7],包括影片《捍衛機密》(Johnny Mnemonic,1995) 和他為《異形 3》(Alien III,1987) 以及兩集《X檔案》(X-Files,1993-2002) 所編寫的劇本。他認為,盡管創意合作對電視或電影製作來說十分必要,但人類學家馬克·歐傑(Marc Augé)的超現代非場所(supermodern nonplaces)實例卻出現在了所有吉布森的影視作品之中。
艾米·埃利亞斯(Amy J. Elias)的《威廉·吉布森的中的實在本體論》(Realist Ontology in William Gibson』s The Peripheral)是另一大亮點[8],它建立在物導向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簡稱OOO)、後人類主義和生機論的唯物主義(vitalist materialism)的基礎上,以達到對小說的倫理解讀。埃利亞斯展示了小說所提出的「實在界」樣式如何引發了不可被化約為本體論事實的復雜倫理問題:它們沒有解決如何理解和使用個體能動性問題。類似的主題出現在文特(Vint)的文章中,她通過藝術和廣告的並置提供了對「藍色螞蟻」三部曲的引人入勝的解讀。[9]對她來說,藍色螞蟻公司代表著不斷擴大的市場范圍,這使得吉布森筆下的角色沒有促進社會變革的集體手段,而只能轉而尋求個人的庇護所。
可以說,《神經漫遊者》(1984)和賽博朋克主導了幾十年來對吉布森作品的文學批評的基本模式,而《威廉·吉布森和當代文化的未來》則朝著更全面的方向邁出了重要的一步,盡管它並沒有做到盡善盡美。吉布森21世紀以來的作品在本書中獲得了相當的關注,並且確實值得稱贊(我由衷地贊嘆本書沒有收錄任何一篇研究《神經漫遊者》的文章的破釜沉舟般的信心),但美中不足在於「橋梁」三部曲(Bridge Trilogy,1993-1999)在本書中本應受到更多關注。例如,《明日之星》(All Tomorrow』s Parties ,1999)僅僅只在引言中被提及,也只有科斯納克將「橋梁」三部曲簡要分析為在「蔓生都會」三部曲的賽博空間沉浸之後向「過度物質性」的轉變(55)。
此外,在「當代文化」的標題下,人們可能希望找到一篇文章專門介紹吉布森最近涉足漫畫領域的嘗試,尤其是在本書第二部分還專門介紹了他業已出版的不同媒介形式的作品的情況下。但無論是《大天使》(Archangel,2016-2017)還是《威廉·吉布森的異形3》(William Gibson』s Alien 3,2019)都沒有受到分析性的關注,即使是在兩者都有被提及的情況下(巴特勒從吉布森廢棄的劇本的角度討論了後者)。《大天使》的故事設定在虛構的2016年和1945年,可以看作《差分機》(The Difference Engine,1990)的或然歷史(Alternate History)與《外圍》的時間旅行結構的結合。由於本書中有幾篇文章涉及到吉布森作品中的時間性、時間旅行和或然歷史,因此將這一漫畫排除在討論之外使我頗感意外。如果能有一篇專門介紹漫畫研究方法的文章,就可以補充對吉布森作品中不同類型的時間推測的討論,同時也可以完善本書第二部分對不同媒介的關注。
本書的北美學術背景在其所使用引人注目且蔚為壯觀的二手材料列表中有所體現。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是迄今為止被引用次數最多的學者,而《科幻研究》被引用的次數比英國《預測》(Extrapolation)、《基地》(Foundation)或其他專注於科幻研究的歐洲期刊都多,唯一的例外是《波蘭美國研究》(Polish Journal for American Studies)2018年的一期吉布森特刊,不過這一期刊在參考書目中誤認成了科幻雜誌。
除此以外,本書還出人意料地忽視了一些特定的方法和二手材料。由於《外圍》和《代理》(Agency ,2020) 都處於復雜的氣候危機的背景下,未來和過去都迫在眉睫,生態批判分析的缺失在我看來是一大不足。尤其考慮到吉布森目前正在創作的系列名為「頭獎」三部曲(Jackpot Trilogy)——「頭獎」是吉布森對消滅了80%人口同時讓富人更加富有的事件的諷刺性說法——我期待一些關於他如何看待人類世的深入討論。環境人文領域大量的著作為這一討論提供了敲門磚,比如厄休拉·K·海斯(Ursula K. Heise)對吉布森小說的簡短討論,再比如提供了有關該主題更總體性的理論背景的一眾生態批評和文學特刊。
同樣,瑞貝卡·列莫夫(Rebecca Lemov)的文章《關於非此在:工作和娛樂中的數據驅動機構》(On Not Being There: The Data-Driven Body at Work and at Play,The Hedgehog Review [2015], online)與克里斯蒂安·P·海恩斯(Christian P. Haines)討論《外圍》中的遊戲、生命政治、經濟學的文章直接相關[10],因為它們討論了相同的主題和相同的小說。最後,雖然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比比皆是,而且展開得從容不迫,但對經濟問題的過度關注可能需要交叉方法來進行補充。事實上,性別、性存在、種族和能力問題大多隻是泛泛提及,而沒有展開全面討論。有時這也讓吉布森倖免於難,可以說,在吉布森處理這些問題的方法中確實本身就存在著一些需要分析和批評的因素。
雖然這本專注於當今一位核心科幻作家寫作的研究合集的深度和廣度令人印象深刻,但它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孤立於當下的文學研究話語之外。在某種程度上,這限制了它對吉布森作品所占據的位置以及他所影響的和被影響的所有領域的更全面理解的潛力。
最後,拋開上述這些缺點不談,《威廉·吉布森和當代文化的未來》是一個令人愉快的補充,它試圖在一些細節和延續性中討論吉布森和他的小說。它提醒我們有必然擺脫對作家作品的僵化性的總體看法,轉而以更明確的重點來構建批評。默里和尼爾格斯的工作令人欽佩,他們編選了這本適合所有讀者的書,但這也使其無法滿足專業讀者的需要。當然,這也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力量。對於進一步努力研究作為當代最有見地的作家之一的吉布森,並且通過其作品來欣賞當下不可化約的陌生感來說,還有什麼更好的跳板呢?
譯者注/讀書筆記:
[1] 標題:
致敬吉布森的名言:「未來已經來到了,只是分布不均(The future is already here, it’s just not very evenly distributed)」。
[2] 詳見《犯罪與錯位:威廉·吉布森的現代性》(Crime and Dislocation: William Gibson』s Modernity)一文:
奧爾德認為吉布森徘徊在現代性的邊緣而又不至於陷入後現代主義,時間、空間、階級、人性、規模、身份、文化和現實的錯位被最現代的情節(懸疑小說、推理或驚悚)的范圍內的意識所調和。前者是吉布森作品的持久主題:錯位、迷失方向、混亂;後者是吉布森小說的顯明元素:犯罪。
錯位是現代性的一個相當普遍的主題,伴隨著現代性的運動與反思,這一主題一再出現在現代小說中,最典型的莫過於普魯斯特《在斯萬家那邊》:「當我在半夜醒來時,不知道我在哪里,我甚至一開始就不能確定我是誰」。而科幻小說,因其通過未來的視角來看待現在的特性,天然具有一種錯位的主題。而吉布森的科幻小說進一步拓寬並發展了這一主題。
吉布森的錯位主題首先是時間性的錯位。吉布森筆下的人物經常發現自己處於一個支離破碎的世界,他們的內心困惑不已。在他們無意識的時候,內部和外部條件會發生變化;當他們醒來時,過去、現在和(分布不均的)未來都是可供選擇的。而吉布森小說中的錯位又不局限於時間性,它是多重且復雜的。除了時間之外,他的人物往往遭受文化錯位的困擾。這最明顯來自於國際旅行,在《模式識別》中,凱西在倫敦、俄羅斯以及日本發現了「鏡像世界」,這一詞匯用以指稱在平行開發過程中出現的特定位置的區別,這是極其細微的行業差異,比如行駛方向或者電源插座類型的區別,而就是這一細微的區別隱藏著巨大的錯位的力量。與此同時,國際旅行這一行為本身就是引發方向的迷失,在《幽靈之國》中,狄托乘坐飛機橫穿全國,但這並不是一種航空旅行,而是成為了現代性的雷達下位置點的變動。而旅行並不是遭遇文化錯位的唯一途徑,同一個城市的不同階層的人生經歷格格不入,他們的參照點無法比擬,相同的詞語卻可能有著截然不同的含義。在更具未來主義色彩的小說中,錯位變得更加存在。吉布森首先通過賽博空間削弱了我們的身份概念,隨後通過化身挑戰了讀者關於什麼是人類的想法,最後在《外圍》中,他通過「存根」(stub)的想法挑戰了「現實」這一概念(關於「存根」的討論詳見注釋4)。
更進一步,吉布森的錯位不僅僅是角色的錯位,角色的迷失方向通常與讀者的方向平行,快速剪輯的場景和多個角色的敘述視點將讀者拉入了與情節一致的錯位之中。這正是我們在現代性中體驗的反映,我們需要在醒來時查看我們的手機,以了解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我們的身份已經變得支離破碎、缺乏穩定。
盡管吉布森的書對人物和讀者來說是一種迷失方向的體驗,但它們絕不是無形或無方向的。事實上,小說傾向於最受情節驅動的文學形式:偵探故事。吉布森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在我看來,偵探小說和科幻小說是一種理想的雞尾酒。」吉布森的小說包含犯罪小說的強烈元素,這使得吉布森的小說得以徘徊於現代的邊緣而不至於滑落至後現代。
偵探故事的主要功能是搜尋,吉布森筆下的許多角色都是由某種特定的「謎」所驅動,他們通過他們不完全理解的方式行事:《模式識別》中凱西的品牌敏感性、諾拉以她周圍的人無法解釋或解讀的方式進行創作,但她的創作卻引起了成千上萬的人的共鳴。他們的特殊能力或洞察力是現代性暴力的副作用。吉布森認為,獲得這種抽象洞察力的方式是非線性的,可能需要一種不同的智慧、對直覺的依賴,而這種直覺往往源於現代世界所造成的損害。在這種直覺的驅動下,即使角色不完全理解他們在尋找什麼、為什麼或如何尋找,但在現代性的危機中——一個混亂、錯位和犯罪的時代——他們仍然會繼續尋找能夠重新創造某種世界觀的敘事或形象。
[3] 詳見《未來保質期:威廉·吉布森的短篇小說和體裁的時間性》(The Shelf Lives of Futures: William Gibson』s Short Fiction and the Temporality of Genre)一文:
尼爾格斯在開篇首先引述了斯特林對吉布森貢獻的總結,認為吉布森的作品通過追蹤按照現在的軌跡可能導致的未來以探索我們現在的物質和社會政治邏輯的基礎,這是其區別於那些「避免與現實的未來糾纏不清」的風格和體裁中尋求庇護的作家的特徵所在。尼爾格斯引述這一評價的目的在於說明,「藍色螞蟻」三部曲並不是通常認為的吉布森由科幻小說創作向現實主義小說創作的轉變,事實上,吉布森的科幻小說根本就是「現實主義」的小說。
吉布森作品的現實主義在於它致力於將科幻小說歷史化,對與外部歷史流動相關的未來、體裁和文化想像的興衰進行自我反思式的檢查。在吉布森看來,未來和體裁都有其自身的保質期,它們出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使我們能夠理解並回應我們眼前正在發展的世界。然而,他們最終會被歷史的洪流所淘汰。《根斯巴克連續體》就是這一思想最為具象化的代表,它概述了賽博朋克的歷史和政治風險,因為它必須背離以往想像未來的形式與觀念。正如菲利普·韋格納(Phillip E. Wegner)所指出的,賽博朋克只有在傳統的未來敘事無法再維持下去的時刻才會出現。同樣的,當賽博朋克的未來敘事走到無法再維持下去的地步時,吉布森走向了《識別模式》:「今天科幻小說的最佳用途是探索當代現實,而不是試圖預測我們的未來。」也就是說,現實主義和科幻小說之間持續存在的歷史化張力對吉布森的作品至關重要,是貫穿於吉布森科幻創作的關鍵所在。
《根斯巴克連續體》的核心可以歸結為一個問題:「從未出現的未來以何種方式對現在產生真正的影響?」它並不是通過現在與可能發生的事情之間的比較來質疑現在,而是通過我們曾經希望發生的事情在現在的存在和不存在之間的矛盾來審視現在。《根斯巴克連續體》的內容和形式並不是現在和未來之間的張力,而是兩種現在之間的張力,兩者之間的差距構成了我們歷史化現在的反向敘事,與將未來看成現在線性發展的敘事不同,這是一個將我們的時代理解為跌落的未來的敘事。我們必須為我們虛構的明天承擔責任,因為我們想像的未來可能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密切參與並支持一組不同的真實社會、物質和政治發展。
然而,將與現在相關的未來概念歷史化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任務,它最終會導致敘述者越過邊緣界限。《根斯巴克連續體》的敘述者發現,沒有實現的未來並沒有簡單地消失或變得過時,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科幻想像的諸多產物正與現在發生碰撞。過去的未來繼續困擾並影響著現在。極度恐懼的敘述者尋求他的朋友的幫助,後者的建議是「符號排毒」——「真正糟糕的媒體節目能幫你驅走那些符號幽靈。」這一建議對我們參與和想像當下問題的替代方案來說同樣至關重要,而這構成了吉布森作品的核心思想,即本雅明所說的「布萊希特格言」:「不要從過去的美好時光開始,而是從糟糕的新時光開始。」吉布森的科幻小說要求我們在與當前糟糕的新日子的積極對抗中改變自己,要求我們以新的方式來想像未來。未來不再是過去架構的發光、閃爍的線性未來,未來也不是現在的延伸,恰恰相反,未來影響著現在。「符號排毒」,就是驅除非歷史化的、靜態的未來主義形式的物化形式,將未來主義從它的崩潰中解放出來,從而進入現在。未來是能動的存在。這是一種通過處理兩個不同的現在的矛盾,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賦予未來想像以歷史化的方法。
九十年代以來,我們目睹了現在與未來的危機之間聯系的蔓延,以及既定的未來概念的崩潰,而替代方案卻遲遲未能出現。於是,這種時間性危機帶來了再現危機和敘事危機。一些評論家,如奈爾·德葛拉司·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試圖通過回到我們尚未「停止夢想」的歷史時刻來重新點燃未來學,但吉布森清楚地意識到,這些重大危機的根源並不在於夢想本身,而是因為我們對未來的看法僵化了。《根斯巴克連續體》中的危機不在於停止夢想,而是夢想落地,無論其實現與否,所造成的既定未來的枯竭而引發的危機。正如敘述者所經歷的那樣,當未來崩潰時,只有敘事才能解決我們的想像危機,才能為我們提供新的時間模型。吉布森並沒有哀嘆仍然讓我們夢想的過去,而是歷史化了這些夢想並突出了它們可能隱藏的危機,從而敦促我們通過處理糟糕的新日子來尋找前進的方法。
吉布森的早期短篇小說在他的作品中確立了一個不變的原則:科幻小說是對自身以及在特定歷史時刻主宰我們文化乃至社會和政治的未來想像的一種批判形式。新的未來在與糟糕的新日子的對抗中出現,從而與過時的未來想像相對立。而這也正是科幻作品才具有的特殊的重要性。
[4] 此處導讀有誤,科斯納克的文章中並沒有解讀《冬季市場》,而是針對吉布森小說的時間性問題進行了研究。詳見《沒有未來,只有另一種選擇:威廉·吉布森作品中的時間平衡》(No Future but the Alternative: Or, Temporal Leveling in the Work of William Gibson)一文:
科斯納克首先指出《模式識別》一文中以一種「令人生疑的低調」方式提到了一件”紐約歷史上最大的私人委託公共藝術之一”——由克里斯汀·瓊斯和安德魯·金澤爾設計的「節拍器」(Metronome)。藝術家們將這件作品描述為「對時間本質的調查」,認為「從本質上講,它把時間從字面上投射到形上學——無法衡量的時間。」但是,科斯納克認為這類觀點忽略了一個事實,即節拍器實際上裝飾著一座豪華公寓大樓,其網站自豪地邀請潛在顧客「在藝術品中奢華生活」。因此,節拍器是一個悖論:一方面,節拍器體現了藝術的可能性和潛力的烏托邦理想,展示了藝術對勞動力驅動的後現代文化的干預以及對秒針主導邏輯的時間體驗的超越。但另一方面,公寓大樓的存在使得節拍器同時成為了一種商品化的審美形式,體現了藝術品在晚期資本主義文化中所面臨的特殊處境。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節拍器成為了吉布森小說基本困境的一個隱喻,突出了吉布森作品中存在的一個中心線索:對當代文化中藝術、時間性和人類體驗之間關系的持續反思。
在具體分析吉布森作品之前,科斯納克首先介紹了將同時性的概念與現代性的時間經驗聯系起來的幾個理論範式:首先,《時間:當下的詞匯》(Time: A Vocabulary of the Present)的導言指出,多樣性和同時性是定義”我們的當下感”的主導術語:「現在」實際上是由同時性和多樣性之間的張力所激發的。他們反對通常理解中將同時性等同於多樣性的減少,等同於受制於資本的單一時間。恰恰相反,「現在」就是一種”同時性的體驗”,一種對當代資本主義的主導性時間的抵抗。與之相對的是,資本主義的當代性構造的「同時性的幻覺」,一種與加速擴張的全球市場的需求一致的單一時間概念。這種”同時性的幻覺”類似於法國哲學家雅克·朗西埃所說的”統治時間”——有一種主導形式的時間性,傾向於將所有形式的時間性統一到它的控制之下的單一的時間結構,而這種同時或同質化的時間正是資本主義邏輯產生的虛構。而恰恰就是在這種幻覺與虛構的內部,存在著自反性的悖論。《時間:當下的詞匯》認為對資本主義當代性的解毒劑是通過揭露構造當下的多種同時性形式來打破「同時性的幻覺」。而朗西埃則確定了兩種可能破壞同質時間主導邏輯的其他形式的時間性。第一是間隔,這是個人或群體”重新協商他們調整自己的時間以適應統治時間”的時刻。第二是中斷,即”構造統治時間的某個社會機器崩潰和停止的時刻”。概言之,當代資本主義虛構了一個統治性的單一時間,而打破這一虛構的方法就是探尋時間的多樣性與同時性。
吉布森對時間性的興趣跨越了他文學生涯的大部分時間。在《死人的歌聲》(Dead Man Sings)中,吉布森將他作品的”中心驅動張力”描述為”沒有新東西……和所有東西都在變化”,即現在的千篇一律和未來的快速變化。吉布森的「蔓生都會」、「橋梁」三部曲,是巴赫金意義上的時空視野。巴赫金強調「狂歡」,強調眾聲喧嘩的多重性,在時空之中就表現為時空的疊加,空間中「保存著過去,並代表著未來」。時間與空間之間單一對應的關系的分離與坍塌在吉布森早期小說中最為突出地表現出來。賽博空間作為一個非物質性的地點,是一個”非空間”,但「最多樣化的人——所有社會階層、階層、宗教、民族、年齡的代表」在這里相遇,使其具有了時間上的多重性。在「橋梁」三部曲中,盡管作為空間的橋梁變成了一個過度物質性的地方,但在其上存在的仍然並不是單一的時間,而是「幾個世紀、幾代人的痕跡都以可見的形式排列在其中」。概言之,吉布森的小說展現了同時性對當下主導性時間邏輯的抵制。
同樣的思考出現在吉布森的後期小說中。《模式識別》中當代資本主義的化身、「藍色螞蟻」公司的執行長比根德(Bigend)宣稱:「我們沒有未來。不是像我們的祖輩那樣有未來或認為他們有未來。充分想像的文化未來是另一個時代的奢侈品,在這個時代中,『現在』具有更大的持續時間。」而這里存在著一個滑稽的互文,宣稱「沒有未來」的恰恰是「巨大終結」(Big end),由此形成了一個荒謬性的自我指涉。《模式識別》就是對這種永久停滯的資本主義當代性的主導意識的反叛。在整個小說中,主人公凱西處於一種永久的時差狀態,這種狀態是由快速跨時區旅行引起的,運動在空間上的變化使時間多重地疊加在凱西身上,其身體和頭腦在兩個不同的時間中運行。
在《外圍》中,吉布森採用雙線敘述,一條設定在近未來的美國農村小鎮,另一條設定在第一條時間線70年後的22世紀初的遠未來的倫敦。在遠未來,一個被稱為「頭獎」的世界末日事件消滅了世界上八成的人口,留下一個由小部分精英統治的世界。在近未來,「頭獎」還沒有發生。而隨著敘述的展開,讀者驚奇地發現,這兩條時間線並不屬於同一線性路徑。近未來只是一個備選方案、一個「存根」,「頭獎」的遠未來並不是近未來的未來。《外圍》中的時間旅行比傳統的時間旅行敘事更令人震驚,讀者發現自己同時占據了多個時空:「外圍」設備是一種「遠程呈現的化身」,它承載了人的意識,使其可以同時存在於兩條時間線上。它是弗琳進入未來空間的一種方式。但同時,弗琳的身體還在過去,她在未來的行動不斷地被「自律性出血」或飢餓、睡眠等身體的需要打斷。這意味著一種身體和心靈的分裂:身體存在於一個世界,而認知卻同時存在於兩條時間線上。在這個意義上,吉布森用他的小說形式破壞了單一的時間概念。他沒有屈從於小說的進步和線性趨勢,而是迫使讀者同時面對多重時間。
[5] 詳見《時間批判和或然歷史的結構:和中的媒介考古》(Time Critique and The Textures of Alternate History:Media Archaeology in The Difference Engine and The Peripheral)一文:
惠特森在這篇文章中引入了沃爾夫岡·恩斯特(Wolfgang Ernst)的時間先決性(time-critical)思想來補充詹明信和菲利普·韋格納對或然歷史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所謂時間先決性可以理解為無法被人類感知的數位化的微型時間,而這一時間卻可以被媒介所捕捉到,由此破壞了人類對時間意識的認知。「發生在微秒領域的事件不再能被人類的感官有意識地感知到,因此它們屬於純粹的測量電子領域,人類的時間敘事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技術媒體的時間。簡言之,即媒介決定了我們對時間的感知與意識。惠特森希望以此來修正詹明信在《政治無意識》中對或然歷史的看法,他重新界定了詹明信所說的或然歷史是「一種本質上的歷史主義觀點,在這種觀點中,我們對過去的解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對現在的體驗」中的「我們」和「現在」。這兩個概念不再被看作是專屬於人類,而是被擴大到包括計算機的非人類過程和時間性,這改變了我們對或然歷史的體驗與理解。
詹姆遜將歷史與拉康的實在界相聯系,認為歷史「除非以文本形式出現,否則我們是無法接觸到的」,對於詹姆遜來說,文本是對「無法解決的社會矛盾」的想像解決方案。在這里,人類從歷史的矛盾中將想像文本化,從而成為象徵性地歸檔歷史的工具。而在《差分機》中,進行歷史歸檔工作的是非人類的分析機。小說開始時,我們看到「合成圖像,由「布魯奈爾爵士號」越洋飛艇的護航機攝制光學加密:瑟堡郊區的俯瞰圖,1905年10月14日」。當我們接近傑拉德時,她的身體分解成必要的部分:「肌腱、組織、關節骨。通過時間和信息的安靜過程,人體細胞內的線已經將自己編織成一個女人。」這種效果既是美學的,也強調了傑拉德的人體是如何通過算法重建來定義的。在小說的結尾,敘事不再以人類時間的線性順序展開,而是呈現出人類不可理解的雜亂,敘述者也顯露其非人類的真身。
在《外圍》中特別出現的是一種反烏托邦式的願景,即或然歷史是班傑明·布拉頓(Benjamin Bratton)所認定的由無處不在的計算帶來的新興主權「偶然的巨型結構」中的一個變量。這個巨型結構或「堆棧」由地球、雲、城市、網絡、地址、界面和用戶的層組成,是一種尚未確定的非人類超級計算地理學。與計算一樣,從根本上講,它涉及循環、分支和處理輸入接口的值,堆棧中的治理性體現在層之間的交互中,這些層的累積相互作用導致更全面的結構,以及將這些結構聚合和分類成更新和更抽象的形式。或然歷史中人類選擇的無限可能性成為吉布森在治理和經濟程序中的工作變量,新興計算系統用於分類、處理和控制的技術。盡管歷史在吉布森的作品中仍然是鬥爭的辯證法,但參與這場鬥爭的參與者包括非人類技術過程,其規模和速度將治理的場所從人類轉移到算法。
概言之,《差分機》所要表明的是歷史不是不可避免的。而《外圍》則要證明,或然歷史確實可以變成不可避免的,但是這一不可避免性是它在人類無法控制的事件群中的隱形功能。
概言之,惠特森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在於,吉布森的小說證明了我們對機會和行動的理解以及我們對或然歷史的體驗,越來越多地受到非人類的時間先決性過程的調節。
[6] 詳見《威廉-吉布森,科幻小說和數字人文科學的演變》(William Gibson,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一文:
這一文章以一個滑稽的新聞引入:2017年,塞維爾以要求獲得與他的電腦結婚的權利為由對猶他州提起訴訟,但很快被駁回,幾個令人信服原因中包括塞維爾的電腦並沒有達到法定年齡要求。這一特殊嗜好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的皮格馬利翁。而在當代,吉布森的作品成為了其最生動的文學藍圖。吉布森小說中這種看似不相容的實體之間的整合模式與新興的數字人文領域有著特別的共鳴。
在《啟蒙的辯證法》的導言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批判了啟蒙思想的「總體化」和「腐蝕性的理性」,在啟蒙中,「任何不符合可計算性和實用性標準的東西都必須被懷疑。」這出人意料地描述了幾十年後數字人文中的一種特殊摩擦——定量計算方法和主觀定性分析之間的摩擦。數字人文可以劃分為三條路徑:媒介理論、實驗美學和人文計算。媒介理論幫助我們評估我們的交流方法;實驗美學指任何與數位技術和形式創新有關的藝術製作行為;人文計算指使用計算方法來對文學文本進行統計分析的領域。然而,直到最近人文計算才開始與其他兩條路徑結合,而且並不順利,科學和人文知識生產之間的鴻溝仍然難以跨越。轉向科幻小說,特別是吉布森的賽博朋克,可以提供有用的方法。
數字人文的吉布森閱讀:在吉布森的賽博朋克之前,科幻小說中與計算有關的作品有難以置信的多樣性,從《格列佛游記》中非個人化的機械到《銀河系漫遊指南》中的地球本身。「計算機」(computer)一詞最初並不是指機器,而是通過復雜的基礎性計算以支持科學工作的人。因此,科幻小說和科學事實中的「計算機」概念就同時涵蓋了與身體、知識和各種信息傳輸手段之間的復雜關系。在這之中,有三個文本對吉布森對數字的處理以及走向數字人文有著重要意義——《嚴厲的月亮》、《2001:太空漫遊》、《歌唱的船》,這些早期的科幻小說文本努力以他們的行動和能力而不是他們的機械部件來定義計算機,這一事實預示著吉布森後來如何融合人類和計算機。這點在《冬季市場》中體現地較為突出,這個短篇小說復雜化了對人類身體的態度,對數位化的消費文化進行了毀滅性的批判,並執行了一種令人不安的文化抵抗模式。
吉布森的數字人文閱讀:以吉布森的作品、學術研究為主要樣本構建起包含四千多份文件的資料庫。發現「吉布森」這個名字和「賽博朋克」這個詞的分布幾乎相等。「計算機」和「吉布森」之間有輕微的重疊,但「計算機」和「賽博朋克」之間沒有重疊。同樣,「數字」這個詞的出現也在兩者之前,但只是稍有重疊。這表明,「計算」和「數字」這兩個詞的內涵有一個耐人尋味的區別。此外,結合數字人文的吉布森閱讀,對《冬季市場》所強調的主題——性別、殘疾、再現等創建了關鍵詞列表,進行比對研究。
[7] 詳見《新玫瑰旅館就是新玫瑰旅館就是新玫瑰旅館:威廉·吉布森的螢幕改編中的非地點》(「a New Rose Hotel is a New Rose Hotel is a New Rose Hotel」 :Nonplaces in William Gibson』s Screen Adaptations)一文:
巴特勒認為,吉布森筆下的賽博空間沒有固定的身份、關系或歷史,且缺乏真實的高度、寬度、深度和質量,可以被認為是法國人類學家馬克·歐傑所確定的超現代性「非場所」的補充。馬克·歐傑認為,現在人們所說的後現代性其實是一種超現代性,在這之中三個過剩:時間、空間與個體的過剩,時間、空間的區別已經被抹去,共同導致我們甚至還沒有進入現在就已經生活在過去之中了,而後者意味著個體無時無處不受到侵犯。在這一基礎上誕生的「非場所」與「場所」相比缺乏身份、關系和歷史,而指向了過渡性地點和臨時性居所(如連鎖旅店、假日俱樂部、難民營、貧民窟),被稱作「運輸工具」的飛機、火車和汽車,供遊客臨時駐足的機場、火車站、主題公園,人們從事日常消費活動的大型零售店、超級市場、咖啡館、餐廳、自助取款機以及利用非地上空間進行交流的有線和無線網絡。所有這種「非場所」給人的是一種約束下的孤獨的自由,而這種約束都是通過文本化進行的,即身體在超現代的信息空間里隨著信息傳播的過程完成自身的文本化。
吉布森的《異形3》中的錨點空間站(Anchorpoint Station)就是一個「非場所」,這是希克斯等人回家路上的一個中轉站,而他們幾乎沒有時間與這里建立關系或確立自己的身份。同時,異形的身份和DNA不斷變化就好像「基因結構是為了便於操作而設計的」,預示著它們居住在一個永久的「非場所」。
由《根斯巴克連續體》改編的《明日呼喚》(tomorrow calling)中比爾開著他租來的日產車在倫敦郊區,被一些不自然和不可思議的東西困擾著,形成了一個「非場所」中的嵌套空間。由《約翰尼的記憶》改編的《捍衛機密》中尊尼是一個「非場所」的習慣者,他拋棄了童年的記憶(因此也拋棄了他的身份、歷史和關系),而選擇了企業的數據租賃空間和一個臨時身份。影片相較於小說的改編之處在於尊尼的母親這一角色,其虛擬版本幫助尊尼得以解密數據,同時恢復童年記憶。
在最後,母親在被抹去時再次死亡,尊尼恢復了完全的男子氣概。他與簡擁抱,從而擁抱關系、歷史和身份,影片用場所代替了「非場所」。費拉拉導演的《新玫瑰旅館》被分為兩個不平衡的部分:前三分之二是詹姆斯·邦德式的抓捕行動,後三分之一是X在一個膠囊酒店的「非場所」中的回憶,這一部分所使用的完全是前一部分的重復鏡頭。費拉拉抵制創造電影的標準本體空間——迴避建立鏡頭,通過將人物與人物的圖像合並,抹去了明確的關系和身份界限。
改編中的主角都發現自己身處「非場所」,他們被與他們的身份、關系和歷史相衝突的符號學和代表形式所淹沒。每個人都求助於酒店等「非場所」。這就是「非場所」的悖論:一個迷失在他不知道的國家的人,只有在高速公路、服務站、大商店或連鎖酒店的匿名中才能感覺到家的存在,顯示了個人在晚期資本主義和超現代性的世界「非場所」的持續異化。
[8] 詳見《威廉·吉布森的中的實在本體論》(Realist Ontology in William Gibson』s The Peripheral)一文:
以往對吉布森小說的研究往往從認識論展開,世界被解釋為認識的方式,而《外圍》迫使人們思考本體論問題,思考現實主義本體論對小說的倫理和社會承諾的影響。
托馬斯·品欽構建了一個兩層的本體論,即「陳述」和「虛擬」(「the Declarative」 and 「the Subjunctive」),前者是現代性的空間,即由人類感知能力、認識論和解釋學來定義的三維的、「常識性」的時空;後者是神話或非西方認識論的空間,是崇高、浪漫或量子可能性的世界。2013年,品欽在《流血的邊緣》中提出了第三個本體論領域,即「數字/模擬」(Digital/Virtual)。這一領域來源於「陳述」,但又是「陳述」理性主義和極權主義控制的斷裂,是對「虛擬」的永恆回歸。這是一種救贖性的本體,它將「虛擬」置換到賽博空間,從而插入無政府主義和解放性集體行動的網絡烏托邦理論。吉布森的本體論與「數字/模擬」相似但不同,其一方面承認人工智慧的陌生性和可能性,另一方面又沒有將其浪漫化為一種救贖。在《神經漫遊者》結尾,人工智慧指出「事情並沒有什麼不同,事物就是事物」,而不是人類邏輯、欲望或控制的投射。
如果我們將現實主義定義為:關於存在的主張(即像桌子和石頭這樣的一些事物是存在的,它們的圓度、硬度、顏色等屬性也是存在的)和關於獨立性的主張(事物的存在和屬性與任何人對它們的感知、說法或信仰無關)。那麼《神經漫遊者》中所體現出的本體論就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本體論,其符合物導向本體論和生機論的唯物主義的主張:
《外圍》是對這一本體論的發展,遠未來的精英無法改變自己時間線上的事件,因為一旦他們干預過去,時間線就會分裂出一個新的「存根」。事物和存在狀態獨立於人類的感覺、感知而存在。這便是「真實」,一個受其自身邏輯的支配,不受人類或人工智慧控制的現實。
而這實際上引發了關於階級特權的政治問題和關於殖民欲望的倫理問題,近未來與遠未來的關系實質上是第三世界與第一世界的關系。首先,這是一個關於干預的問題,即那些有能力干預他人生活(和未來)的人可以為善或為惡,遠未來無論對近未來做什麼都不會改變遠未來的狀況。但另一方面,這又是一個自我決定的問題,遠未來的行動確實決定了遠未來的處境,所有行動都會影響世界。因此,干預者的行為肩負了義務和道德陷阱兩方面的意義。把一個人對自由的希望寄託在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人的持續善意上,而其利潤可能會因為剝削而增加,這是一種愚蠢且不穩定的信仰行為。
現實主義本體論把我們拋回到非常古老的人類問題上,盡管我們與其他事物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但是我們仍然要根據我們自身的能力行事。《外圍》在宇宙的機器邏輯的冷漠中,將我們拋回自身。
[9] 詳見《大而不倒:「藍色螞蟻」三部曲和我們的產品化的未來》(Too Big to Fail:the Blue Ant Trilogy and Our Productized Future)一文:
賈克·湯姆伯格(Jaak Tomberg)認為,「藍色螞蟻」三部曲的特點是 “雙重視野”,即必須被「同時作為現實主義和科幻小說來閱讀」。這意味著科幻小說提供不同於世俗世界的願景的能力的崩潰與新自由主義邏輯的霸權。文特認同這一觀點,認為賽博空間已經向外延伸:「現實與廣告融合,映射並取代了我們對物質的感知」,由此產生了對市場經濟和由其價值和衡量標準主導的未來「沒有其他選擇」的感覺。商品關系已經取代了所有的社會關系,藝術失去了抵抗資本主義對社會、政治生活滲透的力量,文化被資本徹底吞沒。
文特的分析從一個不易察覺的細節展開,比根德的母親與情境主義國際(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有聯系。這暗示情境主義,尤其是居伊·德波(GuyDebord)成為理解「藍色螞蟻」三部曲的一種方式。《景觀社會》認為伴隨著消費主義和資訊時代資本的崛起,社會已經從生產階段發展到景觀階段,生活的每個細節幾乎都被異化成景觀的形式,「景觀不是圖像的聚集,而是人們之間由圖像所中介的社會關系」。我們的全部生活都在景觀的統治之下,「所有活生生的東西都僅僅成了表象」。正如德波所言:「經濟對社會生活的支配帶來了存在到擁有的明顯退化——人的成就不再等同於人是什麼,而是等同於人擁有什麼。」而這種退化已經達到了第二個階段,「擁有必須從表象中獲得其直接威信和最終目的」。「商品的拜物教」在景觀社會中達到了終點,「現實世界被投射在它上面的一些圖像所取代,但這些圖像同時也成功地使自己被視為現實的縮影」。資本主義異化完全殖民了社會經驗,以至於我們不再記得有另一種選擇。
商品對其他社會關系的取代在吉布森小說中最突出的表現為對時尚產業的描寫。《模式識別》中的凱西對品牌過敏,她的天賦在於發現那些仍然與生活經驗有聯系的事物。品牌把服裝從生活經驗的領域中拉出來,進入到景觀的領域中。一些東西越是與時尚和品牌聯系在一起,它與物質存在的聯系就越少。在《零歷史》中,比根德認為軍事風格的服裝的吸引力在於其表達了一種「自我認同」的願望,”消費者購買的不是產品,而是敘事”。營銷,特別是推銷商品優先於其質量的營銷,體現了資本主義的邏輯。
更關鍵的是,被商品經濟污染的不僅僅是全球化經濟的大規模生產的物品,即使是像錄像這樣看似與這些工業力量脫節的東西也帶有其痕跡。《模式識別》中凱西認為在網絡瘋傳的一組匿名影片是與世俗世界無關的藝術對象,但實際上這組影片雖然是諾拉的個人表達,但卻需要監獄勞動力進行逐像素的渲染,從而將監獄變成盈利空間。
在「藍色螞蟻」三部曲中,市場被理解為一個具有獨立於人類需求的機構和實體,它優先於人類的需求,是非人類的異化力量,所有社會關系都崩潰為了市場關系。異軌(détournement)固然是一種情境主義策略,通過這種策略,資本主義大眾傳媒的表達方式被反過來,揭示了商品文化的空洞承諾。但資本主義的復原力再次扭轉了局面,任何試圖逃離商品化景觀社會的努力不可避免地被轉化為廣告策略。凱西在《零歷史》中創立的「加布里埃爾獵犬」牛仔褲因拒絕參與過度的品牌宣傳,反倒更具有廣告效應。即使是尋求擺脫商品化的人,最終與產品的社會關系也會比與人的關系更強烈。凱西迷戀影片,霍利斯迷戀加布里埃爾獵犬,吸引他們的是產品,而不是藝術家。對人或集體的忽視是景觀社會無法扭轉的關鍵所在,吉布森小說中的人物只找到了個人撤退和逃避的空間,而不是集體社會轉型,從而使一個社會的存在大於擁有,生活現實大於景觀。
更進一步,吉布森在這三部曲中說明的問題,即商品化的經濟邏輯對社會生活的征服,同時也象徵著21世紀的科幻小說的問題。正如在批評傳統中所確立的那樣,科幻小說通常被理解為一種烏托邦可能性的文學,其向我們展示了世界可能是另一個樣子,並經常鼓勵我們把現在的時刻看作是預期的未來的過去。然而,最近,來自科幻小說的圖標和圖像越來越多地被用來宣傳技術化的未來產品,而這種技術化的未來仿佛沒有資本主義的外部或替代。
[10] 詳見《「只是個遊戲」:威廉吉布森的外圍的生命政治、電子遊戲和金融》(「just a Game」 :biopolitics, Video Games, and Finance in William Gibson』s the Peripheral)一文:
2018年1月,世界衛生組織在《國際疾病分類》中增加了「遊戲障礙」的診斷,但與將電子遊戲與暴力聯系起來的道德恐慌不同,這一診斷強調的是由於無法正確管理自己的時間而導致的日常生活的破壞。遊戲帶來的威脅不僅是心理上的,也是經濟上的,這一點可以從那些擔心遊戲會導致失業率上升的文章中看出,但實際上,「遊戲障礙」與其說是經濟的原因,不如說是經濟的症狀。主體在經濟停滯的條件下被迫投機於偶然的可能性以求得生存,長期職業已經被臨時工作和消費信貸所取代:「埋頭於電子遊戲的生活,靠不定期工作的微薄報酬勉強度日,可能看起來很空虛和悲傷。但它是否比埋頭於金融業,在辦公室長時間工作而忽視生活的其他方面更空虛和悲傷?這只是一個角度問題。」
遊戲與經濟的關系更多體現在對經濟的主體性形式的培養上,遊戲通過迫使玩家在風險評估的基礎上採取行動,以與零工經濟的節奏相對應的方式分配時間,並與他人競爭獲得信貸,從而塑造了一個新的經濟主體。在《外圍》的開頭,弗琳在遊戲中驅趕空中無人機,直到她目睹一個女人被殺死,「『只是一個遊戲』,她說,她的臉頰被淚水打濕」。吉布森對遊戲的描述幾乎沒有明確區分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這與布蘭登·基奧(Brendan Keogh)的電子遊戲現象學相呼應,「電子遊戲體驗」是「玩家和電子遊戲的結合,不是作為預先存在的、獨立的、不同的主體或客體,而是作為人類身體和非人類身體在現實和虛擬世界中的控制論組合」。在這種後人類的遊戲觀中,遊戲在情感層面上修改了玩家,對玩家的主體性進行了重新編程。但即便如此,玩家仍然通過虛擬性的本體論區別而免受物質創傷。
遠未來的人對弗琳「這是一個遊戲嗎」的回答是「這是一個類似遊戲的環境」。這意味著遊戲的邏輯不再被限制在一個獨特的遊戲空間內,社會生活已經被各種程序化的、基於規則的行為系統的算法所支配,我們生活的世界已經變得「類似遊戲」。生活在其中的主體的思維過程、感受和活動也因此而改變。更具體地說,將社會空間轉化為遊戲空間產生了新自由主義的主體,對他們來說,每一種做法,包括娛樂,都屬於一個競爭的舞台,其目標是超越其他玩家。與新自由主義一樣,遊戲涉及的是一種平等的幻想:遊戲中技能和努力是決定成功的最終因素。但是,玩家在形式上的平等,掩蓋了主體具體的不平等,有些人有能力享受遊戲,而另一些人需要遊戲來維持生計。當下的主體被大量的評級機制包圍,從信用分數到社交媒體上的「喜歡」,這些機制根據主體的歷史和他們未來的收入潛力進行排名。其結果是,每個主體都被迫承擔投資的風險,無論他們是否能承受後果。
《外圍》中的遠未來人物是典型的新自由主義主體,是保羅·納庫納斯(J. Paul Narkunas)所說的「市場人類」。他們對自己的能力有信心,把歷史當作投資機會,這種信念要求其對風險的負面後果進行自我免疫。「存根」是這種免疫邏輯的頂峰,它允許市場人類對無法反擊的主體行使幾乎是神一樣的權力,遠未來有能力利用其對過去的了解而不需要擔心反擊。這是一種時空帝國主義的形式,「存根」中的居民與其說是歷史的主體,不如說是遊戲中的碎片。
如果說存根體現了投機性主體性的時間維度,那麼外圍設備則體現了它的空間維度。外圍是一個通過直接連接到人腦的數字設備控制的人形自動裝置。其以一種自相矛盾的方式消除了有形的玩家和遊戲中的化身之間的差距:玩家通過擁有另一個身體而成為自身的化身。這是一個極端的虛擬現實版本,其前提是將日常生活轉變為遊戲空間。外圍設備的死亡並不等同於其操作者的死亡,而只是一次「遊戲結束」,是一個旨在重復的循環中的臨時站點,玩家可以從過去的遊戲經驗中學習並嘗試不同的行動。然而,《外圍》表明,這種無足輕重的死亡在這種對風險的免疫的意義上成為了「存根」的同義詞:它是一個旨在通過將脆弱性外包給次級主體而將權力集中在富人手中的系統的一部分。
社會空間向遊戲空間的轉化還體現在《外圍》的敘事結構和風格中。各章之間的快速過渡標志著歷史條件的偶然性和遊戲空間的可變性。吉布森的句子是模塊化的,放棄了主語或動詞,創造了新詞,將各種觀點折疊在一起。這部小說仿佛試圖仿效資本主義的節奏,將閱讀行為轉化為一種新自由主義的訓練方式:在學習如何應對時間線的快速流轉和接受身體的可支配性時,吉布森的讀者成為一個優秀的投機主體。在一個數位技術占主導地位的時代,小說做了它唯一能做的事情:它提供了玩家的幻想,只要人們願意向遊戲規則投降,就有可能戰勝自己的競爭對手。
電子遊戲作為遊戲的意識形態化身而運作:一個廣泛持有的、自然化的信念系統,它將逃避現實的幻想與商品形式混為一談,並將遊戲封閉在新自由主義資本的魔法圈內。與此相反,《外圍》成為了一個元遊戲,「闡明了一種褻瀆神聖、使藝術歷史化、調解技術和去掉戀物癖的實踐。」
來源:機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