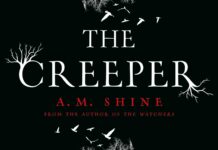一
南方沒有集中供暖,待在室內不過是換個沒風的地方哆嗦。怎麼不開空調?好問題:我連開空調的錢都沒有。
至於為何窮成這副樣子,說來慚愧,我的浪費成性要負五成的責任。明明手頭不寬裕,卻總是大手大腳地消費電子遊戲和周邊商品,從來只囤積不賣出。買的書堆滿地板,讀完的恐怕不足十分之一,還扯什麼「還藏書以自由」、「恢復書籍的真正價值」之類的鬼話。吃得太摳門,結果被送進醫院花了一大筆錢,這樣的蠢事也有。總之,我是個沒救的笨蛋。
餘下的一半責任則完全在社會一方,絕不能賴在受害者身上。證據要多少有多少,但要緊的只有一個:我的文字沒人讀。
高中時我便決心靠文章過活。不是堅信自己文才出眾才做此打算,而是因為除此之外別無所長。對我來說這是生存的唯一手段。醉心於理論與寫作,大學四年我竭力避免與人交遊,與昔日好友漸漸疏遠;改學文學的事情敗露,同父母決裂。陷己身於不仁不義,落得個衣食住無著,最終化為一頭獨來獨往、餐風飲露的猛虎。
我到底沒有成為作家,至少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我不給雜誌投稿,因為覺得那些雜誌都莫名其妙。我不寫網絡文學,並非出於一種「文人」的高慢,單純不會寫而已。我只會寫切實發生在身邊的事,沒有體驗過的東西(不論是在實存還是想像的層面上)既然毫無實感,就沒有寫的價值。
這也不干那也不干,怎麼賺錢餬口?懷著「非此路不可」的想法一頭轉進文學這條岔道,鑽入名為現實的密林中,我才感到茫然無措。
羅生門下待著雨住的家將,想必便是如此心境吧。但彼時我少不更事,心境迂闊,在被社會毒打到不能自理前暫無拋棄理想的念頭。於是打定主意,開個公眾號權且發些文章。不指望靠這個吃飯,先做些兼職養活自己。現在想來,墮落都不徹底,還要順著一根搖搖欲墜的蜘蛛絲掙扎著向上爬,實在悲哀得很。
至此應該不難發現,我有多愛用「不」、「沒」、「無」這類否定判斷詞,出現頻率高到太宰或許都會覺得過分消極。不是刻意要表現得十分厭世,事實上日常的我頗為樂觀:心情大好,吃頓金○門吧;感到煩悶,就出去散散步;窮極無聊,躺在床上發呆也不錯——就是這麼一個精神健全的人,寫出來的東西卻如此異常。
「謹案才子立言,總須大嚷三大苦難:一曰窮,二曰病,三曰社會迫害我。」將陰暗的行文歸因於此三大苦難總不會錯,剛才還在抱怨社會迫害自己呢——這顯然是耍無賴。除了自己,怪罪不了任何人。
我的拒人千里,同我無意識頻繁使用的否定句詞仿佛暗合著一般。不是這個,也不是那個…… 始終拒絕被明確劃定,也不許任何東西占據不斷游離的中心位置。可這個無法被填補的中心,呈現出更為絕對的「我」的形態。
二
因《尋找小糖人》而為人所知的羅德里格斯,我很喜歡他的歌。片中有一個長鏡頭:一身黑衣的羅德里格斯緩緩關上小屋的門,踩著地上分布不均、些許融化了的雪,在夕陽下的街道中踽踽獨行。這個片段叫人印象最深的是配樂《Street Boy》,羅德里格斯的冷冽又溫柔的嗓音伴著和緩曲調唱出的詞,深深打動了我——
“You go home, but you can’t stay. Because something’s always pulling you away.”
我愛散步。愛讀散步的文學。梶井基次郎的《檸檬》,不論讀多少遍總是會被這一段所感動:
「這實在令人擔憂。我指的不是已經確診的肺結核或者神經衰弱,也非猶如芒刺在背的債務,而是指這種不祥之感。無論是從前那些令我快慰的美妙音樂,還是那些華美詩文,哪怕只是一小段,我都不能平靜地坐下來欣賞。有時特意出去聽人家放留聲機,可是只聽了兩三小節便如坐針氈。總之,就是有某種感覺令我坐立不安,所以才終日在街頭游盪。」
在我公眾號為數不多的讀者中,曾有人問我為何不去更大的平台發表作品。他是教科書式的文學青年。和他的幾次交流僅限於文學討論,他字里行間透出的青澀與朝氣叫人羨慕。
「我寫的東西發在那也沒人看。」
「終究還是有人看的吧。總比現在讀的人多。」
「無所謂。耐不住寂寞就別搞文學了。」
「無所謂是否獲得認可,那寫作是為了什麼?」
我一時無法回答。
「況且我也不覺得你是真心不在乎,要是耐得住寂寞的話幹嘛和我聊天。」
如果說之前無法作答是因為辯詞太多不知從何選擇,那麼這一回我是真的語塞了。
我真不在乎名聲嗎?真能將批評與贊美拋諸腦後嗎?苦心構造的堅牢建築,被人手指輕輕一點就轟然倒塌。有夠難看的。
不是沒質疑過文學於我究竟意味著什麼,對於創作而言這是反思與批評的一環。但他提出的問題,則是沿著肌理精準地剖開我的皮膚,把纖弱敏感的肉體赤裸裸、血淋淋地暴露在空氣中。
享受貧窮給我帶來的富足,大啖寂寥與我的充實。我一直在製造這樣的幻象。貧窮只是貧窮,孤獨只是孤獨而已!我似乎應該這樣猛地喚醒自己。可這僅僅是逃進另一個幻象中罷了。
遞到嘴邊的吐司麵包,剛想動口,突然變成了被撕下的一疊書頁。我硬著頭皮咬下去,兌了水塞進空盪盪的胃里。可誰吃書能填飽肚子。
所以,不吃這口飯了。我賣掉了所有藏書,關掉了本就沒人在乎的公眾號,找了一份與文學毫不相乾的工作——這不意味著我拋棄了文學。
恰恰相反,在離它最遠的地方我發現了文學的故鄉,文學分明在這里恣意生長。我只是嫌它的果難以下咽,無法充飢。
文學也沒有拋棄我,至少它還津津有味地嚼著我的腦袋呢。
來源:機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