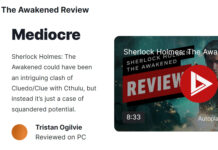The Dark Demon,By Robert Bloch
譯:柯索提亞
正文
埃德加·戈登之死的真實故事從未刊登在報刊上。事實上,除我以外,沒有人知道他的死訊。他的駭人傳說曾在世界各地的奇幻愛好者中廣為流傳,可如今人們卻已經逐漸忘卻了這位古怪的邪惡天才。這也許得歸功於他生涯末期的最後幾部作品中噩夢般的暗示以及反常的幻想,這也使得他與大眾漸行漸遠。許多人認為這些措辭夸張的大部頭出自狂人之手,甚至連他的通訊記者也拒絕對他寄給他們的一些尚未發表的作品評論。此外,他鬼祟古怪的私生活也並未令在他生涯早期有所成就的歲月里所熟知的人抱有好感。雖說事出有因,但他和他的著作註定要被一個總是忽視自己無法完全理解的事物的世界所遺忘。如今,所有能憶起他的人都認為戈登只是失蹤了。考慮到他特殊的死亡方式,這樣反而更好。但我決定將真相公之於眾。我跟戈登很熟。老實說,我是他最後一個朋友,在他人生的最後一刻,我也在場。我對他為我所做的一切心存感激,我想像不出除了將他可悲的精神脫變與淒慘的死亡真相揭露於世外還有什麼更恰當的方式報答他。
如果我能闡明這些事實,將戈登的名字從不公的精神錯亂的污名中抹去,那我也不算虛度一生了。為此,我特此聲明。
我深知這一故事不會令人信服。其中有一些——我們或許應該說,「聳人聽聞的方面」?——使我在將他的案子公諸於眾時所採取的步驟進行了辯論。但我還欠他一筆債;更確切地說,是向曾經的天才埃德加·亨奎斯特·戈登致敬。因此,這就是我們的故事。
我第一次遇見他一定是在六年前。在同一個通訊記者在一封信里無意中提及這件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們是老鄉。
當然,我以前聽說過他。作為一名前程似錦(有時也日暮途窮)的業余作家,他在各種迎合我喜愛的奇幻文學雜誌上刊登的作品對我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並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幾乎所有讀過這類雜誌的讀者都知道他是一個非常博學的恐怖小說作家。他的風格為他在這一小片領域里贏得了聲譽,盡管即使在那時也有部分人嗤笑他的怪誕主題。
但我非常欽佩他。因此,我不約而同地到戈登家進行了一次社交拜訪。最後,我們成為了朋友。
出人意料地是,這位隱居的夢想家似乎很喜歡我的陪伴。他離群索居,沒有結交的熟人,除了寫信外,與朋友沒有任何聯系。然而,他的寄件名單卻長得驚人。他與全國各地的作家和編輯書信往來;還有未來的作家,有抱負的記者,各地的思想家和學生。一旦他的矜持顯露,便很樂意與我為伴。不用說,我也自然欣喜。
埃德加·戈登在接下來的三年里為我所做的一切永遠無法被充分地陳述。他干練的幫助,善意的批評和親切的鼓勵終於使我成為了一名作家,從那以後,我們共同的興趣使我們之間的關系愈加緊密。
他所透露的關於自己的精彩故事令我震驚。然而,我可能從一開始就對此有所懷疑。
戈登是一個高挑,瘦骨嶙峋的男人,蒼白的面孔和深陷的雙眼表明他是一位夢想家。他的言語之間流露出詩意與深邃;他的行為舉止仿如夢游般緩慢編織,仿佛指揮他機械運動的靈魂來自陌生遙遠的彼方。因此,我可能已經從這些跡象中猜到了他的秘密。但我並沒有,當他第一次向我透露的時候,我倍感震驚。
因為埃德加·戈登所有的故事均源自夢境!故事的情節,背景和人物都是他自己絢麗多彩的夢境生活的產物——他所要做的就是把入夢後的幻想撰寫於紙。
我後來了解到,這並不是一種完全獨特的現象。已故的愛德華·盧卡斯·懷特便聲稱他寫過幾部完全基於夜間幻想的作品。H.P.洛夫克拉夫特亦創作了諸多受類似來源啟發的精彩故事。當然,柯勒律治也曾夢見了他的《忽必烈汗》。心理學上有許多例子可以證實夜間靈感的可能性。
但戈登的供認之所以如此反常是因為他的夢境狀態會伴隨著古怪的個人特徵。他非常嚴肅地宣稱,他可以隨時閉上眼睛,讓自己放鬆到進入一種昏昏欲睡的狀態,然後繼續無休止地陷入夢鄉。甚至無關白晝或黑夜;也不知他睡了15小時還是15分鍾。他似乎特別容易受到潛意識的影響。
我對心理學的膚淺研究使我認為這是某種自我催眠,他的打盹實際是催眠入睡的一個特定階段,在這一階段,受試者可以接受任何暗示。
在我的興趣的驅使下,我時常就這些夢境的主題向他進行詳細地詢問。當我告訴了他關於這個項目的想法後,他很快就欣然接受了。
戈登的幻想與普通的弗洛伊德式的升華或壓抑類型相去甚遠。它們沒有任何明顯的潛藏願望模式或是象徵性的表達。它們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都極度異常。他告訴我他是如何夢見自己著名的石像鬼故事;夢見造訪遠在神話般的宇宙邊緣的漆黑城市,以及超越一切物質的無定形王座上與他交談的怪異居民。他對可怖的奇怪幾何形狀和超越地球生物的生命形式的生動描述使我相信他的思想絕非尋常,其中一定藏有這種詭異和不安的陰影。
更離奇的是,他還能輕松記住生動的細節。對他來說似乎根本沒有什麼模糊的心理概念;他甚至能回憶起幾年前所經歷的夢境的每一處細節。有時,他會以「言語無法使事物變得清晰易懂」為藉口以掩飾自己描述的部分內容。 他堅持認為自己看到並理解了許多無法用三維方式描述的事物,而且能在睡夢中感知色彩和感官。
對我而言,這自然是一個迷人的研究領域。在回答我的問題時,戈登曾向我透露,自記憶中最早的童年時起,他一直知曉這些夢境,而最初的夢境與最後的夢境之間唯一的區別就是感受到的強度。他現在聲稱自己的印象更強烈了。
夢境的場景出奇地固定。幾乎所有的夢境都發生在他以某種方式認知到的,我們宇宙之外的場景中。漆黑石筍構成的山脈;死陽坑谷的峰巒和圓錐體;群星中的石城;這些都早已司空見慣。有時,他和其他星球上不可名狀的種族一同行走或飛翔,蹣跚而行或以難以描述的方式移動。怪物也是他能且願意描述的,但有些具有智慧的生命只存在於氣體,朦朧的狀態,還有一些不過是一種非凡力量的化身。
戈登總是發現自己身處於每一個夢境中。盡管他繪聲繪色地描述了這些駭人,常常令人不安的冒險,但他認為這些夢中幻像不能算作噩夢。因為他毫不畏懼。事實上,他有時會經歷一種離奇的身份逆轉,因為他認為自己的夢境才是現實,而他的清醒生活才是虛幻之物。
我盡可能深入地詢問他,但他沒有提供任何解釋。他的家族史在任一方面都很正常,雖說他的一位祖先曾是威爾斯的「巫師」。他本身也並非什麼迷信之人,但他必須得承認,他的某些夢境的確與《死靈之書》,《蠕蟲的秘密》,《伊波恩之書》等書中描述的片段出奇地吻合。
但早在他的大腦促使他閱讀上述提及的晦澀難懂的巨著之前,他就早已經歷過類似的夢境。他堅信,在他了解到它們在亘古傳說中半神話般的存在之前,他就曾窺探過「阿撒托斯」和「猶格斯」。他能夠從與這些寓言般的存在的真實夢境的接觸中描述「奈亞拉托提普」和「猶格·索托斯」。
他的這些陳述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後我不得不承認,我無法給出合乎邏輯的解釋。他本人對待這件事非常嚴肅,我從未想過諷刺或嘲笑他的觀念。
倒不如說,他每寫一篇新故事時,我都會非常認真地詢問他激發這一故事的夢境,幾年來,他在我們每周的會面時都會向我講述這類趣事。
但正是在這段時間,他進入了那個使他備受冷待的寫作階段。迎合他作品的雜誌開始以過於恐怖和不符大眾口味為由拒絕接受一些原稿。他初版的第一本書《夜魔》因其主題的病態而暴死。
我感覺到他的風格和題材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他不再遵從傳統的情節發展動力。他開始用第一人稱來講述他的故事,但敘述者並非人類。他的用詞選擇清晰地表明他的過度興奮。
作為對我關於引入非人敘述者的構思的回應,他認為一個真正的怪奇故事必須從怪物或獨立存在本身的角度講述。這對我而言並非什麼新理論,但我確實反感他如今的故事中強調的那種駭人的病態注釋。此外,他筆下的非人角色也並不是什麼尋常的食屍鬼,狼人,亦或是吸血鬼。相反,他展現出了怪異的惡魔,誕自繁星的生物,甚至還寫了一篇關於某種無形智慧生物的故事,名為《邪惡根源》。
他的這種特質不僅形而上,晦澀難懂,且對於任何正常的思想概念來說都是瘋狂至極。他所闡述的構思及理論變得極度褻瀆。想想他在《混沌之魂》中的開場白:
順便一提,《混沌之魂》是他四本私人出版的著作中的第一本。這時的他已經完全失去了與正規出版商和雜誌的聯系。他也拋棄了大部分通訊記者,從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一些古怪的東方思想家身上。
他對我的態度也在逐漸改變。他不再像我闡述他的夢境,也不再概述情節和風格的構思。我也不再經常拜訪他,毫無疑問,他斷然拒絕了我的建議。
考慮到我們之前的幾次會面,這樣或許最好。一方面,我厭惡他書房的一些新藏書。單就研究而言,一些神秘學的著作倒還能接受,但夢魘般的神秘《屍食教典儀》和《Daemonolorum》對於健康的精神狀態毫無益處。而且,他最後的私人手稿都過於瘋狂。他對待某些神秘傳說的嚴肅態度並未給我留下多好的印象;他的一些想法太過極端了。要是換做在另一個世紀,他如果敢表露出這些著作中一半的觀點,肯定會因巫術而受到迫害。
不知怎的,還有其他一些因素令我樂意避開這個人。他總是選擇做一個寡言少語的隱居者,而這股隱士的傾向似乎明顯地增強了。他跟我說,他再也不出門了;甚至不會在院子里散步。而且每周都會有食物和生活必需品送上門。到了夜晚,他只在大廳的書房里放上一盞小燈,除此之外他不允許有任何光源。他自願選擇這種固化的生活方式。並說要把所有的時間都花費在睡覺和寫作上。
他變得更加瘦削,臉色也愈加蒼白,行為舉止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神秘而輕柔。這讓我想到了毒品:現在的他看起來就像個典型的癮君子,但他的眼睛並不是大麻吸食者那種特有的灼熱火球,鴉片也沒有影響他的體格。隨後我自己也開始懷疑是精神錯亂;他那超然的說話方式及對任何話題都拒不深入的可疑態度,可能正是出於某種神經紊亂。他天生就容易受某些精神分裂特徵的影響。也許他真的瘋了。
當然,他最後說,他最近的夢境內容傾向於證實我的理論。只要我還活著,就永遠不會忘記關於他夢境的最後討論——原因很快就會明了了。
他帶著某種不情願的思緒向我透露他最後的故事。沒錯,它們和其他作品一樣,都是受夢境啟發的。他撰寫這些故事並非為了供大眾消費,編輯和出版商也會因此大發雷霆,但他才不在乎。他會撰寫這些故事是因為自己被驅使。
是的,驅使。顯而易見,肯定是他夢中的怪物所為。他不願談及這件事,但我們既然是朋友……
我不停敦促他。但我現在真希望自己當時沒這麼做;也許我還能免受接下來這些知識的影響……
埃德加·亨奎斯特·戈登坐在寬大的窗前,沐浴著蒼白月光,眼中閃爍的慘白光芒堪比不潔的月光……
「我現在了解我的夢境的含義了。我從一開始就被選為彌賽亞;我是他命令的傳達者。我不是在信教。我指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上帝』,人們會用這個詞來指代任何他們無法理解的力量。我指的是『幽暗者』。在我給你讀的那些書中有提到祂;他們稱祂為『惡魔信使』。但那都是寓言。祂並不邪惡,因為世界本便沒有所謂的邪惡。祂不過是某種異界生物。我將成為祂在地球上的傳令者。」
「別那麼慌張!我沒有瘋。你以前也都聽說過——古時的人類是如何崇拜那些曾實際顯現於地球的力量的,就像幽暗者選擇了我一樣。這些傳說無疑荒唐至極。祂並非毀滅者——祂僅是一種希望與人類的思想建立精神上的融洽關系的高級智慧生物,以便令人類與那些『另一邊』的東西進行某種交流。」
「祂在夢中與我交談。祂讓我書寫故事,並將它們分發給那些知情者。當時機成熟時,我們將共同聯合,揭露一些人類在夢境中只能猜測甚至察覺到的宇宙奧秘。」
「這就是我頻繁入夢的緣由。我被選中成為學者。這就是夢境向我呈現『猶格斯』和其他一切事物的緣由。現在,我正為我的使徒之職做准備。」
「我不能再向你透露更多了。我現在必須大量寫作,睡眠,這樣我才能學得更快。」
「『那這個幽暗者是誰?』我不能再向你透露更多了。你肯定認為我瘋了。我相信你有許多支持這一論點的擁護者。但我真的沒瘋。這點毋庸置疑。」
「你還記得我曾告訴過你我的夢境變得愈加強烈嗎?很好。幾個月前,我做了一些不同尋常的夢。我身處黑暗——不是你認為的那種尋常的黑暗,那里是位於宇宙之外的至暗之域。它根本無法用三維概念或思維模式來描述。黑暗中傳來一種聲音,一種類似呼吸的律動,因為它是活的。當我看見祂的時候,我只是一種毫無軀體的精神。」
「祂從黑暗中現身——與我交流。不是通過語言。我很感激之前的那些夢境,它們讓我適應了視覺上的恐懼。否則我將永遠無法忍受祂的存在。祂選擇的那副非人形體駭人至極。但是,一旦你理解了,你就能意識到這個形體就像那些愚昧之人編造的關於祂和其他事物的傳說一般具有寓意。」
「祂看起來有點像中世紀的人們對惡魔阿斯蒙蒂斯的構想。漆黑的身軀覆蓋茸毛,長有似豬的鼻子,綠色的眼睛以及如兇猛野獸般的利爪和獠牙。」
「不過,在祂與我交流過後,我便毫不畏懼。祂會以這副形體顯現不過是因為古老歲月中愚昧的人們堅信祂會是這般模樣。大眾信仰對不可名狀之力具有一種獨特的影響。人們會認為這種力量污穢不堪,便使它們呈現出邪惡的一面。但祂其實沒有惡意。」
「我希望我能復述祂向我講述的一些事物。」
「從那時起,我度過的每一個夜晚都能遇見祂。但我承諾過在那一天到來之前絕不泄露任何信息。現在我領悟了,我不再有興為這些芸芸眾生寫作。恐怕人性對我而言早已毫無意義,因為我已經掌握了位於另一邊的那些步驟——以及如何實現它們。」
「你可以遠離我,也隨你怎麼嘲笑我。我所能說的是,我的書中沒有絲毫言過其實之處——而它們只涵蓋了潛藏在人類意識之外的終極啟示的極微一瞥。但當祂的約定之日到來時,整個世界就會了解真相。」
「在那之前,你最好離我遠點。我現在不能受擾,每天晚上,這種印象越來越強烈。我現在每天睡18個小時,有時是因為祂希望我能了解更多知識;在准備過程中需要學習的東西太多了。但當那天到來時,我將成為祂向我許諾的神明,我將以某種方式成為祂的化身!」
這些就是祂的獨白的內容。之後不久我就離開了。我無言以對,也無能為力。但後來我對他的話想了很多。
可憐的傢伙,他已經和我漸行漸遠了,顯而易見,再過一個月左右,他就會達到崩潰的極點。我由衷地感到抱歉,並對這場悲劇深感憂慮。畢竟他是我多年的朋友和導師,而且他是個天才。一切都太糟了。
盡管如此,他還是有一個奇怪卻又合乎邏輯的不安故事。如果《死靈之書》可信的話,那當然符合他之前對夢境的描述,傳說的背景也肯定確鑿不移。我想弄清楚他所謂的幽暗者與奈亞拉托提普寓言或女巫儀式的「暗之惡魔」之間是否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但所有關於「那一天」和他成為地球上的「彌賽亞」的無稽之談實在過於荒謬。他說的幽暗者許諾自己成為祂的化身又是什麼意思?像惡魔附身這種古老的信仰一般只有幼稚的迷信之人才會相信。
我對整件事思考了很多。數個星期以來,我自己也做了一些調查。我重溫了戈登後續發表的新著作,與他以前的編輯和出版商的通信記錄,給他的老朋友們寫下的留言。我甚至親自研究了一些古老的魔法巨著。
然而,我並沒有從這一切中得到任何實質性的信息,唯有必須做些什麼來拯救戈登的意識愈發強烈。我非常擔憂這個人的精神狀態,我知道必須迅速採取行動。
因此,大約在我們最後一次會面三周後的一天夜晚,我離開家,開始步行前往他的住所。如果可能的話,我打算懇求他放下這一切;或者至少敦促他接受醫療檢查。不知怎得,我帶上了這把左輪手槍——某種內心的本能在警告我,我可能會面臨某種過激的反應。
無論如何,我把槍藏在外套里,一隻手緊緊握住槍托,穿過一些漆黑的街道,通向他位於雪松街的舊住所。
那是一個無月之夜,不詳的跡象預示著雷陣雨的來臨。預告即將落雨的微風早已在頭頂的黯淡之森中嘆息,偶爾閃過的幾道條紋狀閃電也正於西邊閃爍。
我的思緒一片混亂,被恐懼,憂慮,決心和潛在的迷惘緊緊纏繞。我甚至都沒想好見到戈登後該說些什麼,做些什麼。我一直在琢磨他在過去的數周時間里都發生了些什麼——他所說的「那一天」是否早已來臨。
今晚是五月前夕……
屋內一片漆黑。我敲了敲門,但沒人回應。門最終在我肩膀的撞擊下打開了。木頭碎裂的聲響被頭頂的第一陣雷聲掩蓋。
我沿著大廳向書房走去。周圍黯淡無光。我打開書房門。一個男人正躺在窗邊的沙發。毫無疑問,他是埃德加·戈登。
他夢見了什麼?是不是又夢見了幽暗者?那個「漆黑的身軀覆蓋茸毛,長有似豬的鼻子,綠色的眼睛以及如兇猛野獸般的利爪和獠牙」的幽暗者;那個許諾他成為其化身的幽暗者?
這就是他的五月前夕之夢嗎?埃德加·亨奎斯特·戈登以古怪的姿勢睡在窗邊的沙發……
我伸手觸碰電燈開關,但一道突如其來的閃電令我措手不及。它只持續了一秒鍾,但它的光亮足以照亮整個房間。我瞥見了牆壁,家具,桌上駭人的潦草手稿。
最後的閃光消失前,我用左輪手槍開了三槍。一陣新近的雷聲仁慈地掩蓋了駭人的慘叫。我自己也隨之尖叫。我沒有開燈,只是收拾了桌面上的文件,然後奔向雨中。
回去的路上,雨水夾雜著滴落臉龐的淚珠,每一次雷聲的轟鳴,我都以一種將死的恐懼的抽泣來回應。
我無法忍受燈光,我捂住雙眼,盲目地跑回自己屋內的安全地帶。在那里,我沒有閱讀帶回的文件,而是直接將其燒毀。我不需要這些,因為我不必知道更多信息。
這已經是數周前的事了。人們最後進入戈登的住所時,沒有發現任何屍體——只有一套看起來像是被隨意仍在沙發上的合身衣物。屋內其餘的一切都完好無損,但警方指出,屋內沒有任何可以作為戈登證件的文件表明他失蹤時帶走了它們。
我很欣慰他們沒有找到其他線索,如果不是因為戈登被認為是瘋子,我將很樂意保持沉默。我曾也以為他瘋了,所以我必須將一切公之於眾。我之後打算離開這里,我想盡可能地忘記一切。在這點上,我很慶幸自己沒有陷於夢境。
埃德加·戈登沒有瘋。他是個天才,是個善人。他在書中道出了真相——恐怖在我們周圍盤旋,在我們之間盤旋。
因為當閃電劃過房屋時,我瞥見了躺在沙發上的東西。也就是讓我開槍射擊的東西;讓我在暴風雨中抽泣的東西,也正是讓我確信戈登沒有瘋,只是道出了真相的原因。
因為附身的儀式已經發生了。在沙發上,躺著一隻穿著埃德加·亨奎斯特·戈登的衣物,形像阿斯蒙蒂斯的惡魔——一隻漆黑的身軀覆蓋茸毛,長有似豬的鼻子,綠色的眼睛以及如兇猛野獸般的利爪和獠牙的生物。那正是埃德加·戈登夢中的幽暗者!
END
來源:機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