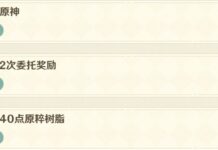賽博利亞,虛擬空間里的各色生活
道格拉斯·拉什科夫
1994年紙質版前言
我寫完這本書的一年內發生了很多事情,多得遠超平時。感謝像電腦,調制調解器,互動媒體,英特網等技術,我們不再依賴印刷品,或別人口中的話來探索最新的流行、創新或者發現。當一段故事出現在報亭的刊物中時,大部分知道內幕的人認為那已是「舊聞」,並早已忙著賣力處理下一批顛覆文化的發明和活動了。
賽博利亞(Cyberia)是我們最近歷史中一段非常特殊的時刻,是一切都看起來皆有可能的時刻。在這一時刻,一整個亞文化,正如初次興奮嘗試虛擬現實(Virual Reality)的小孩,見證了最新電腦技術和最隱秘埋藏的夢想、最古老精神真相結合的狂熱前景。這一時刻早於美國上線、兩千萬網民、連線雜誌、比爾柯林頓和信息超級高速公路。但這一時刻預見得更遠、更多。
這本書不是關於一切「賽博」(Cyber)人和「賽博」事物的調查,而是一場新生文化之旅,我有幸能親歷其中。回想起來,這麼多曾經荒誕的想法如今被人們接受,成為真理,這很讓人驚訝,同時,看到許多對未來最樂觀的估計離實現又那麼遙遠,難免痛心。
賽博利亞追隨眾生,翻譯了第一批少數意識到我們文化將要躍入未知的人們的經歷。其中有些人野心勃勃期待的未來,並且大獲成功,如今已家喻戶曉。而有些人則飽受災禍。還有些人完全淡出視野,他們對賽博利亞復興的貢獻已完成。
本書中的人物,以及世界上成千上萬與他們相似的人們,都了解科技對我們文化、思想系統、精神信仰、甚至是生物演化的影響。對於文明的未來,他們仍然以最樂觀和最前沿的眼光審視著。當我們越來越接近賽博利亞人藍圖繪制的交感虛擬現實,他們對前沿生活的影響與其餘人愈發相關,也更有意義。
道格拉斯·拉什科夫
1994,紐約市
引言
漫遊西西弗斯學習曲線
發傳單給我的那個小孩一定以為我比實際看上去更年輕或開明。或者他從一開始就注意到我了。當然,我在大學里做了一點「實驗」,並且稍微拓寬了自己的世界觀。但我還沒准備好沉浸到如此奇怪、如此具有影響力的亞文化中。
傳單上分形強化的「地圖點」展現出一個巨大的非法組織——「烏鴉」,其中成千上萬的名流服用精神藥物,隨著電腦生成的音樂起舞,他們談話的方式表明現實早已與自己幻象的投影重疊。不是什麼大事。波西米亞人這麼說話已經很多年,乃至很多世紀了 。問題是,在他們當中呆了幾個月以後,我開始相信他們了。
一名受人尊敬的普林斯頓數學家迷上了迷幻藥,在喜馬拉雅山洞中沉思了好多年,腦子神遊天外,然後,又回到大學,致力尋找能夠描繪自己迷幻體驗形狀的方程式。他想出的方程式能比以往更准確地預測天氣甚至股市。
舊金山的三個孩子帶著一台攝像機和一台壞掉的酒店門卡制卡器,成功騙過銀行取款機,取出了別人的現金。
一套全新的電腦會議系統讓人完全沉浸在「虛擬社群」中,以至於另一種人格取代了自己的精神力,失去了自我掌控,隨機向「在線」女性求歡。
一名科幻作家,見證了共生催眠中的孩子在電子遊戲中的奇遇後,發明了一個虛擬現實「賽博空間」——電腦產生的「集體幻覺」,其中每個人的想法完全展現,而現實本身以腦電波形式展現。
於是,在一個自我實現的奇異預言中,刻意設計的現實科幻概念開始成為一種被認可的信念,而不僅限於在夜晚節日里舞蹈的孩子們。科學家、程式設計師、作家、音樂家、記者、藝術家、活動家甚至是政治家都採納了這一新範式,而且還想變成你的範式。
現實之戰始於數碼互動領域。
我們的信息、錢財和通信越來越依賴於電腦和電子媒介,讓我們成為容易攻擊的目標,即便我們不願意成為受試者,我們仍然參與了本世紀最奇怪的社會實驗之一。我們被要求在一個全新的賽馬場——電子信息領域花費越來越多的時間。雖然我們正漸漸習慣這一點,但這一領域和我們生來熟知和熱愛的現實截然不同。它是一個無垠的宇宙,其中人們可以跨越時間和地點,自由互動。我們可以通過電話線發送傳真「文件」,跨越不同國家同時打二十個視頻電話,甚至於通過像虛擬現實這樣的新科技「觸碰」千里之外的人,在虛擬現實中,世界正如你所夢寐以求的那樣展現在你面前。
比如說,許多這些電腦程式和數據圖書館以網絡方式建構,其格式稱為「超文本」。為了了解一名畫家,電腦用戶從某一特定博物館開始。在畫家名單中,他也可以選擇一幅特定的肖像。之後,他可以尋求肖像本人的生平信息,從而揭示他的族譜。並一直沿著族譜探索到現在,之後跟著家族分支找到美國的移民政策數據、紐約的不動產發展乃至於倫敦東區的雜貨區。在超文本電子遊戲中,玩家可以扮演偵探,搜尋房間。而這個房間里滿是櫃子和抽屜。選擇一個抽屜。打開一看,里面是一張便簽,點擊它,文本顯現。閱讀便簽,就看到一個名字,選擇名字,看到一張圖片。圖片上的物件是一輛車。選擇車,便身處車中,穿越街區。看到一棟有趣的房子,走進去…….
也許這並沒有那麼讓人嘖嘖稱奇,這些科技花費了數十年才生根發芽,而我們當中很多人已經習慣了它們的運作方式。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在舊金山遇到了第一批人,他們聲稱自己不需要電腦,就能體會到相同的無垠超文本宇宙。對他們來說,可以通過藥品、舞蹈、精神手段、混沌數學和異教徒儀式進入賽博空間。就像登錄電腦一樣,他們進入這樣一種意識狀態,在那之中時間、距離和身體限制都失去意義。人們相信他們在這些領域中穿梭,正如在電腦程式或者電子遊戲中穿行一樣,不再受到線性和物理現實規則的束縛。不僅如此,他們說,我們的現實本身在科技的幫助下,也將要大規模躍入這一嶄新的超文本維度。
通過遞給我那張命中註定的宣傳單,這個舊金山青年讓我再也不能無視如下的現象:越來越多相當聰明,甚至樂觀的人,正為自己還有我們其餘人准備新科技所能帶來的最狂野的可能未來前景。我越是和這些人待在一起,這些前景就看起來不再那麼狂野。無論轉向哪個防線,結論始終相同。在最頂尖研究所中的量子物理學家們一致認同,構成物質本身的最微小粒子已不再遵從線性方程的預測。相反,它們以不連續的形式跳躍,消失、重現、突然獲得或者失去能力。數學家也得出同樣結論:自歐幾里得第一次在紙莎草上畫下三角形以來,那種平滑的幾何模型也已過時。他們反倒用電腦製造迷幻的佩斯圖案,認為這些圖案更能反映現實存在的自然。
誰最先談論這一切?在地下俱樂部聽著電子音樂起舞的孩子們,他們的結論似乎就是現實自身觸手可及。夢想可以成真。
這也許很難被認真對待;對我來說一開始是這樣的。但我們只需要轉向現實的仲裁者——主流科學家——就可以證實這一點。觀察現象的能力,他們現在相信,已經和現象本身不可分離。這些量子物理學家和系統數學家已經不再相信存在的物質解釋,轉而認為現實適應對它們的預期,反映出觀察行為本身會改變世界。正當他們愈加仰賴電腦,他們的懷疑愈發地被證明了:這不是一個可以還原為簡潔的方程式和簡單答案的世界,而是一個相互依賴的無限復雜序列,這里遙遠位置的微笑改變可以產生全系統范圍內的影響。
當電腦從現實世界的觀測中處理數據時,他們並不產生簡單的線性有序存在的曲線,而是輸出相位圖和圖表,其螺旋錯綜復雜,好似古代馬賽克畫、珊瑚礁或者幻覺。當整個歷史、生物和星際事件的排列通過現代數學發現重新分析時,它指向這一時期——世紀之交——正如人類躍出歷史總體跳入某種無盡的維度。
這一維度可能的模樣來自電腦黑客和迷幻劑旅行者,他們認為自己不是人類活動的極端,而是創新思考者,協同著把最新的科技和先進的精神體驗帶到普羅大眾的客廳。迷幻劑可以為任何敢於冒險的使用者提供薩滿式的體驗。這一體驗讓使用者認為被普遍接受的現實是武斷的東西,然後去想像從過時的思維系統、機構和神經官能症解放出來的世界的可能性。同時,控制論經驗使任何年紀的人都可以去探索一個全新的電子圖景。只需要用一台個人電腦和路由器,任何人都可以接觸數據網絡。電腦交互新科技諸如虛擬現實,承諾將數據網變成一個不僅是意識可以接觸,而且身體也可以進入的地方。
你將要遇到的人們把數據網絡的發展解釋為全球大腦的硬連線。這將是「蓋亞」發展的最後階段,地球本身作為生命體,而人類則是里面的神經元。作為電腦程式設計師和迷幻劑勇士一同發現「全為一」,出現了一種共同的信仰,那就是人類進化是有意識的進程,構建意識下一個維度的家園。
我們需要一個新詞來表述這一無垠領域。這本書中的孩子們稱之為「賽博利亞」。
賽博利亞是商人們開電話會議要去的地方,薩滿勇士們離開身體時去的地方,「酸屋」舞者感受致幻酸液極樂時去的地方。賽博利亞是每個宗教神秘神諭暗指的,每種科學的理論區間和每種想像的最狂野推測的地方。然而現在,不像歷史中的其他任何時候,賽博利亞被認為是觸手可及的。我們前現代文化達成的科技成就,伴隨著古代關於精神的想法的重生,讓越來越多的人認為賽博利亞是人類很快就會達到的維度平面。
但即使是我們當中從未進入俱樂部、物理實驗室或者電腦公告牌的人,也正越來越多地接觸到動搖我們最深信仰的文字、圖片和想法。賽博利亞人的範式更少依賴於結構和線性流程,更多依賴於組織上的體驗和一個個瞬間感受的新藝術和娛樂,從而進入到了我們毫不懷疑的意識中。角色扮演遊戲,比如說,沒有開頭和結尾,而是仰賴其玩家的創造性,他們一同經歷復雜的幻想,嘗試他們今後會在生活中用到的策略,因此他們的生活變得愈發相似於遊戲角色狂野漫長的冒險。同樣,賽博利亞藝術和文學拋棄了《星際迷航》和《2001太空漫遊》中干淨的線條和平滑的表面,而採用骯髒的、後城市風格的《蝙蝠俠》、《神經浪遊者》和《銀翼殺手》中的現實主義,其中電腦不會簡化人類問題,而是暴露甚至強化我們邏輯系統和社會工程系統中明顯的錯誤。
不令人驚訝,傳統主義者對這一表達的反應是劇烈的,且充滿恐慌。賽博利亞人質疑的正是現實本身,是控制和操縱想法的基礎;而且隨著電腦網路技術進入更多賽博利亞人的手中,歷史的權力中心遭遇挑戰。一個聰明的年輕黑客只要有足夠的時間,可以侵入世界上幾乎任何電腦系統。
同時,diy科技和一個巨大的飢餓媒體帝國種下了自己毀滅的種子,邀請私人公民通過雜誌、有線電視節目和互動電視參與進來。電視和它緊密的公眾關系製造催眠咒語被破解了,隨著人們學會破壞和重組本應用來說服他們的圖像。結果就是大部分人口獲得了重新評估之前被接受的政策和偏見的自由。
使用媒體「病毒」,有政治傾向的賽博利亞人進入數據網絡,以光速傳播公開挑戰虛偽和無邏輯的社會結構,於是使得它們變得無力。
一個新的科學範式,一次新科技上的飛躍,一種被創造出來的新藥,都是我們今天所目睹的,許多人都認為是新的文藝復興中的一環。我們的時代和過去的文藝復興當然相似:電腦和印刷機,lsd和咖啡因,全息圖和透視畫,輪子和宇宙飛船,農業和數據網絡。但賽博利亞人不止把它們當作傳統想法的復興。他們相信我們現在的時代會把人類經驗的形式升級到未知的、超越維度的領域。
這樣相信所有這些的人們,目前正處於流行文化的最前沿。但正如我們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見證的那樣,邊緣文化的信仰可以向上滲透到年輕一代直至主流。事實上,我們很快就可以推斷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和迷幻時代對流行文化最為重要的一個貢獻就是這樣一種想法,那就是我們任意選擇了自己的現實。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裝備了最新科技、熟悉賽博空間,並且敢於探索意識未知領域的賽博利亞反文化的主要目標是有意識地和主動地重新選擇現實。
這本書旨在通過這種觀點,亦即賽博利亞,指明方向。這是一個參與,或者至少是趕上一場能給夠重塑現實運動的機會。我們將在接下來的章節中遇到賽博利亞探索者們,他們展示出了自己富有人性的樂觀主義、聰慧和脆弱。正如同任何新世界的先驅一樣,他們也忍受著同樣的恐懼、挫敗和失敗,正如那些呆在後面從熟悉的安全區觀望的人一樣。這些不是媒介人物而是真正的人,在現實的邊緣為了生存,發展著他們自己的處事手段。
不管我們是否註定要飛躍進下一個維度,許多人相信我們熟知的歷史將要終結。賽博利亞人的美學、發明和態度將會很有可能像自動櫃員機和mtv一樣無法忽視。我們不管怎麼樣,總歸要面對時間的流逝。這引導著我們感受賽博利亞。
7
第一部分
計算機:宅男的復仇
第一章
數據流導航
克雷格發現「地下墓」時只有七歲。他的父母帶著自己拜訪他的叔叔,大人們坐在廚房談論沙發價格和當地政治,而年輕的克雷格·內多夫,日後當局會將其認定為危險且有破壞性的黑客,發現了第一個通向賽博利亞的傳送門:一款叫《冒險》的電子遊戲。
正如和家長一起在梵蒂岡旅行時的小孩兒,會獨自走開探索公眾道路底下的古老神秘迴廊,克雷格開始了自己的電子「尋夢之旅」。正當他在遊戲中探索著各種螢幕畫面,並收集魔法道具時,克雷格發現,自己能夠使用這些道具來「看」任何其他人都不能看到的遊戲部分。即使他已經完成了遊戲早期所有的必要任務,他還是被吸引著用自己的新視角繼續探索。克雷格不再熱衷於單純贏得遊戲,他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做到。現在他想身臨其境。
「我能夠穿過牆,走進一間並不存在的房間,」某天深夜,克雷格通過加密電話線路對我解釋說,「那不在遊戲說明里。也不是遊戲的一部分。而那個房間有一條訊息。那是遊戲製作者發出的訊息,閃耀著黑色和金色。」
克雷格的聲音變弱了。休奇(Huge),我的助手和電話網絡連機藝術家,調整了他的耳麥,檢查了一下儀表盤,然後點頭示意說,對話仍在錄音中,情況滿意。克雷格不願意跟我分享那個訊息說了什麼,只是提到那激勵著他成為了賽博利亞人。「這個過程,發現某些沒有寫下來的事情,發現一些本不應該被知道的事情,讓我很感興趣。我在許多其他遊戲中也搜尋了,並且用盡我能想到的所有手段,甚至包括擺弄電源線和暗盒,來看看會發生什麼。那就是我興趣開始的地方……然後我得到了一台蘋果電腦。」
在那之前,賽博利亞被限定於電視螢幕另一邊,現在已經擴張到電腦螢幕另一側。在名為「貓」的電話連線的幫助下,克雷格連接到了計算機和通信的全球系統中。現在,相比於探索電子遊戲的內部網絡,克雷格暢游在數據網絡世界的秘密通道中。
十幾歲時,克雷格·內多夫被逮捕了。他當時是「線上雜誌」(通過電話線在電腦之間傳閱的雜誌)《弗拉克》(Phrack)的編輯,他被指控發表(如果是合法的,就是「轉移」)一份危險、但價值七萬九千美元的程序文件,里面細致入微地展示了貝爾南方公司的911緊急電話系統(尤其提到了能夠追蹤來電的特徵)。在內多夫的庭審中,一名貝爾公司的員工最終揭示,所謂的「程序」,只不過是公司用戶花費不到三十美元就能獲得的三頁備忘錄。內多夫被緩刑一年,但他還在籌集捐款來償付十萬美元的訴訟費。
但是當局、成人社會錯過了最關鍵的地方,大部分情況下都是如此。克雷格和他的同伴們並不感興趣於獲得和出售有價值的文件。他們並非在竊取信息,而是在數據中漫遊。在賽博利亞,計算機就是工具的隱喻;從一個系統黑進另一個系統,再到第三個系統,不過是為了發現秘密房間,以及從未有人涉足的秘密通道。互相連接的計算機網絡給正在成長的大腦們提供了電子-神經系統的終極拓展訓練。要面對這一人類意識的科技前沿,就意味著要重新評估信息、創造力、財富和人類關系的本質。
克雷格是這一新領域內年輕天才先驅的典型。他如此描述自己第一次看到的黑客行動:
「我真的不記得他怎麼做的了;我坐在那里看著他打字。但看著這些系統出現,就很有趣。我看到類似購物商場那樣的東西,那里有發熱的計算機,你甚至能打電話過去,查看它們的溫度設置。有幾台這樣的計算機連在一起。一個公司為不同的用戶運行恆溫器,如果外溫為82華氏度,他們會根據特定設置調節溫度。所以,當我們十三歲時,就已經談論著某一天調一下溫度,要麼過熱,要麼過冷,說不定很酷,但我們沒這麼干過。」
他們本可以做到,這才是最重要的。他們獲得權限。在賽博利亞,這就是游樂場探險。內多夫認為這就好比「你八歲時,知道你的哥哥和他朋友在林子里有一個小樹屋,或者妙妙屋,即使你明白你哥哥要是發現你在里面,可能會殺了你,你還是會和朋友去看看」。大多數孩子都是這樣開始黑客活動的,正如前幾代孩子們游盪在學校地下室走廊,或者拆了他們父母的電視機。但有了計算機,他們仿佛撞到了頭彩:那里有一整個世界——一個全新的現實,他們可以進入甚至改變它。賽博利亞。每一次新的打開都會發現一整個新世界,每一個世界都通向無數其它新世界。你並不只是到了某處,環顧四周,發現是死路,然後離開。湯姆·索耶和貝基·柴契爾被幾個蜿蜒的山洞迷住;賽博孩子們則闖進了無限復雜、值得一探的網絡。每一個新螢幕帶他們進入一家新公司、研究機構、城市、政府或者國家。他們可以從任何地方冒出來。這是一場永無止盡的旅行。
黑進廣闊的計算機網絡不僅是最具價值的賽博空間探索技術,還是賽博利亞中首要且最重要的隱喻。第一次,存在一個可以展現賽博利亞人激情的技術舞台:從單純的運動到精神迷幻,從重新設計現實到徹底顛覆一切。
破壞系統
大衛·特魯普在地下計算機界出名靠的是寫了一個叫「保鏢」的程序,這個程序幫助黑客們通過一系列復雜的長系統保持連接。通過另一個巧妙的通信系統故障,我們說話時他在明尼蘇達州的客廳沙發上休息。從他的聲音我我知道他在用免提,我聽到了他幾個朋友的聲音,他們也在房間里,打開啤酒,低聲表示同意他們的地方英雄特魯普。
「黑客的樂趣在於解決謎題。發現下一個角落、菜單或者密碼里面的東西。發現你能繞多少曲折。從計算機網絡到電話網絡,然後再回來。描繪世界網絡圖。我們看到密爾沃基發展自兩個系統,最終變成巨型網絡。我們和他們一起去了。到最後,我們可能能獲得比他們更詳細的網絡地圖。」
「保鏢」成了黑客日常生存裝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一種蠕蟲(一種鑽探用的計算機病毒),跟隨你一同黑進去。比如說我黑了某家工程公司的十五台unix(使用unix軟體的計算機)。每次我進入一台unix,我就會上傳保鏢程序。它會監視我和系統。它有系統操作員的名字。如果系統操作員(系統op,對付非法入侵者的看守方)或者其他能夠檢查系統的人登錄(通過他自己的計算機進入網絡),那麼『保鏢』就會閃爍一下警告標志(警告!危險!),然後終止你的活動。它還會給你發送一串你侵入的機器中下一個層級的數字。你最後會連接到你被困住之前的那個機器。這需要四五分鍾。效果很好,因為當你深入一組系統中,你很難觀察所有事,你的『保鏢』在系統操作員登錄時立刻帶你下線,趕在他認出你之前。即使他們只是登錄,你也已經走人。沒必要冒險。」
雖然真正的黑客之道是不破壞任何東西,大多數年輕人面對可以肆意破壞的權利,很難抵制如此誘惑。正如特魯普解釋的那樣:「大部分孩子會做他們知道的最具破壞力的事情。他們並不需要、想要甚至理解如何使用其中的力量。每個人總會破壞一個系統。」
某人在特魯普那頭表示懷疑,不贊同地咳嗽了一下。大衛糾正了他自己。沒必要承認他做了任何非法的事情,現在,有嗎?「我得說九成的人。每個人都有那種沖動,你懂嗎?『上帝,我獲得了系統全部的控制權——我可以做一個遞歸rm(移除東西的循環),然後和系統吻別。』更可能的情況是,某人製造一個小bug,比如說在每個人的密碼之前加一個空格(使得所有人都無法登錄),然後看系統操作員多久會發現。」系統操作員羅列密碼的時候,會發現密碼都是正確的,只是每一個前面都有個小空格。當操作者把用戶密碼和電腦顯示用戶應當有的密碼對應時,他們不會發現電腦版本上顯示出來的空格。這是對n次方公司的惡作劇電話。黑客不會戲弄電話另一頭的人,而是使「惡心西裝人」運行的大公司癱瘓。難以抗拒,尤其是當對方是一個監察著我們的公司時。一件嚇得特魯普暫時不敢再進行黑客活動的事情就涉及這麼一家公司。
「TRW是黑客們的聖杯。他們涉及所有事務,這也就是為什麼大家都想侵入他們。而公司聲稱自己無法被侵入,這也是大家都想侵入的另一半理由。你越是調查,就能看出他們越來越多的安全漏洞。他們沒有那麼糟其實。」特魯普的一個朋友驕傲地咯咯大笑。「那很難,因為你要掩蓋自己的痕跡,不是不可能的,只是要花時間,」特魯普解釋道。
「我記得TRW之前有個廣告說『TRW,讓明天更美好』。那就是他們的所有技倆,他們讓我們習慣於見到他們。因為他們涉足一切。他們往政府的所有系統里派「飛虎隊」(在系統里建立安全協議的專業計算機突擊隊),要麼是為了增加系統安全性,要麼是從頭建系統。他們在所有東西里都留了後門,可以操控一切想操縱的東西。他們很大,他們很壞。他們實際擁有的權力比他們應有的大得多,這也就是為什麼我盯上他們了。他們在機場安全、航空安全系統里都有「飛虎隊」。政府從TRW那里獲得軟體,然後升級也是靠他們(也有後門)。
「當我們一直追蹤到鎖眼衛星,然後說:『夠了』。我們有很好的資源,我們有可以假裝不存在的人才——他們有社保號、稅號等一切。但這一切有點嚇到我們了。我有一整套計劃可以繼續,但我們決定收手,把我們所有的TRW東西都丟了。我把它們給了一個朋友,埋在大西洋大陸架底某處。如果我叫他把它取回來,他會的,但如果我聯系他的時候使用了稍有不同的措辭,他就會消失……原因很明顯。」
大部分有目的的黑客活動沒那麼浪漫,只是為了獲得計算力量的系統權限。如果某人正在研究復雜程序或者系列計算,使用一些公司的龐大系統,花費幾分鍾、幾小時完成這一過程,顯然比在小小的個人計算機上花費數日方便得多。技巧在於在系統操作員發現干擾之前結束工作。正如一個黑客通過加密電子郵件向我解釋的那樣,「他們可能找到你了,這時候你跟他們還沒完,你還在研究另一些公司的事情。但如果你侵入了比如說二十個或三十個unix系統,你可以隨心所欲地出入並改變它們的順序。你總是看起來來自其他地方,他們就是在黑暗里射擊,你無法被追蹤到。」
這個黑客以像沖浪手那樣在湍流中翻滾和沖過管道的手段出入系統為傲。但是,正如沖浪手可能會為了現金、獎章和啤酒代言競爭,許多初入賽博利亞的年輕黑客憑借自己的技藝,很快被老闆給出的好處所誘惑。對年輕黑客最危險的可能不是來自法律,而是來自希望利用他們天賦的那些人。
我和一個稱之為皮特的十七歲哥倫比亞大學工程學生黑客進行了一場實時電話會議,國內的幾個其他黑客也一同分享了關於「工業黑客」領域的故事。因為大多數參與者相信自己的電話線有數個竊聽者,他們第一批回應通過螢幕上系列奇怪符號開始。當皮特啟動了密碼協議並且解碼了發進來的信息,它們看起來是這樣的(名字是我的):
#1: 純粹者
工業黑客是黑客的暗面。公司A雇傭你來放慢、破壞、攪亂或者偷竊公司B的R&D部門(研發部門)。比如說,我們可以讓他們的cadcams(計算機輔助軟體)的數學計算全部錯亂,所以當他們檢查電腦時一切看起來都很正常,一旦組合起來就全錯了。如果飛機引擎的所有部位都偏差了一毫米,那就飛不起來了。
#2: 搗蛋鬼
佛羅里達有一個傢伙在操作cadcam系統,他用的是盜版軟體。他很聰明,所以沒靠任何說明書就學會了使用。他工作了一年半,然後被無故解僱。他找到我們,讓我們把公司弄關門。我們說:「好的,沒問題」。Cadcam系統軟體公司給我們發了很多樣本。我們獲得了一些樣本,然後寫了一個簡單的彙編程序,只要一個人把盤放進去,然後打「安裝」或者「樣本」指令,它就會抹消整個硬碟。所以我們把它包好,送給德州或者反正就是軟體公司所在地的朋友,讓他用合法的郵戳寄到目標公司。於是乎,某人把樣本放進電腦里,公司只好再購買價值兩萬美金的軟體。而他們不能有怨言,因為我們抹消的軟體本來就是違法的。
純粹者
這沒什麼,只是私人恩怨。工業黑客是大買賣。大部分公司有專門的計算機咨詢專家來做這種事。但作為自由人,你可以被這些公司其中的一個雇傭為常駐顧問,比如說麥克唐納·道格拉斯讓你去副總統辦公室,給他們展示洛克希德情報系統,比如一個他沒見過的先進戰鬥機,然後你可以說「這來的地方還有更多呢」。干這種事你可以獲得成千甚至上百萬美元。
#3: 理論家們
伴隨著大公司的收購狂潮,要被接管的公司開始注意到很多事開始變得不對勁。工資名單亂七八糟,電子郵件發不出去,電話系統在日中時不時崩壞。這是收購活動的一部分。
董事會里的頭頭之一可能在大學里有在計算機工業里工作的夥伴,他時不時雇傭他們幹些奇怪的工作。
純粹者
我喜歡工業黑客,出於對這麼做的想法的喜愛。我一年之前就開始這麼做了。威廉·吉布森用《神經漫遊者》給這一活動帶來了浪漫。它太好做了。
#4: 贊同者
我們受在政治系統、毒品組織當然還有公司里升遷的人們的雇傭。我們甚至為外國公司工作。如果豐田雇傭我們攻擊福特,我們會稍稍攻擊福特,但之後會回頭猛攻豐田。我們寧願招惹他們也不願意找自己的茬。
大部分的工業黑客會同時進行兩次侵入。他們從受僱的公司那里獲得信息,但他們也會黑進雇傭他們的公司,如果他們受到背叛,背後被捅刀子,他們會留有後手。所以說要做的工作很多。報酬是實質的,但要做的工作也很多。
在一場真正的侵入接管中,一半的黑客活動是物理的。你們中的很多人要在公司里找工作。你得獲得信息,但你不想讓他們知道你在干什麼。戰爭遊戲式的自動撥號器在掃描中會被發現。他們知道那是什麼;他們之前經歷過很多次這樣的侵入了。
我記得我曾經在當地電視台有過一份工作。我進去假裝是為通訊課題做研究的學生。我和工程師一起轉了轉,我把他說的話都匆忙地記在筆記本上。那傢伙把我帶到計算機房。現在美國幾乎每個計算機部門的「貓」外殼上面都有一張膠布,上面寫了電話號碼。這給我省去了掃描一萬個號碼的麻煩。我已經在記筆記了,所以寫下了號碼,回家等一周左右,然後打電話給他們(你不會立刻打電話給他們,那樣很蠢)。你本地的電話公司不會注意到你,你攻擊的公司也不會注意到你。你嘗試扮演一個隱形炸彈客。你慢慢靠近他們,然後把他們狠狠擊暈。你採取軍事行動,採用信號的智慧、人類的智慧;你有特殊的作戰士兵,他們在那里參觀或者找了一份工作。然後他甚至可以作為員工參觀-之後他出於某種原因受到了信任-就因為他在那里工作,那里就是最大的一壇屎。
斷線
某個人變得神經質,然後某個人的線路電壓變化太明顯,我們認定有竊聽,我們的對話自動中斷。
皮特在光碟里儲存了交談,然後送我到他公寓的消防通道抽菸聊天。他看出我有點慌張。
「那其實不是真正的黑客,」他說,遞給我一卷大麻,我點點頭。但選了一包駱駝之光。「那是解碼。黑客是沖浪。你不為了什麼而做,你只是做。」我們看到我們底下一個流浪者從一隻空冰箱盒子那里撕下一片紙盒子,估計這將會是他今晚的家。
「那傢伙也在某種程度上做黑客,」我說,「社會黑客。」
「瞎說。他這麼做是有原因的。他偷了那個紙板是因為他需要庇護。那沒什麼錯,但他也沒怎麼享受。」
「那什麼是真正的黑客,那是關於什麼的?」
皮特深吸一口大麻,然後笑了。「那是敲打全球的大腦。信息成為一種材質,幾乎是一種經驗。你做黑客不是為了獲得知識。你只是在數據上沖浪,它們想把你弄出水。但那同時又像是一個環保露營者:你把你找到的所有東西都維持原樣。沒有任何你存在的痕跡。就像你從來不在那里一樣。」
公寓那里傳來了Grateful Dead樂隊的歌曲。里面沒人,皮特把的錄音機連到了一個計時器上。那是紐約周一晚上十一點,是大衛·甘斯的廣播節目「死亡小時」播出的時間。皮特踉蹌走進公寓,開始找尋磁帶。我給了他采訪用的一盤空磁帶。
「這個偏差比較低,不過也行,」他說從我手中拿走了錄音帶,並把它塞進一個湊合做的磁帶機,那看起來是霍爾根筆下的英雄遺物。「不要讓盒子騙了你,我親自重調了這東西的。它有硒礦頭,總共有九碼。」對機器正常錄音感到滿意後,他問:「你喜歡Dead嗎?」
「當然。」我可不能錯過這個問題,「我注意到很多玩計算機的都喜歡Dead……整個亞文化。」我後悔過早地提起迷幻話題。然而,皮特並不這麼敏感。「大部分我認識的黑客都服用迷幻藥。」皮特在他的書桌抽屜里翻找著。「它讓你更好地當黑客。」我看著他在房間里走著,「看這個。」他給我看一張Grateful dead演出的票。票正中是一個分形的色彩復制圖。
「現在你也許要問,Dead的票上怎麼會有一個計算機生成圖?」
來源:機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