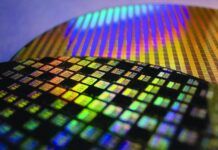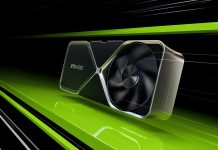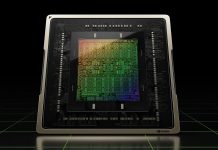第十七章
新殖民主義
正當我們無精打采地走向時間末尾的混沌亮點,我們發現我們的網絡,電子色號被或其他東西都在反對其原初的目的,或者被導向不同的目的。亞網絡和超網絡從原來的媒介中像苔蘚一樣生長出來。不管這是社會衰落的症狀,賽博利亞創世或者兩者兼而有之,我們的舊系統和結構周圍增長的新殖民主義給這個千年的終結帶來了某種奇怪的黎明前黑暗的感覺。
讓我們把賽博利亞亞文化和霍根英雄作比較,後者在獄警眼皮子底下,在戰俘營挖地道反叛逃脫。也許我們時代最顯著的標志就是美國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多的入獄人口比例,並且正養育著罪犯亞文化,越來越遠離被認可的社會體制。
正是在監獄里,傳奇的電話弗利阿科脆帽(phone phreaque Cap’n Crunch,他的名字由來是用他在一盒脆帽穀物里發現的雙音符口哨來打免費長途電話)被迫加入了犯罪亞文化的行列。他的真名是約翰·德雷珀(John Draper),我在圖恩小鎮發現他正在操作電腦視頻交互界面。
在幾次快速爬升到編程專業頂級水平之後,德雷珀跌入了富裕-貧困無窮無盡反復橫跳曲線的低谷,這定義了他過去二十多年的生活。看起來,每次他發明出智慧的新程序,一場調查就會把他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牽扯到非法的事情上,然後德雷珀的器材連帶著他的生計就會被沒收,讓他的進展被拖累合同也告吹。這位白發、戴眼鏡的網絡老兵建議我們潛進大腦-機器房間談論他的監獄經歷。
「為了自己能在監獄存活,我得讓自己足夠有用,這樣他們就不會騷擾或者調戲我。所以我得教所有人怎麼打電話,怎麼進入系統,進去後又該干什麼。我們會開辦小課堂。純為了生存,我被迫傾囊相授,相信我,我確實這麼幹了。」
德雷珀相信,因為他的監獄課程產生了成千上萬起電信和計算機犯罪。當他的技術落入因貪污或欺詐而進入正在服刑的囚犯的手中時,他們反過來又發展出了一些今天最先進的工業黑客行為。
德雷珀的經驗反映出賽博利亞反文化運動在社會中進行的一般方式。為了智力、情緒甚至是物理生存,一小撮人,不總是地理上相互聯系,構成了以連接他們的特定網絡為特徵的武裝小團體。這之後,啟動了自下而上的賽博利亞意識循環。
一個驚人的例子就是「鼴鼠人」社群的增長,他們住在紐約地鐵系統中被遺忘的隧道中。紐約市交通管理局估計,大約有5000人住在一層,但這只占隧道系統的三分之一。其他官員估計,整個系統中有近2.5萬人,這個系統的深度比警察或交通人員不敢走到的地方要遠得多,由19世紀90年代建造的數百英里的廢棄隧道組成。地鐵里灰白色的居民們選舉出他們的市長,布置自己的地下公寓,尋找電力,在某些情況下安裝自來水。聽起來更像是都市傳說,而不是真實存在的人口,鼴鼠人聲稱,他們是出生在隧道里的孩子,從未見過天日。另一些人則提到了由鼴鼠頭領組織為防止被發現,組成巡邏隊,確保誤入他們營地和村莊的外來者不再誤入。不管這是否夸張,我們確實知道,許多試圖進入較低隧道的電視新聞工作人員被投擲石塊,被迫撤退。
「安全起見,」J.C.解釋道,他被自己鼴鼠社群的市長叫來向珍妮·托斯,一個與鼴鼠人在1990年保持友好的紐約記者,解釋他們生活的哲學,「社會生存在一個穹頂里,然後鎖上所有的門以保證安全。我們被鎖在外面,留在底下。他們忽視我們。他們忘記了生存的本質。他們重視錢財,而我們重視生存。我們互相照顧。」異化、迷失和最重要的必需構成了社區合作的新的紐帶,這在地上是不曾被體驗過的。
一個生活在中央車站數百英尺下的男人解釋道:「你下去,擺弄一下電線,然後就有光。在你知道之前,會有十二到十五個人在那跟著你。他們變得像鄰居;你和所有人都是朋友。你認識在盡頭的女孩子和在中間的家庭。當某人生病了,我們一起籌錢弄藥。大部分人都團結著。你可以做到這樣。」
這個自下而上的網絡正和全球電子村的構建相似,它也依靠共同利益的紐帶和志同道合的政治。每個系統都由需求沒有得到已建立的渠道滿足或甚至被阻礙的人組成,每個系統利用現有網絡,用於其不曾設想的目的。這類社區構成了整個社會動力系統中日益重要的組成部分。程式設計師馬克·德·格魯特將這一社會景觀與系統數學的結論進行了比較:
「傳統的反饋循環例子是恆溫器,它控制自身。我想我們現在正在發覺,現在最普遍的因果種類是反饋而非線性或者自上而下的。效果反過來影響原因,原因又影響效果。我們有一個權利去中心化的社會,我們有反饋循環,可以從底層產生改變。有權力的人會試圖消滅這些威脅。」
對網絡進化的恐懼可能源於對這些新的反饋和疊代渠道的部分察覺。那些認為自己現在很強大的人試圖壓制疊代器,但會發現他們的努力是無效的。就像變異的細菌甚至蟑螂一樣,反饋循環將促進適應性變化,比為對抗它們而開發新的抗生素或殺蟲劑來得更快。與此同時,那些從前無能為力的人,現在認為自己通過反饋和疊代對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們著迷於自己的原因,著迷於自己的技術。但無論他們多麼痴迷或沉迷,無論社會反應多麼恐懼或暴力,反饋和疊代都不可避免地緩慢地推動著革命的車輪。
負面反饋疊代
反饋迴路是數學描述革命的方式,是存在的自然組成部分,就像浮游生物、火山或甲狀腺。以消費為基礎的機械文化的負面反饋循環是憤怒的勞工、生態恐怖分子和意識擴張的倡導者,他們通過廉價的通訊、印刷和視頻製作來進行他們的疊代。
以克里斯·卡爾森(Chris Carlsson)為例,他是《加工世界》(Processed World)雜誌的編輯,他說這本雜誌「講述的是資訊時代的陰暗面,以及在一個以買賣人類時間為基礎的反常社會中日常生活的痛苦。」卡爾森看起來更像大學教授,而不是上班族;他是一個才華橫溢的60年代前激進分子,他退出了激烈的競爭,在舊金山做了一名作為在辦公室處理臨時數據的員工謀生。
在一個慵懶的周日早晨,卡爾森正在解釋他錯綜復雜的歷史哲學觀點,他用菸鬥和咖啡壺里的渣滓調整了螢幕的位置。他認為,我們目前生活在一個「社會建構反常」中,一個不自然的現實,這將被迫改變。卡爾森認為,我們的社會對消費上癮,這種上癮導致我們做的事情和支持的系統只對美元有利,而不是對個人。像助興音樂一樣,這些體系本身就是為了粉碎個人權力的概念而構建。
「很難想像還能怎麼樣。在這個社會你被問的唯一的問題就是『你想買什麼?』還有『你拿錢准備干什麼?』,你不能說『我想對生活所求什麼,我怎麼才能對總體作出貢獻?』。我們的社會沒有促進個體的某種角色的機制。」
在「經過處理的世界」中,底線是最重要的。工人們拿著盡可能少的工資生產出盡可能快損壞的產品,或者除了賺錢以外沒有任何其他功能。在信貸和GNP擴張時代的最後階段,永遠不會有足夠的東西——如果有,企業就會倒閉。出售是動力;生活水平、環境、文化發展以及生命的意義都不在這個等式之內。
例如,想要銷售化學品的化學公司,靠貧瘠的作物和牲畜興旺發達;他們希望創造一種依賴化學的農業。「因此,基因剪接技術的第一個應用將是牛生長激素,」卡爾森說。「並不是說我們國家需要更多的牛奶;我們有盈餘!」但生長激素會增加奶牛的產奶量。農夫瓊斯需要跟上農夫史密斯的步伐,所以他也會購買激素。不幸的是,這種激素也會使得奶牛的膝蓋變得脆弱,這就要求農民購買更多的抗生素和其他藥物,給化學公司帶來更多的收入。另一個例子:為應對加州地中海蒼蠅危機游說反對果蠅不育化是對這家化學公司有利的。通過「說服」政府允許使用殺蟲劑,化學公司削弱了他們正在「節省」的工廠,從而進一步依賴化肥和藥物——更多的錢,更少的效果,更大的污染。
卡爾森並不為我們的困窘責怪「當權者」。「董事長並不感覺自己有任何權利。他只是被困住了。持股人只在乎紙面收益看起來多平衡。」往遠了說,隨著工作環境越來越非人化,系統失去了可以糾正自己的珍貴反饋渠道。美元過度簡化了工作社會的復雜性(而它的需求,正如我們會在這章稍後看到的那樣,將全球生態簡化到了災難性的水平)。隨著工作地點愈發自動化,工人成了電子表格程序的一部分:他們的輸入和輸出都被電腦監控、規制和控制。隨著工作被機器取代(它們工作效率更高),工人們被降職而非升職。他們隨著時間推移發展的任何特殊技巧現在都變得毫無意義。
解決方法,根據卡爾森所說,是顛覆和破壞。「當你出售你的時間,你正在放棄決定什麼是值得去做的權利。工人階級的目標應該是廢除他們正在做的事情!不是要反對科技,而是反對科技被利用的方式。人類可以找到電腦和復印機這些東西的顛覆性利用方式。它們並不是為了增強我們的溝通能力被造出來的,但它們確實能。它們給每個人一個通過印刷媒介說話的機會。工作經驗讓工人知道他沒有發言權,並且他做的事完全是浪費時間。但這深深地空虛和不滿在電視上並不明顯。社會中所有東西都在侵蝕你的自尊心。」
《被處理的世界》(Processed World)雜誌希望通過喚起他的智力並且給他關於如何顛覆工作場所的建議來增強工人的自尊。它是一個樸素的闡明辦公室工作人員的經驗,以便讓他們知道他們並不是在發瘋,他們的情況也不是獨特的出版物。它也作為一個論壇,讓工人分享他們對消費者社會、工作濫用和反抗技巧的觀察。像「破壞……這就簡單得像拔插頭一樣」的標語和用來抹消辦公室硬碟的「鈷磁數據分區」的笑話廣告伴隨著讀者/工人寫的關於如何讓工作場所不能運轉,從而破壞大公司的邪惡行為的文章。
電腦是工作場所中破壞的最主要工具。工業黑客對競爭激烈的公司使用的技術現在被工人用來對抗他們自己的公司。通常,在賽博利亞之中,公司的老闆們無意中為了能更好地監控和控制他們的員工已經建立了造成最大破壞的捷徑。
在參觀一家大型保險公司的數據輸入部門時,一位計算機服務人員和辦公室破壞者解釋道事情可以逆轉。「我們的辦公室經理通過員工電話里的一個特殊對講機功能來監控員工,」當我們在桌面漫步時,他低聲說道。「我知道這一點,因為我安裝了電話系統,我教辦公室經理如何使用它,我知道他們確實在使用它,因為我監控他們!」我們來到另一位正在玩電腦遊戲的員工桌前。當他按下退出鍵時,一個虛擬的電子表格覆蓋了螢幕。
「給他看電話是怎麼工作的。」我的同行人要求。
工人在他電話上輸入了一些密鑰然後把聽筒遞給我。有人在口述一份關於如何訂購文件的備忘錄。
「那是本層經理辦公室,」工人說,他在他拿回聽筒並小心地掛掉時驕傲地笑了。
我的導游為這一成就感到驕傲。「你可以通過調制調解器修理一個Rolm(IBM的一個子公司)電話系統,讓它像竊聽設備一樣工作,這對老闆監視他們的員工很有用。但如果你修改了軟體,不用進老闆的辦公室,遙控通過調制調解器就能做到,你就可以反過來利用同樣的功能!」
「他就是從我桌子上的電腦這麼做的!」工人感激地補充道。
當我們走著,大部分工人都對著我的導游會心一笑。他們都是一夥的。用著辦公室破壞的暗語,他驕傲地吐露道:「我們把這地方鎖得很好。」
破壞,正如同電腦駭客,可以被同時認為是自然循環和破壞沖動。確實,它讓人們覺得自己更強大,並以負面反饋的方式對系統全局發送出一個警示信號。但它同時也是讓人們發泄不滿的機會。一個感到無力和不受歡迎的孩子突然用計算機數據機獲得了力量和地位。一個匿名的工人看不到他生活的任何目的,當他精心設計的惡作劇使整個公司癱瘓時,他的自尊心得到了提升。
不管動機是賽博利亞理想主義,還是自慰式的自我滿足,這些行為會作為循環反饋生效。我們不能僅僅因為肇事者不能用賽博利亞式的修辭為自己辯護就把這些努力貶斥為神經沖動或者幼稚的權力幻想。即使是破壞者最強烈或病態的沖動,在賽博利亞的背景中看來,似乎都是疊代系統對威脅其存在的條件的自然反應。
當然,這些情況中最緊迫的是目前正在破壞生物圈的行為。正如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所觀察到的那樣,蓋亞通過浮游生物、藻類、樹木和昆蟲等疊代反饋循環來保護自己,這些循環有助於維持一個平衡的地球環境和適合生物生命的條件。其中的一個反饋循環可能就是激進的環保組織「地球第一!」。這些自稱「生態恐怖分子」的人,就像他們的創始人、身材高大的亞利桑那州人戴夫·福爾曼(Dave Foreman)一樣,已經發展出一種極其致命的社會政治病毒,叫做「生態化」或「生態防禦」。
生態化是保護環境的恐怖主義手段。生態恐怖分子沒有進行抗議、實施封鎖或通過游說影響立法,而是採取利落、迅速、外科手術式的行動,挫敗那些想破壞環境的人。這些行為被稱為「撓猴」,其形式是將尖刺埋在樹上,以免被砍倒;禁用車輛;拉下招牌或電線;毀壞重型機械或者航空器的;在道路或樹林上釘釘子使其無法通行;引發動物陷阱;最重要的是,不受懲罰地逃脫。他們的行為絕不是隨機的,而是經過精心計劃的,以最少的努力和風險產生最大的影響。例如,在噴灑殺蟲劑的前一晚切斷直升機旋翼上的兩根電纜所造成的損害,比在一家公司的停車場從40輛吉普車上偷取分電器蓋造成的損害還要大。幾次低成本、精心策劃的生態化攻擊可以使整個森林砍伐項目無利可圖,並導致項目取消。
正如福爾曼在他的生態防禦中解釋的那樣:《撓猴野外指南》——某種有目的的無政府主義者的食譜——撓猴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它是非暴力的(沒有針對任何形式的生命,只有機器),沒有組織的(不可能被滲透),個人的,特定的目標,及時的,分散在全國各地,多樣的,有趣的,本質上是非政治的,簡單,深思熟慮,合乎道德。當然,倫理是有爭議的。企業有破壞環境的「合法」權利(特別是如果他們為這種權利支付了大筆的游說或賄賂)。他們認為當前的政治體系只是毀滅機器上的一個裝置,剩下的唯一策略就是直接行動。
鮑勃和卡莉(對,她是一個TOPY成員)是來自西北部的生態恐怖分子。他們行為限定於(或者說他們只願意談論這些行為)「廣告牌的破壞與修改」。他們的願望是保留國家公園和扭轉潛在的破壞環境者的宣傳活動。卡莉在州際公路服務區做服務員,她是美國金發美女,腳踝上帶著環的Deadhead追隨者——在從櫃台到桌子的路上,可以聽到她以高露潔式的的微笑哼唱著《糖木蘭花》(Sugar Magnolia)。她毫無威脅的舉止讓她能夠傾聽,甚至激起卡車司機和建築工人關於正在進行的項目的對話。她的男朋友鮑勃通過學校的電腦網路將這些信息交給了他們所在地區更嚴肅的撓猴者們。
鮑勃是高速公路上游州立大學的一名藝術工作室助理。他每天晚上開車去餐廳接卡莉下班時有動力採取行動反對廣告牌。「每周都有越來越多的廣告牌。通過了一項法律來限制廣告牌的數量,但每次我們通過這樣的好法律,現實中都會發生相反的事情。」他的筆名鮑勃來自亞天才教會的「救世主」,這是一個諷刺的賽博利亞邪教,他對自己撓猴和他展現自己視覺智慧效率的歡愉的態度是半開玩笑。
「一罐2美元的噴漆可以逆轉10萬美元的媒體宣傳。你用自己的話對付他們,用幽默揭穿他們的謊言。」鮑勃用他自己版本的福爾曼《野外指南》中描繪的裝置,把一罐噴漆放在一根長金屬棒的頂部,金屬棒上有一根繩子,手把上有觸發器。在地面上,他可以在他夠不到的幾英尺外的地方對廣告牌進行修改或添加。按照福爾曼的建議,他把工具拆卸下來,藏在卡車的一個鎖著的隔間里,並時時改變「襲擊」的地點和時間,這樣他就不會被抓住。「書上說要回答廣告牌。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就好像他們給我們留下了評論的空間。」鮑勃最喜歡的是在萬寶路鄉村的地平線上畫墓碑,把競選口號從「選舉」改為「豎立」。
鮑勃和卡莉都支持那些更激進的撓猴者的活動,但恐懼讓他們不敢去執行這些任務。「不是每個人都要冒生命危險,」卡莉解釋道。「他們被拿著球棒的人追趕。」
「但他們所做的事情至關重要,」鮑勃補充道。「這是完全自然的反應。當身體生病時,它會產生更多的白細胞。這些傢伙是這樣的。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像那樣。」
從賽博利亞角度來看,生態恐怖分子是偉大的蓋亞有機體中負面反饋的自然產生者。就連思想科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Noetic Sciences)負責研究的副所長布蘭登·奧雷根(Brendan O』regan)也承認,生態化的行為是對抗地球破壞的一種有價值的模因:
即使你不同意這種策略,他們也指出,這個行業正在對環境產生一種無政府狀態。生態恐怖分子又引發了無政府狀態。這里有一種極端在驅使它。生態化是為了環境所做的破壞。它是這樣被合理化的,系統的所有者沒有遵循正當的法律程序和道德關切,所以「去他們的吧。」很多這樣的事情都將通過技術,如傳真、復印機、計算機網絡等協同發生。這是用混亂對抗混亂。」
由「建設」所建立的系統,只要我們使用全面的術語,就創造了一系列新的反饋循環和疊代器,以取代或至少讓我們意識到被森林砍伐和環境暴政所破壞的自然循環。像綠色和平組織這樣的大型組織依靠電腦黑客和衛星專家來建立自己的通信網絡,並攔截有關計劃行動的執法通信。在德國已經使用過的非法電視廣播車,在舊金山灣區正在建設中;他們將能夠用激進的宣傳取代原先預定的節目,甚至在常規的傳輸之上疊加文本。
生態恐怖分子從來不反對技術。他們將高科技視為更快、更有效的反饋和疊代工具。再加上其他原因,蓋亞假說的創立者並沒有預言我們星球的末日——特別是從那些看起來不自然的發明的發展來看。他們意識到技術在更大范圍內的地位,甚至它在調節生物圈方面的價值。正如蓋亞假說的創始人詹姆斯·洛夫洛克向我們保證的那樣:
「最終,我們可能會實現一種合理而經濟的技術,與蓋亞的其他部分更加和諧。不可能自願放棄技術。我們是技術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放棄它就像在大西洋中部跳下一艘船,在光榮的獨立中游泳度過餘下的旅程一樣不現實。」
社會理論家、《全球評論》(Whole Earth Review)編輯、《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等電腦文化書籍的作者霍華德•萊茵戈爾德(Howard Rheingold)也承認:「科技在很久以前是錯誤的選擇,它導致了非常糟糕的情況,這種說法可能是正確的。但我看不出有能擺脫它的路好走,如果我們不學會更好地利用科技,地球上大部分人都會死。」
當然,這里的危險在於高估了我們認清現狀和實現必要的技術的潛力。過於簡化問題對我們的生存,甚至對我們的解放都是危險的,就像通過消滅數以百萬計的物種來減少和簡化我們的生物圈一樣,蓋亞依靠這些物種來進行反饋和疊代。
第十八章
讓最好的模因勝利吧!
正是通過控制推動者鋪墊的技術和道路,賽博利亞人們相信他們必須進行自己的改革。例如,大型電視網絡的最初目的是為了銷售產品,讓大眾接受瘋狂的政治方針,除了越南戰爭那段時間之外,如今已被低端家庭視頻攝像師納入反饋機制之中。新聞周刊封面杜撰出了「視頻警察」,私人公民正將現實帶入媒體之中。當一隊警察過度使用暴力制服嫌疑犯時,很有可能會有人在一旁拿著攝象機將畫面記錄在錄像帶上,而幾個小時內CNN就在全球傳播開來。此外,像深盤TV(Deep Dish TV)這樣的樂隊現在使用公共接入有線頻道傳播視頻,里面展示的現實和網絡新聞廣播中呈現的截然不同,讓人們深信不疑。
「槍枝曾是偉大的均衡器。」提到攝象機,傑克·納克巴(Jack Nachbar)如此說道,他是
博林格林州立大學的流行文化教授。「你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這像6把新槍。確實可以賦予普通人力量。」現在,警方攜帶自己的攝像設備,通過像DIVA(該死的干擾視頻活動家,簡稱DIVA)這樣的團體展示他們那方的故事記錄。新的戰爭,就像蝙蝠俠和小丑的媒體大戰,並不使用常規武器,而使用數據空間中的圖像。賽博利亞的終極武器不是利劍,甚至不是筆,而是媒體病毒。
任何思想都能成為媒體病毒,滲透入現代社會宿主機體內。它可以是真實事物,例如馬克·海利的智能吧,在有機層面發揮功能,同時也傳播一種強大概念,能夠改變我們對藥物、醫療和智能的感覺。同時,病毒也可以是純粹的思想或觀點,比如「蓋亞」或者「形態共振」,一旦傳播開來,就會改變我們的現實模型。「病毒」這個詞本身就是某種超媒體病毒,社會作為免疫缺陷宿主有機體,極易受到「更好」思想和信息的攻擊。病毒包含遺傳密碼,賽博人稱之為「模因」(meme),只要信息或者編碼仍然有用,或者甚至僅僅具有吸引力,模因就能在系統內復制傳播。賽博活動家都是市場營銷專家,發動的是媒體運動,而不是軍事活動,在賽博空間內戰鬥。計算機網絡、新聞、MTV、時尚雜誌和脫口秀主持人如何報導病毒將取決於病毒傳播的廣度和深度。
在賽博利亞,公關遊戲都公開、直接。如我們所見,像喬迪·拉茲克、地球女孩和黛安娜認為自己的市場營銷事業與顛覆性事業完美兼容。這兩者是同一回事,因為她們推廣的產品:浩室文化,就是媒體病毒。「促進這一文化生長的燃料就是成為潮流兒、嬉皮士。」拉茲克說,「我們用文化市場來打敗文化市場。」所以,要更加嬉皮、更加潮流,人們爭相購買拉茲克的一幅,接觸各種浩室文化的模因:分形、混沌、狂喜和藥物,薩滿主義以及兼收並蓄的態度。讓愛律動起來。
但是,更年長、更務實的前輩們無法輕易被潮流所左右。賽博利亞希望用不同類型的病毒吸引這一市場,這些新病毒帶著傳統價值、工作倫理和醫藥模型的面具。麥可·哈欽森(Michael Hutchinson)是《巨型大腦,漂浮之書》(The Book of Floating, Megabrain)和《性與力量》(Sex and Power)這兩本書的作者,依靠兜售關於腦機和其他壓力緩解設備而生。他是一個堅定果斷的紐約人,穿著馬林縣的當地服裝:寬松的上衣,卡其褲和網球鞋。同樣的,他的「壓力緩解」系統背後的賽博動機也打包放進了聽上去很純潔的包裝中。
「60年代,我們磕酸的時候,」他承認,「我們覺得自己的發現會改變世界。當時真是靈感爆發『嗨,讓我們把這玩意兒倒進水庫里,讓美國……全世界都嗨起來!人人都嗨起來,酒不會再有戰爭啦!』」
但是,戒掉酸卻異常艱難。讓人們戴上目鏡可就簡單多了,甚至醫學也能為其正名。許多研究表示,腦機產生的閃光燈和聲音能夠讓人們放鬆下來,賦予新鮮活力,甚至緩解他們藥物濫用、臨床抑鬱和焦慮症狀。與大腦同軸運作的機器調低頻率,把人們帶入意識的深度冥想狀態。用哈欽森的話來說,就好比進入了一場溫和的迷幻之旅,還有許多同樣的轉變質量。
「潛意識物質慢慢浮出水面,但通過機器,你很放鬆,能夠應付任何出現的事物。再過一段時間,人們能夠以非常溫和的方式釋放自己的惡魔。如果是一場體驗強烈的酸之旅,就會把人都嚇跑。」哈欽森笑道。從某種角度來說,他樂於承認,腦機就是披著機器羊皮的變形狼。「我們這里乾的事情確實顛覆。我們說服企業使用這些設備來緩解員工壓力,讓學校使用獲得更好的學習曲線,而醫生則可用來作為藥物治療手段。隱藏的計劃就是我們確認讓人們進入大腦的深層狀態,促使真正的人格轉變。這是我們的秘密文檔。我認為長此以往,這種機器會發揮改革意義的作用,如果世界上每一個人……」
他的聲音越來越低,他也逐漸陷入腦機啟蒙的沉思中。但是,對於這些設備,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另有打算。在沒有收到FDA批准之前,生產商不再公布這些機器的醫學斷言,因為獲得批准要花上百萬美元。哈欽森堅信,腦病毒機器的打壓背後有各方勢力。
「喬治·布希曾說過:『我們唯一的敵人就是不可預測性。』權威系統依賴自己的公民,需要他們以可預測的方式行動。但是,任何增強意識狀態的事物都會增加不可預測性。這些機器引導人們接觸關於自己的不可預測新信息。因此,導致不可預測的行為,這樣的機器就很危險。一旦人們親手掌控智能工具,老大哥就危險了。」
這就是為什麼哈欽森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教育人們關於腦機的知識,而不僅僅兜售機器。他的每日頭條詳細講述了哪里可以購買機器,機器如何運作,為什麼是好東西,如何製造機器。「大眾教育就是大眾製造。」他說,「即使機器被沒收了,我們列印的電路圖也維持著技術可及性。」
最後,盡管如此,大腦病毒機器的大部分賽博元素是觀點,或者模因:人類應該通過技術,自由自在、有意識地改變自己的意識。只要病毒被接受,設計師現實的賽博理想距離真正實現又近了一步。
模因工廠
為了讓病毒生存下去,發起人所說的「安置」就是一切。出現在《今夜秀》上的一個激進觀點看似太過普通,而《沉思》雜誌尚的一篇文章卻與令人作嘔的「新」時代聯系起來。模因安置對媒體病毒的重要性不亞於封裝生物病毒DNA編碼的蛋白衣殼,蛋白衣殼提供安全通道,與靶向的細胞連接起來,病毒內的程序成功注射入細胞內。而媒體病毒的一個蛋白衣殼就是天狼星的《Mondo 2000》。
最初誕生的雜誌名為《高度前沿》(High Frontiers),關於藥物、意識改變狀態以及相關哲學的雜誌,然後短暫地變身為《現實黑客》(Reality Hackers),關注計算機問題和激進主義,因為此時賽博利亞的興趣點在於高科技。現在的名稱簡單明了《Mondo》,每年貝克利山頭編委會巫師大集會後發行兩三期,每次都重新發明各種賽博參數,沖擊一下當時參數。如果病毒出現在《Mondo》頁面上,那麼很快就會出現在地圖上。賽博利亞之聚光燈——Mondo,將新哲學、藝術、政治和技術匯聚一堂,定義那些尚未完全上線的美學和議程。Mondo就是雜誌界的浩室俱樂部。但遠不止將地理區域內的人們聚集在社交單元中,Mondo還將更遙遠區域的人們聚集道志同道合的模因陣營中。它的讀者也是它的作者,還是它的主題。
賈斯·摩根(Jas Morgan)喬治亞州雅典市的醫學預科生,知道有一些超越現實的東西,但不知道去哪里找。就和許多真正的賽博利亞人一樣,藥物、音樂和媒體無法讓賈斯變得更傻更喪,它們只會讓他更想擺脫高中畢業後面臨的現實困境(有一次,他把自己的全A成績單放在父母的廚房桌上,旁邊是一袋水煙和一張便條,上面寫著「我們要談談」。)
和美國許多其他初出茅廬的賽博利亞人一樣,賈斯沒有什麼信息來源能夠確認他對生活的懷疑。他收聽FM深夜電台廣播,讀了兩遍利里所有的書。賈斯尤其受到利里這條建議的影響:「找到其他人」,後者不斷重復,催促人們行動起來。當賈斯看到《高度前沿》雜誌時,他知道自己找到了。
《高度前沿》首次將精挑細選的模因放在同一處。以前從未相互關聯的觀點,除了在煙霧繚繞的宿舍內,現在共同存在,相互依賴。新興文化斷斷續續的病毒鏈找到了歸宿。利里寫得內容關於計算機和迷幻劑。特倫斯·麥克納的主題則是熱帶雨林保護和薩滿主義。音樂家寫政治,計算機程式設計師寫上帝,藥劑師寫混沌學說。這本巫師們編纂的雜誌給賈斯·摩根帶來了愉悅之感,仿佛自己敲開了出版商Domineditrix穆女王(主編之一,原名Alison Kennedy)俯瞰貝克利的樸素宅邸大門。Mondo之家,那些不住在那里的人們如此親昵地稱呼,就是鮮活模因的城堡、集體農場和家園,在山頂上,雜誌被撰寫、編輯,生生不息。Mondo的作者們也就是它的參與者和主體。摒棄客觀現實形式,雜誌接受當時任何模因並出版。而決定這一切的就是R.U.天狼星,又名肯·戈夫曼,雜誌主編,人形吉祥物。
賈斯搬入其中,並很快成為了Mondo一炮而響的社交達人。他英俊的外表和學院派的舉止出色掩飾他「非法」的另一面,他讓雜誌獲得灣區(舊金山)和南部地區(洛杉磯)長久以來所希望的認可。但隨著賈斯不斷發展雜誌的國際化形象,天狼星也不斷發展賈斯的現實形象。賈斯很快學會將自己長期懷疑的共識現實視作真理,他接觸了新的信息和人(霍夫曼的前妻成為了他的女友),還有化學物質,讓他學會了行話,了解了資料庫,談論起風暴。
「每次我想要CD,我都要出門,花15美元才能買到一張,要是能連上計算機或者和計算機將一句話,就能得到一張最新專輯,而且只要付一分錢,那就太美妙了。這樣,它也不占物理空間,而且也不讓CD工廠里的人被趕出去掙吃飯錢。我想要人人均富的文化。人們在家工作,或者在某個新興部落中心相互合作,就像科學家工作的方式那樣,進行頭腦風暴。人人擔心動機,但不要怕,人們不再只是呆坐在電視機前。」
他沉思了一回兒。「也許人們想要放假一年,吸吸草,看看電視。但他們很快就會厭倦,會發現更多的自己。」
Mondo的男男女女創造出一種放棄勞動力、磕磕藥、圍坐在一起討論這些內容的職業。(自從我與Mondo的孩子們共享體驗以來,出版商努力讓雜誌更受人尊重。大部分和藥物有關的內容消失了,後來,雜誌嘗試與更成功的《連線》雜誌競爭,為此更多傳統作者和編輯逐漸代替出版女王稱作「小團伙」的最初常駐叛逆成員。這個策略似乎遭到了反擊,在失去了賽博利亞創始團隊之後,Mondo 2000所剩的日子屈指可數。但是,在鼎盛時期,Mondo就像安迪·沃霍爾的「工廠」一樣活躍,如同60年代匯聚了loft/社團/影視工作室/藥物那樣的盛況。作為雜誌的Mondo和作為社會背景的Mondo給新思想、時尚、音樂以及行為提供論壇。)
就和沃霍爾的紐約時代一樣,我在這里遇見的孩子們,最初狂野的Mondo 2000致力於進入改變狀態,討論邊緣性概念。他們的編輯決議源於「如果我們聽著有趣,那麼他們也會覺得有趣」哲學,他們的大受歡迎使雜誌有權利僅僅印刷「他們」喜歡的模因。
Mondo成員入駐整個部落的方式和賈斯的經歷極其相似。有人直接出現在門口,談話對胃口,就加入其中。現在固定成員約20人。在中心的便是天狼星。他是賽博利亞的戈麥茲·亞當斯(Gomez Addames),人們甚至懷疑他是不是和他周圍的人有血緣關系,又或者僅僅是古怪的偷窺狂。很難說天狼星是否是賽博利亞之父,或者只是其卓越的超然觀察者,又或者兩者兼而有之。也許他的成功證明了,最終沉浸入超空間是自我風格的元參與,一個人周圍的環境、朋友和愛人都成為了信息矩陣的一部分,下一個議題的潛在文本。雖然一些社會團體會譴責這種對待自己親密愛人的方式,但Mondo族們蓬勃發展。他們就是人類模因,他們依賴媒體認可,從而存活下來。
「我們生活在沉浸於媒體的巔峰時代。」肯推測著媒體旋風中的生活,「我們是誰,通過我們藉助媒體渠道對世界展示的內容表達。如果你不被媒體提及,在某種程度上你不算存在。你不存在於地球村的織物中,除非你是向外傳播交流。」
所以,根據這樣的邏輯,天狼星決定什麼存在,什麼不存在。他的編輯權力凌駕於現實之上。「只要你想,你可以反對。」一天晚上,我和天狼星驅車離開圖恩鎮活動返回Mondo的路上,他這麼跟我說,「但是相對於數據流,你已經存在,就像息肉之於珊瑚礁,或者螞蟻之於蟻山,又或是蜜蜂之於蜂巢。早已無法擺脫。」而天狼星是賽博利亞的基因工程師,通過挑選模因設計媒體空間的現實。
當他人批評天狼星在扮演上帝,因此需要為自己辯護時,他的優勢就是他並不是出於刻意的目的或議程為雜誌選擇模因。他早早離開圖恩鎮的原因(凌晨兩點之前)是他認為,他們太過教條地展示自己的模因。「馬克·海利和浩室現場展現自己的作為,有點宗教化了。Mondo 2000沒有意識形態。我們在新領域內唯一推崇的就是自由。而通向自由的唯一方式就是沒有任何條條框框。抗議不是什麼創造性活動,真的。」
盡管如此,天狼星為自己雜誌挑選的模因往往具有政治不穩定特徵:性、藥物、顛覆性科學、技術、哲學和搖滾。僅僅把這些觀點全部塞進一本雜誌,就是在宣布信息之戰。天狼星說,他們的一位粉絲,也是CIA和NSA的技術顧問,總是在自己同事和調查員的桌子上看到他們的雜誌。「他告訴我:『他們都愛你們這幫人。他們讀你們的雜誌,想要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怎麼這麼可憐,我告訴他我們只是在編造故事。」
盡管態度諷刺,天狼星承認他的雜誌反應並推動社會變化,即使沒什麼特別原因。「我們這里並不提供什麼解決方案,好讓火車跑得更准時。其實,我們的出發點是一個相對社會不負責任之處。」但是我們提供視角,傳播給想要看到它的人們。我們沒必要去回答政治問題。我們只是說:「我們來了。」
我們就這樣來到Mondo之家。天狼星下車時出了點小麻煩。「我現在要吃點大腦藥」他道歉說,「我以前經歷過後背疼,所以現在要遠離藥物。」他揮舞著身上的鬥篷,試圖下車。他動起來像個魔法師,有點兒怪異的魔法師,好像每個動作不僅僅是動作,還代表著那個動作。沒有意義。只不過是表演技巧。
走在通往房子的步行短路上時,他遇到了一位記者瓦爾特·科恩(Walter Kirn),後者正在前廊下的灌木叢內小便。
「我們有衛生間,瓦爾特。」天狼星可能是賽博利亞中唯一一個不帶諷刺口吻說出這句話的人。
瓦爾特很快道了歉。「這只是實驗的一部分。」他邊說邊拉上拉鏈,想了想要不要握個手。他接著說自己等了快一個小時,不過他好像看到里面有人影在動,但是沒人應門鈴。於是,他就開始等,等啊等。接下來,他就想起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每次只要我撒泡尿,就會發生不同尋常的事情。就像混沌數學中的奇異吸引因子。當我將看似隨機、奇異的行為引入情境中時,整個動態系統就發生了變化。我並不真正相信這個理論,但看來奏效了。」
天狼星盯著科恩看了好一會兒。這人和上周來貝克利的記者完全不同。他已經皈依了。
「所以,我猜,你在這里尿了尿,我們就出現了。」
瓦爾特大笑起來,因為這句話聽上去非常荒謬。「值得一試。」
「顯然如此。」天狼星總結道,他用霍比特人似的奇怪優雅方式打開了門。
為什麼沒人聽到科恩的門鈴和敲門聲,始終是個謎。大約有十幾個Mondo們坐在拱形天花板客廳內聊天。其中包括埃里克·古利克森(Cric Guillichsen,負責第一台廉價系統Sense8的VR設計師),兩位表演藝術家,其中一個是蒂姆·利里的助理(蒂姆晚上很早就離開了,要准備第二天的演講),一個是女子樂團DeCuckoo的成員,還有薩拉·德魯,賈斯·摩根,以及其他一些編委會成員,另外幾位未來成員。
穆女王在廚房煮咖啡(希望足夠強勁,能夠讓久坐不動的土豆們趕緊離開),有一個誰都不認識的人坐在桌邊,仔細閱讀著散落的Durk和Sandy食品罐頭上的成分表。在客廳後面,編輯空想意見交流會議喋喋不休,永無止境,或鼓舞人心,或令人乏味,內容抽象,讓任何大腦化學物質與此刻屋里其他人不匹配的人困惑不已。但又非常具體,足以在下一期雜誌上找到蛛絲馬跡,雖然仍會有幾張空缺頁面。可能有作者會報導尚未存在的「如果……會怎麼樣」技術,而VR設計師則可能由此獲得下一個項目靈感。或者VR設計師調整了假設的互動視頻提案,而表演藝術家則以此為基礎創造出新的作品。這一切充滿樂趣、相互有距離、強烈、迷幻,也許最重要的是帶來商機。
「看到迷幻劑在體內發揮什麼作用,這很有趣。」有人說道,「感受它。其中一些可能會很陌生,一些非常蓬鬆、柔軟,感覺奇妙。好像給你某些暗示,暗示物理身體發生著什麼變化。」
「還有感官。尤其是聽覺和聲音。」薩拉補充道,深深地看著她的一位仰慕者的眼睛。她就是這家工廠的伊迪·賽奇維克(Edie Sedgewick),除了一副精明的頭腦和關懷的靈魂。「讓我們想想,如果我們將聲音的再製造融入藝術中,而不是發展TV。這將會創造出不同的社會。」沒人贊同這個觀點,但薩拉毫不擔心。雜誌下一期已經預定了她的音樂,會大肆宣傳一番。
天狼星坐在薩拉身邊,而她的粉絲們則在她身後。金看著這兩人互動,默默猜測他倆的親密程度。也許天狼星只不過是賽博版的沃霍爾。Sara可能只是他的藝術項目,而不是他的愛人。同時,其他人都等著天狼星引導話題。他有心情聽聽別人的想法嗎?圖恩鎮怎麼樣?他想好下一期的主題了嗎?
從記者轉型為明星製作人的天狼星是Mondo的大腦「負責人」,他也是不斷壯大部落的模因裁判。由天狼星最後決定一個模因是否值得印刷出來,而他與「運動」保持距離的能力給了他一雙幽默家的雙眼來看待世界,他本人並不完全參與其中,世界完全是個縮影。在心智完好無損地經歷過60年代之後,天狼星以驚人的寬容姿態,接待每天造訪Mondo之家的人:賣力討好的人以及揮舞拳頭的人。在某些方面,他是最真實的賽博利亞人,R.U.天狼星只提出問題,詢問每個人,詢問展示給他看的每一件事物。他虛假的笑容,迷幻的「眨眨眼」語氣讓他無動於衷於任何想法。他「無計劃」的政策激怒了一些人,但也偽裝了光鮮雜誌中的模因,披上了一層無害糖果的外殼。見鬼了,60年代最強勁的酸出現在米老鼠吸墨紙上。
天狼星坐在搖椅上,沉默著微笑了一會兒。他知道,這些人是他心甘情願的臣民,不是農民與國王的關系,而是音頻采樣和浩室音樂家的關系。正如那天早些時候,他講道:「我想要在我身邊聚集奇怪的人,我就是那種復制-黏貼的藝術家。」他等待著人們給他提供拼貼元素。
「我們在談論時間的盡頭。」一位表演藝術家最後開口道,「誰能到達,而誰又到不了。」
「她想說,通過時間盡頭的偉大吸引器」另一個人繼續說,「進入下一個維度。」
「只有付費訂閱Mondo 2000的用戶才能進入超空間。」天狼星戲謔道,「當然,還有對雜誌做出貢獻的低薪工作人員。」
大夥兒笑了起來。嘲笑暗示著他們將會獲得獎勵,進入下一個維度,因為他們現在賣力工作,獻身於Mondo,尤其是那些沒有要求太高稿費的作者們。天狼星換了一副更加真誠的口吻,也許是為了科恩,他時不時地在筆記本上記錄些什麼。這是一媒體向另一媒體講述元媒體。
「我不確定這一切將如何過去,真的。」天狼星慢慢講道,這樣科恩的筆能夠趕上他的語速。「全部人類是否會發展成一個龐大群體,或只是一小部分,這很難推測。我認為都不會是富有的、枯瘦的白人共和黨活到最後。更可能是那些能夠應對個人技術的人們,還有那些在自家車庫發明科技的人。你必須在你的地下室擁有自己的DNA實驗室。」
「我有這個關於新時代人類和電視的理論。」賈斯從椅子上端坐起來,准別好發言。輕松的環境不會減少個人和專業風險。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場編輯會議。
「新時代的人們和Mondo們以及迷幻時代的人們一樣,他們出門露營,因為他們害怕科技。因為成長於60年代,父母會拿走電視機作為懲罰。另外,電視成為了電子保姆,扮演著權威角色。我認為必須要觀看一定數量的電視,這樣才能獲得徹底的突變,成為我們中的一員。他們做得還不夠,所以成為了新時代人,對科技有著輕微恐懼症。」
這是停頓了一下。房間內的大部分眼睛看向天狼星,等待他對這個理論的判斷,可以是一個眼神,或者一項編輯任務。這個想法會成為新哲學病毒嗎?
「嗯……也許……」他笑了。沒說更多。
賈斯下了樓,掩飾自己被擊敗的事實。穆女王倒了更多咖啡。在廚房的那個傢伙走了。有人在放錄像帶。瓦爾特現在想知道他喜歡薩拉的什麼地方,看了眼手錶。不知何故,很難想像這次聚會的人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游吟詩人。(穆女王後來告訴我,比起在有限時間內我接觸道的天狼星同伴們,雜誌的業務運營其實更傳統,更商業化。)
但也許這就是真正的賽博利亞:不去解決復雜的計算機問題,吸收新的迷幻物質,又或者依靠設計師的薩滿之旅而生活。不去學習媒體病毒、混沌數學或者浩室音樂的專業術語。而是搞清楚兩個在同一城鎮兜售藥物的人不會彼此發瘋;學會如何將矽谷最繁榮企業的前途與迷幻藥使用者的價值觀匹配。賽博利亞將夜店變成了現代版的瑪雅廟宇,不受警察打擾;它會檢查你的銀行帳戶情況,看看是否你的ATM被破解了,搞清楚情況懲罰破解了ATM的孩子們,而不讓他成為頑固的罪犯。那些聲稱自己沒有計劃的人們的計劃不會影響到賽博利亞,還有那些說著空虛、空洞陳詞濫調的人。賽博利亞學著將我們文化的真理包裝成對媒體友好、只有比特大小的作品中,然後找到編輯願意列印出來,因為他會覺得很神奇。
應對賽博利亞意味著使用我們當下有限的人類語言、身體、情緒和社會現實,來迎接擺脫這些限制的事物。像虛擬現實、智能吧、超文本、WELL、角色扮演遊戲、DMT、浩室、分形、采樣、反助興音樂、技術薩滿、生態恐怖主義、形態發生學、視頻賽博格、圖恩鎮、以及Mondo2000等等,慢慢拖動我們的社會,甚至我們的世界,穿過偉大吸引器的事件視界,直至時間盡頭。但就像這些,下一個登上新聞頭條或者計算機網絡的驚天動地模因可能是一段失敗的關系、毒品蕭條、或者門口的小便。
對每個人來說,賽博利亞都很可怕。不只是對技術恐懼者,富有的商人,中西部農民和郊區主婦,而是大部分人,那些希望登上信息浪潮巔峰的男孩兒、女孩兒們。
讓我們浪起來吧。
來源:機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