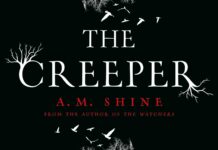楊慶祥
一個「回憶症」患者的孤膽之旅 |《七步鎮》讀札
來源:楊慶祥大風號專欄
一、
作為小說最基本的組成部分,故事重要嗎?也許這是個不言自明的問題,君不見多少研討會、批評文章都圍繞「故事」展開,以至於書寫「中國故事」變成了當下最流行的意識形態。這當然沒有問題,但我們也可以聽聽睿智的福斯特的觀點,他對此有極端的態度。
福斯特說故事是小說中最低級的層次,只有那些心智不夠健全的原始人才熱衷於讀故事,因為故事可以讓他們從昏昏欲睡中驚醒,從而保證不被環伺四周的野獸們吃掉——更進一步,福斯特認為當代的很多電影,比如好萊塢傳奇,也不過是發揮同樣的功能,僅僅是刺激神經,而對精神生活無益。但有意思的是,即使對故事如此大加鞭撻,福斯特依然用了很大的篇幅來論述故事的種種面向,並且將故事的變種之一——情節——的地位提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我大概能夠明白福斯特的這種良苦用心,他將故事視作一個前現代的觀念形式,僅僅是在時間的向度上展開,而將情節視作是一種更高級的現代的觀念形式,是在復雜的因果鏈中展開。簡單來說就是,情節依然是故事,不過是,它採用了更加復雜的視野和維度來結構故事,從而突破了前後相繼的單一性講述方式。
一言以蔽之,對於一個小說家來說,如何用更高級的形式來講故事,依然是衡量其是否有創造力的首要標準。
以這個標準來看,陳繼明的《七步鎮》是一部很高級的小說。

作者:陳繼明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年1月
從內容上看,《七步鎮》集中在三個層面,一是作家東聲在當下的寫作和愛情;二是其故鄉《七步鎮》近年來的人事變遷;三是土匪李則廣的人生際遇。這三者都是普通的題材,日常生活,鄉土變遷和歷史傳奇,也是近年來小說家們熱衷的內容。因此,對於陳繼明來說,首要的挑戰就是,如何規避那些已經成為「成規」的故事講述方式,從而尋找到一種新的講法。陳繼明的野心在於,他試圖整合這三者並將這三者鍛造為一個有着內在肌理的完整的「故事」。於是,小說的開篇就給出了一個設定:
原因是,我患有回憶症。大家也許並不知道有回憶症這麼一種病。回憶症,的確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病,死不了人,對健康沒什麼明顯的影響。……回憶症的症狀不難猜想,即:不能不回憶,一旦開始回憶就沒完沒了,很難中止。任何一個偶然因素都有可能觸發某一段特殊記憶,這原本很正常,人人都會如此,然而,對一個回憶症患者來說,墜入回憶卻殊為危險,如同災難,他們會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會反復糾纏事件的每一個細節,有時會對其中一些關鍵的細節做出修改,以便演繹出更好的結果,或者更壞的結果。
一個患有回憶症的作家東聲於是成為了這個故事的主角,這個設定至關重要,它是敘事的邏輯起點,因為只有通過回憶症,歷史和過去才能「奔涌」於當下。我們毫不懷疑這是一個完全的「裝置性」結構,但是正是在這個裝置里,故事才變得高級,而小說的旅行,也才能行得通。
順便說一句,在《十月》上刊發的版本,開篇多了一段「走向文學之路」的前史敘述,個人認為完全多餘。
二、
在現實中的東聲,是小有名氣的作家,大學教授,正苦於書寫一部新的長篇。他遭遇到的第一個影響其生活的人,是居亦——陳繼明小說中人物的名字都很有深意,我們暫不探究。居亦是一個在讀博士,年齡大概可以做東聲的女兒。但是沒有關系,這絲毫不妨礙他們之間發展出如火如荼的愛情——這愛情來得過於快捷迅猛,不但是讀者,甚至連主人公東聲都覺得有點不合常理。但小說已經如此展開,我們似乎也可以不必拘泥於現實邏輯和小說邏輯的不一致,在一部強調創造性的作品中,我們往往看到的是小說邏輯對於現實邏輯的背離。我們的主人公東聲有過數次婚姻,也經歷過幾次愛情。但是,依然有一種無愛的匱乏感。而對於年輕的居亦來說,「你愛我嗎?你愛我多一些還是我愛你多一些?」是哈姆萊特式的疑問。這兩人,雖然年齡懸殊,經歷不同,但是在一個共同的當代時空中,都對愛充滿了渴望和欲求。
我有人愛嗎?這可以視作小說的第一個主題。
不止於此,還有另外一個東聲,還有另外一個主題。這個東聲患有精神疾患回憶症,在回憶中他夢見自己的「前世」,騎着一匹白馬,穿軍裝,斜跨槍支,走在七步鎮的街頭。「我是誰」這個古老的哲學命題被陳繼明置換為「我的前世是誰?我的夢中為什麼會重復出現這樣一個場景?」這樣一個需要藉助敘事來解決的小說問題,於是,小說的敘事模式轉換為偵探式的田野調查。返鄉的理由得以成立——去為自己的夢境尋找一個現實性的緣由。夢境和前世意味着某種非「現實性」,而回憶症恰好又是非常現實性的困擾,當東聲開始他的返鄉之旅時,意味着一種「現實性」和「非現實性」開始糅為一體。與此同時,歷史和現實之間的對話也告開始。
寫到這里容我盪開一筆,我在前文已經提及,對李則廣的書寫屬於歷史小說的范疇。歷史題材一直是小說寫作的寵兒,但歷史題材也最容易被庸俗化處理為一種簡單的「歷史故事」和「英雄傳奇」。正如本雅明所謂的歷史唯物主義必須是一種「當下」的歷史性,歷史題材的現代處理也必須是一種當下對歷史的突入,而不是僅僅書寫一種靜態的「過去發生的故事」。
陳繼明應該對此有着十分的自覺,因此,我們在小說中讀到了一種猶豫不決的語調,對自己前世的生活和故事始終有一種不確定性。從敘事的層面來看,對土匪李則廣的調查是在建構故事,但是與此同時,因為時間、當事人、史料的種種缺陷,這一建構同時又變成瞭解構。也就是說,這里面藏着一個「正反」雙重的敘述機制,如果讀者們僅僅是為了讀故事,也許將不能看到這一敘述機制所帶來的智力挑戰。
無論如何,在草蛇灰線般的架構和溯源中,作家東聲的前世漸漸被勾勒出來了——雖然這線條還是過於粗糙,而真實性也讓人懷疑。為農,為兵,為匪,情愛,仇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感興趣的讀者自可一讀。我想強調的是,在這個故事里,有一個核心的問題,那就是,李則廣以一種殘酷的方式——剝人皮——殺人了嗎?在我讀到的版本中,對這一「殺人酷刑」有大篇幅的描寫甚至考證,這麼寫是為了展示人性的黑暗和殘酷嗎?這讓我想起莫言《檀香刑》中對凌遲的書寫,人類黑暗和殘酷歷史真是太漫長了!而作為一個書寫者,該如何來處理這種殘酷和黑暗?
這就是我想指出的,這部小說的第二個主題:我有罪嗎?
如果我的前世——雖然科學並不能證明我的前世和「今我」之間有必然的因果邏輯——殺了人,那「今我」有罪嗎?
如果人類彼此殘殺,作為人類的一分子,我有罪嗎?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開篇就尖銳地提問:如果羅伯斯皮爾再砍下法蘭西的萬千人頭,還有人為大革命喝彩嗎?
在《七步鎮》中,敘述者有這麼一段反思之語:
在我看來,剝人皮比殺人更不能接受。因為,剝人皮是殘忍。殺人是兇狠。殘忍和兇狠略有不同,甚至大有不同。殘忍是有組織有計畫有方法地對人進行摧殘和折磨,比如,同樣是死刑,五馬分屍就比腰斬更為殘忍。比如,同樣是暴力,冷暴力比肢體暴力更為殘忍。同樣是武器,生化武器比常規武器更為殘忍。納粹大屠殺,一開始是用子彈射擊,後來想出了「更人道的殺人方法」:用毒氣殺人。猶太人以為他們進了浴室,但是,進去後才發現浴室的蓮蓬頭只會釋放毒氣……
殘忍常常和才華和智慧成正比。
再問一句:如果人類的罪行罄竹難書,那我有罪嗎?
三、
寫到前世,讓我想起另外一位作家,日本的遠藤周作。他完成的最後一部長篇《深河》,講的是來世的故事:中年男主角的妻子死了,他四處尋找妻子的來世,最後在這個過程中更深入地瞭解了本來陌生的妻子以及本來陌生的愛。雖然有不同的背景和指向——遠藤更指向宗教性的東西,他更著名的小說《沉默》尤能體現這種指向,而陳繼明的《七步鎮》更指向歷史性的東西,雖然他的歷史性是一種帶有精神分析色彩的歷史性——但是,卻都涉及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那就是,在「形而上學」和「天道」都不能提供行動指導的現代語境中,人應該如何保全其精神性?在終極的意義上,也就是人如何成為一個看起來「完整的人」——至少是也只能是看起來「完整的人」。
在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之前,需要治癒自己,這正是《七步鎮》孜孜以求要完成的工作。
心理治療的方式首先就失敗了,這一點基本上是一筆帶過。
然後是性的治療,但結果也並不樂觀:
「人類對性的渴求,和對食物的渴求沒有本質區別,為什麼可以隨口說出餓了、渴了,而不敢大膽說出,我想做愛了?尤其是女人?」
我承認,聽了居亦的話,我反而不會做愛了,原因很簡單,做愛的時候,我變得憂心忡忡,我要在乎很多問題:我的男性身份、文化身份、哪些言行可能觸犯了禁忌、調情是否涉嫌輕浮是否含着性別歧視、做愛的力度是否合適是否涉嫌暴力……我甚至很容易就會突然掉鏈子,做着做着,思想深處不小心開個小差,就陽萎了,就像從天外飛來一把鋒利的刀子,准確地越過所有的障礙,擊中要害。更要命的是,突然掉鏈子竟然成為一個習慣,哪怕不開任何小差,也會在某個時間點上如期而至。
最後是歷史和人性的治療:
突然,我不相信我的前世李則廣會剝人皮,會有製作人皮鼓的雅興。我不相信李則廣有那麼壞,也不相信任何人有那麼壞。不相信姓馬的回民有那麼壞,不相信兩家子寄居在他鄉異地的陝西人有那麼壞。
經歷這種種治療之後,我們的主人公作家東聲痊癒了嗎?他在前世今生中穿行,在歷史和現實中漫步,在人情世故里察言觀色……至少在小說的結尾,他獲得了新的認知,他是否真有一個前世,他的前世是否真的殺人越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重新拾起了對人性的信心——「信」——這才是最好的靈丹妙藥。
有了信,才有愛,有了愛,才可以抵抗墮落與罪行:
我突然渴望開始一次新的寫作,以從未有過的魄力,用自然、精確、銳利的文字,撥開歷史的迷霧,捅破認知的侷限,到最幽深的地方去,到最迢遠的地方去。
一次旅行結束,一次新的(小說之)旅又開始了。
內容簡介

「愛是我們貧賤的一種標志」,有多愛就有多怕。那決定了我們命運的,不在記憶的深處,就在時間的遠處。我們需要被拯救,而不是被治療。
男主人公東聲患了回憶症,四處求醫中遇到了女孩兒居亦,遇到了自己的前世,遇到了歷史,還遇到了潛藏在婚姻失敗、生活焦慮中的「我」。於是,他回到故鄉,尋找前世,尋找歷史,尋找「自我」,尋找愛的理由。他找到的是自清朝以來寧夏兵匪頻仍的歷史,找到的是西北人的性格,也找到了自己的前世——土匪李則廣,他曾加入胡宗南的部隊,參加過中條山戰役,之後卸甲歸田,1966年被同鄉殺死。他的同胞兄弟,去了延安,建國後主政一方,李則廣死後他才返回故鄉。
「出門七步,遇敵十人」是七步鎮的諺語。以「七步」為名,就是以殺伐決斷為名。古有「七步詩」裁決兄弟生死,今有「七步鎮」量度前世今生。相愛相殺,不只是歷史和現實,還有昨天的自己跟今天的自己。
這一部感性、智慧的小說,語言盪漾,故事細密,情節迷人。格局、情趣和深度都足夠豐沛。
如果你還沒有失去文學感受力,就會知道,它幾近完美。
作者簡介

陳繼明《七步鎮》 | 當愛出現,一切都如春天般甦醒
來源:華人頭條來源:人民文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