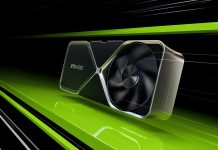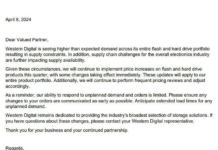1994年,台灣茶人在收藏的普洱茶餅內票上找到原產地,遠赴雲南易武,尋找老茶。
27年後,我偶然看到他們當年拍下的一張照片,臨時起意也想去趟易武,尋找老街。
在那張豎幅照片上,上半是雲霧籠罩的高山,下半是泥牆黛瓦的小村,看不出前後景相隔多遠。民居依山錯落,破爛的主路與一條石階小徑在畫面中央交會,不知各自通向何方。

現在,易武老街僅剩的幾間老宅被茶葉作坊包圍著。 (丁子凌/圖)
古樹新生
聽說我要去易武,賣茶的朋友很詫異:「你又喝不了茶,一喝就醉,去幹嘛?」幾個月前在西雙版納為旅遊指南調研的朋友拋來一張街道開膛破肚、泥濘不堪的照片,「易武地方不錯,就是大路修得一塌糊塗。」我樂觀地忖度著,已經開始進入春茶季,肯定修好了。
去易武註定要翻山越嶺,充氣枕隨著海拔起伏時脹時癟,路邊植被從橡膠樹、香蕉樹漸漸變成茶樹。穿過氣派的「中國貢茶第一鎮」牌樓,路邊開始零星出現人家和茶廠,又行一陣,車子在狹窄的街道左右閃躲,終於停了下來。雖然朋友已經打了預防針,眼前的塵土飛揚還是猝不及防,一輛外地牌照的越野車呼嘯而過,我趕緊壓了壓口罩。
不足兩公里的主街很快就走了個來回,路面還在修,房子還在建,易武看起來並沒準備好迎接來搶春茶的各路茶商大軍,我過於樂觀了。不過轉念一想,茶客大概不比遊客,有好茶就夠了。短短一條街上,賓館、客棧一家挨一家,茶莊、茶號、茶廠、茶葉初制所……各種名頭的招牌宣告著,茶是這里的「命根子」。
初到易武,不見一絲那張老照片的印跡。我灰頭土臉地找了家客棧,隨口想還個價,正在喝茶的老闆笑道:「一看你就是來玩的,不懂行情,再晚幾天,三月下旬到四月,我們還要漲價呢。」說著邀請我一起喝茶,我喝第一杯時,他瞟了一眼,大概已經看出是個外行,強調道:「我這可是純正的古樹茶,不像外面賣的易武茶都不知道摻了什麼。」我辨不出真假,只覺得喉嚨很滋潤,回甘持久,想要多飲幾杯又怕醉茶,老闆見我無意買茶也意興闌珊。
雖非茶友,我卻老愛往茶山跑,之前去景邁山、南糯山、章朗,都會給親朋帶些古樹茶,這兩年越發覺得買不起了。2007年,普洱茶市場曾像股市一樣崩盤,資本洗牌後,茶價又重新上漲,一路飆升到每公斤干毛茶成千上萬元。確切地說,值錢的只是古樹茶,多古才算古呢?茶友、茶農、茶商眾說紛紜。2011年頒布的《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古茶樹保護條例》將古茶樹限定為野生型茶樹和樹齡在100年以上的栽培型茶樹。然而樹齡的測定並非易事,大部分都是老人憑記憶口口相傳。
作為後輩的台地茶廣泛種植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這種茶樹低矮密集、萌芽力強、產量很高,使得東一棵西一棵、不便採摘管理的古茶樹相形見絀,在很長一段時間都被棄置,甚至砍倒。誰料命運輪轉,現在古茶樹翻身成了搖錢樹,採茶葉就像摘鈔票一樣,要爬再高都沒人抱怨了。

晴時露天曬青,天氣不好則利用曬棚。 (丁子凌/圖)
瑞貢天朝
離客棧不遠的岔路口立著一塊大石頭,厚厚的灰塵蒙住「茶馬古道」四個紅字。從那里拐上坡道,爬至高處俯瞰易武,腦海中冒出四個字——野蠻生長,正如當下的普洱茶市場一樣。雲南古鎮常見的屋頂露台在這里大多用透明建材圍了起來——那是給茶葉遮風擋雨的曬棚。
遠遠看見幾株大榕樹遮天蔽日,這片被稱為公家大園的樹蔭下,曾經每日迎來送往,馬幫在這里歇腳、裝卸茶葉、舉辦隆重的啟程儀式;如今忙碌的場景轉移到各大快遞公司運營點,而這里只有茶客朝聖和遊客打卡,也是不遠處易武小學孩子們的遊樂場。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茶馬古道起點」,幾個外地年輕人正在錄製視頻,不知是做茶葉還是旅行自媒體。我退到遠處想拍一張全景,坐在坡地上玩耍的男孩喊道:「拍樹幹什麼,神經病!」也許在他們眼里,正常的遊客都應該去拍樹下的雕像:馬鍋頭趕著六匹馬,馬背馱的竹筐上分別刻著——曼撒、倚邦、革登、蠻磚、莽枝、攸樂——西雙版納古六大茶山的名字。

幾株大榕樹庇護著茶馬古道起點。 (丁子凌/圖)
古六大茶山中,曼撒屬易武土司管轄,因火災衰落後逐漸被易武取代。從清朝中期到20世紀30年代,易武一直是普洱七子餅茶的加工集散中心。從這里啟程,馬幫兵分三路:北上赴京、西穿藏地、遠下南洋。其中運往京城的頭等要緊,那是給清廷的貢茶,1732年起,易武和倚邦土司分攤貢茶任務,易武主辦約130年,年納貢66666斤(舊制1斤等於596.8克,約合40噸)。飲用普洱茶一度成為皇宮貴族的風尚,見多識廣的曹雪芹還在《紅樓夢》中點了一筆普洱茶有助消化的功效。
易武茶文化博物館內藏的一塊碑上記載著,雍正、乾隆年間,為應付巨大的貢茶採辦壓力,清政府號召漢人上茶山,給外地茶商頒發執照。響應最積極的是石屏人,這些明朝初年從江南遷到雲南的移民,給易武帶來精細的制茶工藝和先進的經營理念,在傣、哈尼、瑤等民族的世居山林里建起一座漢人商業王國,創辦知名茶號數十家,聽管理員介紹,博物館所在地就是石屏會館的舊址,易武許多村寨主體都是石屏人的後代。
經人指路,終於在山的另一面遇見靜謐的易武老街。石板路尚在,老宅仍存幾間,爬來爬去也沒對上照片中的街巷,索性閒逛。大炒鍋旁堆得高高的柴火,隨處可見的曬架和竹簸箕,外牆上的宣傳照片、文字和二維碼……幾乎每家都能找到經營茶葉生意的線索。
每隔幾步就會碰到由政府設立的重點文物保護碑,寫著某某茶號舊址。這些老茶號有的被後人重新註冊經營,守住老宅和家業;有的則遭人搶注,房屋也幾經轉手,命運不盡相同。其中車順號曾獲道光皇帝御賜的「瑞貢天朝」牌匾,代表著易武貢茶歷史的高光時刻,如今車順號舊址門上貼著孝聯,複製的牌匾正對著一個簡易雞窩。

老茶號車順號獲御賜「瑞貢天朝」。 (丁子凌/圖)
清末,普洱茶隨時局衰落。抗戰時,東南亞銷路又被完全切斷。建國後,私人茶號逐漸收歸國有,而後受政治運動影響,茶山一度荒蕪。1970年,易武老街又遭大火,一半淪為廢墟。
好在,先民種下的古茶樹一直堅韌地生長著,而當年走水路到香港的茶餅也為多年後的普洱茶復興埋下種子。
易武滋味
在老街上路過一間敞著門的家庭作坊,我探頭仔細打量了一番,空間不大,設施簡陋。兩張大炒鍋嵌在靠牆的水泥灶台上,旁邊的機器看起來也是炒茶用的。地上鋪的方形蓆子、架上堆的圓形大簸箕都由竹篾編成,中間或深或淺地浸染著茶葉汁液的顏色。茶農採摘的鮮葉經過攤晾後,在這里完成殺青和揉捻兩道工序,炒茶的火候、揉茶的手法都沒有統一的說法和標準。無數個類似的小作坊、初制所散落在雲南各大茶區的村村寨寨,我不禁對其衛生監管打個問號。
下到坡底的一片平地,成排的簸箕整齊躺在曬架上,經過揉捻的茶葉捲成條形,薄厚均勻地鋪展開,等待完成曬青環節。我把相機高舉過擋在身前的鐵絲網,主人冷冷丟下一句「不能進去」就轉身回屋了。又至一棟老宅,見院里兩個女子正圍著一大堆曬乾的毛茶埋頭挑挑揀揀。曬青毛茶是茶商收購的主要產品,它們經過高溫蒸濕、壓製成形、自然風乾,成為普洱生茶,在蒸壓前加以渥堆發酵的便是熟茶。

人工從毛茶中挑揀出顏色、形狀較差的「黃片」。 (丁子凌/圖)
傳統普洱茶製作工藝的復興源於台灣茶人,也就是1994年到易武追根溯源的那批人。制茶工藝找回來後,隨著古樹茶的火熱,普洱茶界逐漸形成產地意識,像咖啡和葡萄酒一樣,講究一山一味,不同產地的氣候、土壤、微生物等因素造就出獨特的滋味。其實早在貢茶時代,易武茶號的產地意識就已經寫在內票上:「自曾祖住易武百年有餘,揀采春季發生之嫩尖茶,新春正印,細白尖,並未摻雜別山所產……」而在衰敗的數十年間,易武茶葉只是作為原料交付給國營茶廠,混在其他茶區的茶葉里,默默無聞。
最近幾年,普洱茶的原料來源被細分到越來越小的村寨和山頭,高級玩家甚至只喝單株古樹茶。成熟的茶商腦袋里都存著一張表格,對比列出易武各個小微產區茶葉的滋味、價格、產量和品質。表格不斷更新,新產區也在不斷開發中,越是險以遠、至者少,越能吸引茶人朝聖、茶商炒作,這一點倒是跟旅行有點像。
古茶樹本就稀缺,產地劃分得越細,單一產地的產量就越少,往往有錢也買不到。茶農過度採摘、大小樹混采,茶商弄虛作假、以次充好,似乎已是坊間公開的秘密。茶企、茶商、茶友,以及像我這樣的旅行者都想親臨易武,修路、建廠、蓋房,無不對古茶山的自然生態造成威脅。尋找老街的心愿已了,我便沒再往茶山深處打擾。

鎮子周邊種著台地茶,古樹則散落在更偏遠的茶山。 (丁子凌/圖)
告別易武前,坐在客運站等班車,看到座位上的灰塵已經懶得擦了。一個瑤族小伙子過來託運包裹,我以為是寄新鮮的春茶,卻見箱里塞滿紅彤彤的羊奶果,噪子冒煙的我一邊望果止渴,一邊尋思著,無論茶人口中的易武茶多麼柔和順滑,也許對離家在外的易武人來說,最想念的不過是那羊奶果的酸澀滋味。
丁子凌
來源:kknews易武古鎮,因茶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