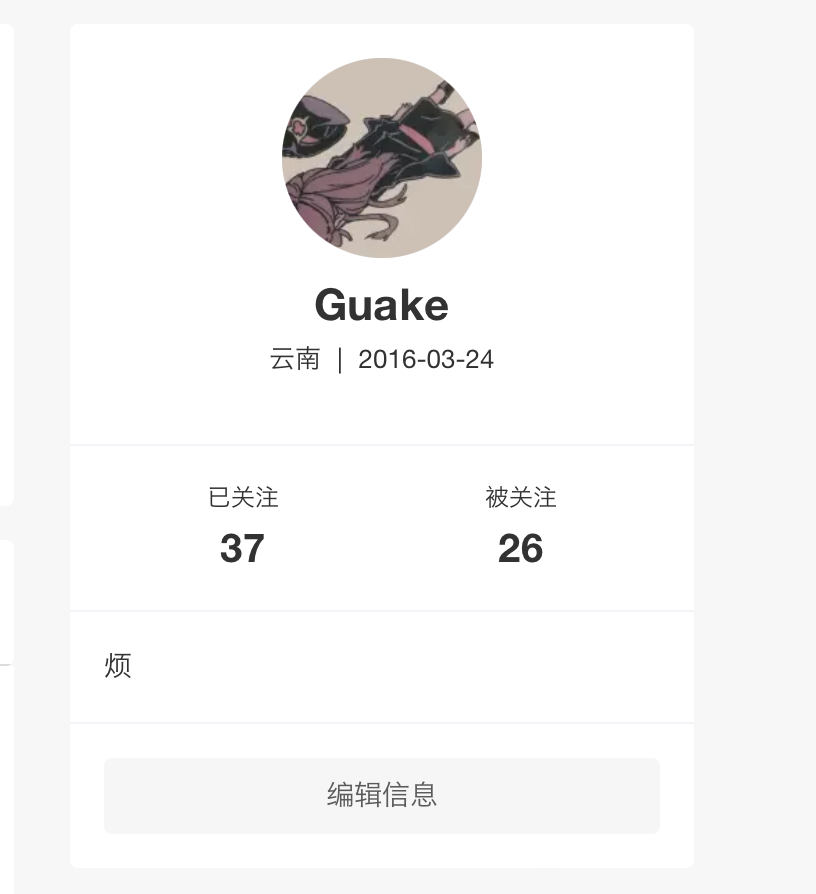寫在前面&前情提要
本文是《為什麼沙丘2不只是一個科幻的中世紀的故事》的下篇,可以單獨閱讀,也可結合上篇一起看。本文同時含有對《沙丘》小說和電影的劇透。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為大家簡單介紹了現代帝國和帝國主義在《沙丘》中的體現。本文將借《沙丘》宗教和美國《獨立宣言》的歷史去討論電影《沙丘》除帝國主義外的現代性內核。
生來就是那個「必定」的救世主?
保羅生來就是救世主嗎?關於這一點,無論是電影還是小說都給出了一些明確的信息。首先,弗雷曼人的宗教並不是在厄拉克斯上自身封閉演化出來的,整個「造神運動」中,充滿了姐妹會的計劃:
換句話說,這個「造神運動」人世間的力量所計劃事物,而非有高位神行動在其中。其次,電影中保爾的夢境也不是完全無誤的「預言」——保爾夢見到契尼被核輻射照射後燒焦,但在實際作戰中並沒有真正出現這樣的情況。因此,整個保羅成為「彌賽亞」的過程中,「存在一個掌控世間所有事物的神」這一命題是不穩固的。換句話說,這個過程應當是受到人世間各個人的所作所為深刻影響的。那麼進一步我們可以得出一個來自於邏輯推導的結果:《沙丘》系列,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其於宗教的處理,並不是復現一個生活在中世紀的人對宗教的看法,而是站在一個更加現代的視角去敘述這個故事。接下來,我將介紹一些現實世界中的宗教理論,以繼續剖析《沙丘》中的現代性和宗教。
宗教指南
在繼續討論之前,我會給出一個恩格斯對宗教的論述,以供參考:
這種「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無論在厄拉克斯還是我們自己的世界中,無疑都包括自然環境以及人類自身的創造物。人類在與這些事物互動時,需要持續不斷地將這些事物囊括在人的意識觀念中去理解並運用,而這一過程,我們可以稱之為文化(同上,252),而一個完備的宗教應該是成體系化的文化,而這樣的文化採取了超人間的力量形式,也就是「神」。而弗里曼人的宗教文化更是對這一論述的具體反映:沙漠、沙蟲、水以及弗里曼人自身都是自然的一部分。如要在厄拉克斯生存,弗雷曼人需要理解並適應周遭的一切,使其在代際和族群中能被傳播和傳遞。
讓我們回到電影《沙丘2》中的葬禮環節——這是一個絕佳的弗雷曼人藉助宗教(體系化的文化)適應「外部力量」的例子。在葬禮上,弗雷曼人面臨著兩個困局:死亡給人帶來的悲傷和水資源的稀缺。在社會生活中,人與人的聯系是以網狀結構運行的。一個人的死亡,往往意味著這樣的網狀結構出現了一個缺口。如果說種種社會關系網是人賴以生存的客觀存在,那麼一個缺口的存在意味著對網狀結構內所有人生存的威脅,人們由此被拋出了某種日常生活秩序中,悲傷與恐懼會接踵而至。如果不對屍體進行處理,對即將腐敗的屍體的厭惡和對親人的追思所產生的矛盾將持續使人暴露在理性的矛盾之中(Olberding 2015, 150),因此一個能將這種矛盾彌合的「文化」是必須的。其次,弗雷曼人無時無刻不面臨水的問題——人體內70%的水不應該在厄拉克斯這樣的星球上被浪費。而弗雷曼人的體系化的以及需要被實踐的文化(也就是宗教),給予了弗雷曼人一種可被接受的認知方式和衍生於此的實踐方式——一個抽乾死者身上水的儀式(沙丘2[電影],19』9′-19』50″)
首先我們說水。在弗雷曼人更具體的宗教經書中,水具有絕對的優先級:
在小說文本中,水被體系化地表述為可以被交易的客體化的貨幣,也時常被表述為生命本身:
換句話說,這種部族作為的弗雷曼人的社會組織模式,衍生出一套人身歸屬權。而這樣的人身歸屬權,又被以水的歸屬權的形式被理解與接納。那麼人活著是部族的人(水),死後自然也應當是部族的人(水),人死後由部族將其身體里的水抽乾是合理的。在此,宗教作為超越性的規定,它為弗雷曼人運作水資源的實踐提供了理性的保證——「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就是(缺)水對於弗雷曼人的日常支配,而人間的力量(關於水的需求和實踐)採取了超人間的力量形式,也就是宗教。
其次我們說儀式。在《沙丘1》小說中(364-378),當詹米的水被抽乾後,詹米的朋友們坐在一起敘說詹米的生平,同時也在分配包括水在內的詹米的遺物。而在儀式之後,詹米的妻子和孩子的未來也經由葬禮和習俗得到了保障:
最重要的是,這樣的行為是藉由宗教文化去規范化的,而非哪個人的即興表演。因此,我們可以說整個弗雷曼人的葬禮,將死亡帶來的人際關系網漏洞緩和並填補上了。死亡與水,這些支配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性力量帶來的創傷與問題,盡管是由具體的人為的力量去解決的,但是卻需要宗教這種看似超越性,實際上卻仍然人為的力量去解決(鑒於弗雷曼人的宗教是姐妹會的計劃)。弗雷曼人的宗教是實用的,符合邏輯的,也是顛倒的。這也應證了一段馬克思對於宗教社會的評論:
造神與神造
相比作為他者的弗雷曼人,保羅更接近於我們——一個銀幕前的現代人。在他的家族不得不捲入厄拉克斯的爭斗之前,他對厄拉克斯的認知範式和我們相差無幾:用自己使用的語言聽取人類學家的的調查、閱讀百科全書、聽自己人對厄拉克斯的數據報告、各種來自於帝國內部的傳聞……(說句玩笑話,也許我們現代人還不如保羅,因為我們有短視頻和公眾號,所以能靜下心來看文章的朋友都是好人)
但是當一個被這樣的範式澆灌出來的帝國人,遇上了被宗教澆灌出來的弗雷曼人。彼此認知的顛倒性就顯得淋漓盡致。關於保羅認知中的問題可以具體參考我的上一篇文章:,這里就不多贅述。而當保羅和傑西卡作為「外來人」去理解水這個問題時,他們並不是從宗教方面開始的(沙丘1, 364-365):
水在傑西卡身上是以非常直接的生理反應去被思考的,而回看我們之前提到的弗雷曼人關於水的觀念與實踐,從頭到位都是以宗教的方式去把握的。換句話說,對更接近於我們現代人的厄崔迪家族思考方式的描寫,恰恰是《沙丘》系列中所包含的現代性(modernity)。對於弗雷曼人來說,宗教是先置於他們對水的理解中的:
「上帝創造厄拉克斯,以錘煉他的信徒——摘自伊勒琅公主的《穆阿迪布的智慧》」(沙丘1,363)
簡而言之,對弗雷曼人來說:「我們之所以缺水是因為宗教如此規定」,對可以站在宗教之外去理解宗教的現代人來說,道理就是這樣的:「因為我們缺水,所以我們需要宗教去節水」。
理解了這樣的思維模式,也就不難理解電影《沙丘2》中斯蒂爾格的迷信了。首先,他的信仰是一種基於宗教的生存方式,而且這並不妨害理性能力運作其中。簡而言之,大多數弗雷曼人不依靠保羅的具體行為去理解他們的宗教,而是依靠宗教去敘述保羅的行為。宗教的語言,現代人的語言,具體每天日常所用的語言皆是如此地生產著我們自身。電影中以斯蒂爾格為代表的弗雷曼人對保羅的「迷信」是不可撼動的。
在此我以駁論的方式進行一個小結。小說作者對宗教的處理極其現代,甚至是後現代的——他對厄拉克斯的生態及人文構造包含了對於現代性的思考。而小說中厄崔迪家族視角的存在,更是將現代性刻入了作品基調。「宗教只是迷信」的觀點,在小說中是站不住腳的。電影並非「兩頭靠不上」,小說也更非「完全非理性的,前現代的一個宗教歷史故事」(「兩頭靠不上,所以電影《沙丘2》的改編令人惱火,錄音筆 VOL.161」,2』35』』-2』45』』),因為《沙丘》從來都只有一頭,就是現代性的那一頭。
先知防偽驗證碼
在亞伯拉罕諸教的歷史上,出現過比真先知更多的偽先知。檢定先知預言的真假,可以說是檢驗先知的唯一真理。那麼怎麼在先知的預言驗證前就知道他和他的預言是真實的呢?(畢竟這事關天堂與永生!)我的答案是:無法鑒定。
電影《沙丘2》中,保羅來到了南方並進行了一番演說。在面對部族人群拔刀相向的時候,保羅說出了我認為最有意思的台詞(沙丘2 [電影], 2˚04』36」-2˚04』38」):
保羅面對這種懷疑所採取的回應方式並不牢固——他說了其中一位部族首領祖母的故事。而獲得這樣的一個過去的故事並不需要什麼預言能力,這完全是可以通過合理地方式獲得的信息。他描述的方式是如此強調細節,或者說,他之所以強調細節,是因為過去的故事不是預言,它需要細枝末節的信息,展現無畏的攻擊性(如果他真的能以一敵百,就不需要展現攻擊性了)去講一件他無法論證的事:他有預言能力,他的預言是真的。那麼哪一句是預言呢(沙丘2[電影],2˚05』44」-2˚05』45」)?
而是否能抵達這個天堂,其實靠的是弗雷曼人自身的作戰經驗與意志,還有最重要的:弗雷曼人的鮮血。這正是保羅在騎上沙蟲前,女孩們說的話(沙丘2 [電影], 27』53″):
事實上也如此
這里遺留給弗雷曼人的邏輯學家一個問題:預言沒有實現,那麼眼前這個孩子就無法證明他是否是真先知。先知無法驗明正身,那也就無法確定被領導的我們是在參加一場真正的聖戰,抑或是滿足某個軍閥自己的野心?如果我在會議上看穿了保羅的把戲,那我憑什麼要用自己和自己部族的生命作賭注呢?
讓我們回到一個我們現實中的時刻,一個相似而重要的時刻——美國《獨立宣言》的簽署。
在《獨立宣言》中,有這麼段話:
這段話里的合眾國代表們面臨著同樣的問題(Derrida 1986,10):在《宣言》前沒有合眾國,那麼合眾國的代表如何證明「各殖民地善良人民」給他們的授權是合法的呢?「善良人民」怎麼證明他們是是「善良的」,而非英國屬下的「亂臣賊子」呢(就以法理上來講,在獨立前,這些人屬於英國臣民)?為避免這種非法的存在,《獨立宣言》的起草者傑斐遜在這里所採取的戰略依舊是引用了一位「神」。
這里的行文邏輯是:道理是神定的,我們是依從神定道理的人,而英國人缺不如此遵從,所以我們的所作所為具有合法性。但是,如果依據我們之前提到的宗教的運行模式來理解的話,「we hold」(我們認為)這句話是多餘的,因為自然神與其法則的存在與真實性不需要任何人的成立。下面這段話是漢娜·阿倫特(2011,159)的分析:
因此,漢娜阿倫特對「we hold」的存在做出了更進一步的推論(161):
換句話說(Hoing 1991,108),《獨立宣言》的真正價值在於它是一個述行話語(performative utterance),用簡單的話來說,就是一個關於現實世界中具體的人(美國先賢)的寓言(fable)。這樣的處理放回到弗雷曼人的「獨立宣言」大會上也是適用的——保羅用戰鬥成果、姐妹會的鋪墊、個人道德(如「預言」般獻出眼淚)、智慧(用過去的故事哄騙遲疑的人)、還有臨場發揮,在預言實現之前就賦予了自己統治弗雷曼人的事實。
但是,把這種立國行為化作寓言有其自己的問題(Hoing 1991,107)。它忽略了暴力的在立國中的作用,而帶來了模糊性。促成宣言的獨立戰爭和促成預言的聖戰是無法被語言輕易消除的,而「判斷力,是一個旁觀者把行動轉化為故事的能力」(同上)。在美國政治中需要宗教力量的時候,依舊會有人回到宗教中去尋求保證其語言系統合法性的「超人間的力量」,強調他們「山巔之城」的權利;統一帝國的弗雷曼人也會延續他們僵化的信仰以統合聖戰後國家(保羅不得不在後面的文本中成為反抗他自己秩序的隱士)。無論他們的創立者與先知是多麼深思熟慮,模糊不清的寓言,為我們揭示了一個現代解釋學的道理(馬元龍 2021,7):
尾聲
行文至此,原本計劃的女性議題以及我遇到的一些些新的問題,限於篇幅和本人的能力,只能在此做一些嘗試性的討論了。計劃變動還望各位海涵。
首先是姐妹會。關於姐妹會,我想說的是,在《沙丘》世界中,帝國女性的地位是處於極端被物化和異化的狀態。但是在設定中禁止克隆與禁止智能機器的情況下,女性在帝國的社會結構中仍然掌握著具體勞動力的再生產——生育後代,維護戰爭機器(包括武器裝備和人本身)。而恰恰是受到高度異化,生育還要受到姐妹會規制的傑西卡培養了主人想要的和不想要的——一個毀滅帝國的先知。這正如42所說的:
這也許和被壓迫的弗雷曼人最終摧毀了帝國的故事一樣,是一個寓言,一個關於主奴辯證法式的寓言:主人的欲望要求奴隸實現,而奴隸在每天面對具體事物的勞作與生產中掌握了自然,主人(帝國)依舊需要奴隸的勞動去存在,但是奴隸已經可以隨時准備好脫離主人了。但是當奴隸又回去做了主人准備奴役其他人的時候……這也許就是《沙丘》後幾部小說會討論的內容了
其次是關於電影對契尼的改編,有一種觀點認為這部電影仍然是老生常談處理:女性出走。對於具有血緣親族的壓迫性的結構,反抗往往來得更加復雜。「契尼出走後會如何?」,這個問題真的和「娜拉出走後會如何」一樣嗎?電影里對契尼所做改編給出了不一樣的感覺——除了勇敢,她還清醒,除了清醒,她還能打,除了能打她還有志同道合的夥伴。作戰意志,作戰水平,組織能力,甚至還有掌握蒸餾服的製造和水(蒸餾服與營地里的水由女性掌握)。當一個戰士掌握了作戰的能力與資源之,掌握了戰後建立新秩序的能力,那麼暴力的男性凝視也許要向武器的批判低頭了。
最後是這個電影「獻給誰」的問題。寫這篇文章的初衷,只是因為弗雷曼人的游擊讓我想起了哈馬斯對抗以色列的「反坦克體操」,緊接著我腦海里想到了這麼一句話:「早幾個月上,這個電影在西方主流敘事下,也許就是獻給烏克蘭人的了。」之後又了解到電影上映延期,和好萊塢編劇導演罷工有關系……那麼這場現代文學和現代電影工業為我們營造的夢境到底獻給誰?我的文章是否過度解讀?且讓我再引用馬元龍教授(2021,21)的話給大家吧:
致謝
文章不是什麼史詩大作,因此致謝也顯得矯情與無力。但該有的禮儀還是又得有。謝謝各位閱讀至此的讀者,在這個時代能做長時間閱讀,本身就是稀有價值。感謝機核平台的努力,讓我自己從 8年前的迷茫的小孩變成現在能和大家一起思考的人。
最後的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獻給我的小青苔。你對創作的著迷追求以及堅實的成果是我現世的「we hold」——一切傳奇,或是平凡的故事都自你生發。我們是這個世界的他者,弗雷曼人,弗雷曼人的女性。規訓是來自帝國的:如何書寫,如何說話,如何將自己逼迫到身心破碎……今日奴隸的枷鎖,是我們未來的武器,我們就是最偉大與最可愛的人。我想,我永遠愛你
參考書目
漢娜·阿倫特 [美] 著 ,陳周望 譯,2011. 《論革命》 ,譯林出版社.
馬元龍,2021. 《欲望的變奏——精神分析的文學反射鏡》,北京大學出版社.
弗蘭克·赫伯特 [美] 著,潘振華 譯,2016. 《沙丘》,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文中為區別系列電影小說,標記為《沙丘1》)
丹尼斯·維綸紐瓦 ,2024. 《沙丘2》[電影],傳奇影業.
丹尼斯·維綸紐瓦 ,2021.《沙丘2》[電影],傳奇影業.
42,蘿卜蘿卜蘿,說書人Jerry,2024.《兩頭靠不上,所以電影《沙丘2》的改編令人惱火,錄音筆 VOL.16》,機核網.
Bonnie Honig,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t: Arendt and Derrida on the Problem of Founding a Republic,」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 (1991): 97-113.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New York: Penguin, 1963).
Jacques Derrida,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t,」 New Politic Science 15 (1986) :7-15.
Olberding, A (2015). From Corpses to Courtesy: Xunzi』s Defense of Etiquett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49 (1-2):145-159.
來源:機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