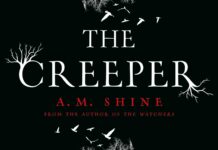愛與死,雷馬克一生的命題
「不需勸誘,你就會被他的作品征服;無需誇張,他就能震撼你的心靈。」
這是斯蒂芬·茨威格對於埃里希·瑪麗亞·雷馬克的評價。作為《西線無戰事》的作者,雷馬克也許是那個時代將殘酷和柔情糅合得最為完美的作家。終其一生,雷馬克因為這部講述一戰故事的小說贏得了巨大榮譽,也遭遇了無盡的苦難。他一生中十多部小說,從未遠離戰爭的陰影。
在雷馬克的寫作中,極致浪漫和極致殘忍的碰撞,使得他每一部作品都給人帶來熾烈、濃郁的情感沖擊。正如諾獎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所說,任何時代都有三件大事:殺人、相愛、死亡,而雷馬克出於身處其中的親歷者,本能地不斷就這一主題進行延展和闡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她說:「在雷馬克和海明威的作品中,有一種男性的浪漫主義和古老獵人的本能。」
1916年11月,18歲的雷馬克自願中斷學業去參軍,踏上「一戰」戰場。他五次負傷,最後一次重傷後被送入軍醫院。戰爭結束的第十一年,也就是1929年,雷馬克做雜誌編輯期間,《西線無戰事》出版了。雷馬克參戰不足一年,在前線的時間更是只有6周,這短短的6個星期改變了雷馬克的一生,也擊碎了世界億萬讀者對於血色浪漫的幻想。上了前線,他們日夜守在戰壕中,「生活」盡是荒謬,與老鼠鬥智搶麵包、分辨不同的炮彈、學會掩蔽、抵禦毒氣……腦袋被彈片削掉的士兵依舊在慣性奔跑,搶來了漂亮的戰靴卻丟掉了腿……他們上戰場前已經看到了為自己准備好的棺材,而死後能得到一副棺材卻又是一個巨大的奢望。

寫就《西線無戰事》的雷馬克,被德國當局認為是「對世界大戰中德國軍人的背叛」。電影在德國遭禁,小說也被公開焚燬。在這段日子里,身處瑞士家中的雷馬克身邊時刻備着一隻打包好的箱子,隨時准備逃亡:「這個箱子總是准備就緒,以防我什麼時候要突然起程。」
1938年,雷馬克被剝奪德國國籍。1939年9月5日,雷馬克乘和平時期的最後一班瑪麗王後號郵輪抵達紐約。此時他已經是知名作家,在榮耀和鎂光燈下,雷馬克的生活在表面意義上達到了完美狀態。
 《西線無戰事》
《西線無戰事》
然而,1943年底,雷馬克的妹妹被行刑,罪名是「渙散軍心」。庭審上,法官羅蘭德·弗萊斯勒說:「因為她的哥哥不在法庭的控制中,所以她要為他贖罪。」遠在紐約、因此背負上沉重心理負擔的雷馬克,在1952年將小說《生命的火花》獻給妹妹。這是他僅僅能做的事。
二戰後,雷馬克回到瑞士馬焦雷湖畔的龍科港,並時常往返於瑞士和美國之間。1970年,他在妻子的陪伴下於瑞士病逝。
在1946年接受《紐約時報》的采訪時,他曾說,寧可這一切都未曾發生。從另一種意義上,他寧可沒有開始寫作。
但他改變不了已發生的一切。在時代洪流前,個人命運如此微不足道。

一個士兵只有度過一千次偶然性才算活着。
——雷馬克
在作品《愛與死的年代》中,雷馬克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恩斯特·格雷貝爾是一名德國士兵,他所在的部隊從法國到北非曾經戰無不勝,但在1944年的蘇聯戰場上,他們卻遭遇了寒冷與失敗。在蘇聯前線待了多年的格雷貝爾終於幸運地獲得了三週假期,滿心歡喜的他輾轉回到後方,但所看到的卻是和前線一樣被炸燬的建築、同樣的成堆的屍體。
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他重識了童年時代的舊友伊麗莎白。兩個孤獨無依的年輕人成為了彼此的慰藉,隨即陷入愛河並迅速登記結婚。很快,格雷貝爾重新回到前線,戰況依舊令人絕望,經歷了愛情洗禮的格雷貝爾更加痛恨納粹的殘酷統治,厭倦了這場看似永無止境的戰爭。
終於,一次偶然的機會下,他開槍打死了篤信德國必勝的黨衛隊員施丹勃雷納,放走了蘇聯俘虜,而他自己也死在了蘇聯游擊隊員槍口之下。
有評論認為,這部小說之於「二戰」和德國士兵,正如《西線無戰事》之於「一戰」。它刺穿人對人的殘暴,也閃現偶爾照亮最黑暗角落的火花。
2017年夏天,世紀文景開始重新出版雷馬克系列作品,選取了九部雷馬克不同時期、不同風格的作品,其中包括翻譯家朱雯和李清華的經典譯本,《愛與死的年代》即其中最新問世的一本。
-節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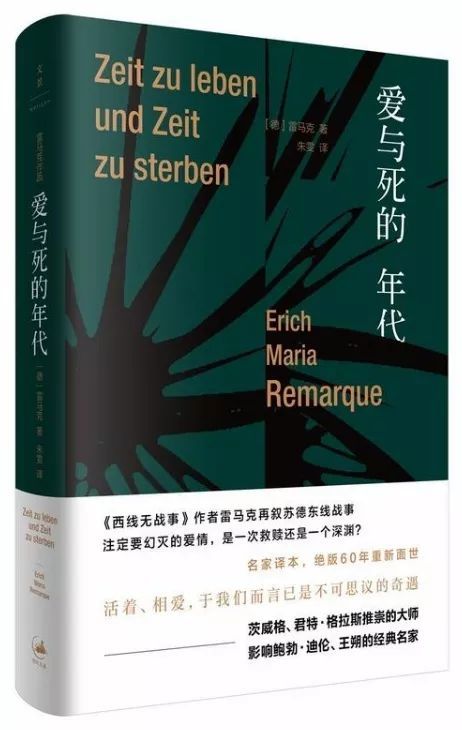 《愛與死的年代》 [德]埃里希·瑪麗亞·雷馬克/著,朱雯/譯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版
《愛與死的年代》 [德]埃里希·瑪麗亞·雷馬克/著,朱雯/譯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版
死的味道在蘇聯跟在非洲不一樣。在非洲,在英國人的猛烈炮火底下,火線中間的屍體也常常躺在那兒,好久好久沒有給埋葬,可是太陽起的作用卻很快。一到晚上,有股甜蜜的、悶人的、濃郁的味道隨風送來——毒氣灌滿了屍體,他們在異國的星光里如同鬼怪一樣站起來,仿佛正在毫無聲息、毫無希望地各自做那最後一次戰鬥——可是一到第二天,他們便開始皺縮,無限疲乏地緊貼着地面,仿佛打算鑽進里頭去似的。要是過後他們能夠被運回去,那麼有的已經很輕,已經干癟,也還有過了幾個星期才給發現的,那就只剩下一些骸骨,在突然顯得太大的制服里寬寬鬆鬆地搖得響了。這是在沙地上、在太陽下、在風里頭的一種乾燥的死法,而在蘇聯卻是一種醃臢的、發臭的死法。
一連下了幾天雨,雪在融化了。一個月前,積雪還要深三碼。那個被轟毀的村子起初看來好像只有燒焦的屋頂,這會兒已經悄悄地、一夜又一夜地從那正在下沉的積雪里冒出來。窗框已經露出來了;幾夜過後,門的拱道出現了;接着,通到下面那污糟糟的白色中去的梯子也可以看見了。雪在融化,融化,而隨着融化,屍體也露出來了。
他們都是陣亡已久的人的屍體。那村子曾經被爭奪過好幾次——在十一月、十二月、一月,還有如今這四月。占領了又失陷,隨後又占領了。來了一場暴風雪,有時候在幾小時里就把那些屍體掩蓋起來,弄得埋屍隊也常常找不到他們——直到最後,差不多每天都有新的雪白的一層撒到廢墟上去,正如一個護士把一條被單鋪在一張血淋淋的、骯髒的床上。
最先露出來的是一月里陣亡的人的屍體。他們堆在最上面一層,四月初,積雪一開始消融,馬上就露出來了。他們的軀體凍得挺硬,他們的臉像是灰色的蠟。
他們如同一塊塊木板似的被埋葬。村子後面有一座小山,那兒雪積得不太深,把雪刨掉,就在凍冰的地上挖了些墓穴。這是件煩重的工作。只有德國人才被埋葬起來。蘇聯人都給扔在露天的圍場上。天氣一轉暖,他們便開始發出臭味。臭得太厲害了,就鏟些雪來蓋在那上面。把他們埋葬起來是不必要的,誰也不指望那個村子會守得很長久。步兵團正在撤退。挺進中的蘇聯人自己會把他們的陣亡者埋葬的。
在十二月里陣亡的人的屍體旁邊,還發現一些武器,這些武器是一月里的陣亡者的。步槍和手榴彈比屍體陷得更深,有時候鋼盔也一樣。這些屍體制服上的標志比較容易扯下來,正在融化的雪早已把布給泡酥了。水積在他們那張開着的嘴里,仿佛他們是淹死在水里似的。有時候,手腳都已經爛了。他們被抬走的時候,身體還是硬邦邦的,可是一條胳膊、一隻手卻會搖啊晃的,倒像那死屍在揮手,那樣子冷漠得怕人,而且幾乎有點猥褻。所有這些屍體一擱到陽光里,眼睛總是先爛。它們會失去玻璃似的光輝,眼珠子會變成膠凍,里頭的冰融化了,慢慢地從眼睛里淌下來——好像在哭泣。
突然又冰凍了好幾天。雪面上長了一層皮,就結起冰來了。雪不再往下沉。可是那時候,懶怠的、悶熱的風又開始吹起來了。起初,只是一個灰色的斑點在逐漸消退的白色中顯現。一小時過後,那已經是一隻向上伸出來的、捏緊着拳頭的手了。「又是一個。」紹爾說。
「哪兒?」伊默曼問。
「在那邊教堂前面。我們要不要把他挖出來?」
「有什麼用啊,風會把他挖出來的。那兒後面的雪至少還有一兩碼深哪。這個倒霉的村子比周圍地勢都低。難道你想把你的靴子灌滿冰水嗎?」
「見鬼,才不呢。你知道今天吃什麼?」
「捲心菜。捲心菜燒豬肉和馬鈴薯,不過豬肉是不會有的。」
「當然是捲心菜囉!這個星期已經是第三次了!」
紹爾解開他褲子上的紐扣,開始小便。「一年以前,我小便起來還要弄成一個很大的弧形,」他愁眉苦臉地解釋着,「那是一種道地的軍隊派頭,大家都那麼做,我也覺着很好。每天挺進這麼多公里,滿以為不久就可以回家了。如今我像老百姓一樣小便,隨隨便便,也不覺得高興了。」
伊默曼把手伸到制服里面,舒舒服服地在搔癢。「怎麼樣小便我倒一點也不在乎——只要讓我再當老百姓就好了!」
「我也是一樣,可是看樣子我們得當一輩子兵了。」
「當然囉,當英雄當到死。只有黨衛隊員小便起來還弄成很大的弧形。」
紹爾扣好褲子上的紐扣。「他們當然能那樣做。我們幹著骯髒的活兒,可是那些寶貝卻得到了所有的榮譽。為了一座倒霉的城市,我們打了兩三個星期的仗,臨到最後一天,黨衛隊員來了,他們搶在我們頭里,意氣揚揚地開進了城。只要看一看他們得到的那種待遇!總是頂厚的衣服,頂好的靴子,頂大塊的肉!」
來源:華人頭條A來源:文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