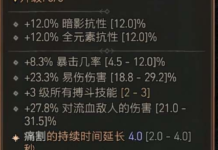如果要評選2021年最受矚目的新書,諾獎得主石黑一雄的小說《克拉拉與太陽》(Klara and the Sun)定會榜上有名。這是石黑一雄的第八部長篇小說,也是他繼201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最新出版的長篇小說。以不可靠敘事著稱的石黑一雄,這一次把一個可靠的太陽能機器人作為主角,據他本人敘述,這部小說原本會是寫給女兒的童話,但成品在溫暖之餘,又如同一個底色灰暗的現實寓言。石黑一雄在新書中完成了對「記憶、時間與自我欺騙」的又一次追問。如詹姆斯·伍德所說,他可能是本世紀最接近納博科夫的一位作家。

一場存在主義危機
《克拉拉與太陽》發生在未來,質感卻很當下。基因編輯、人工智慧、教育差距,乃至書中世界彌漫的生活細節,處處都讓人感到,這是石黑一雄對此刻世界的又一次逼近。
那是一個真實而陌生的世界,一個文明人士禮貌而疏離、冷漠假借關懷之名彌散的世界,那里技術並沒有帶來更高的善,而是為人類世界提供了新的存在意義難題——當機器人可以取代大部分勞動力的工作,前者擁有比後者更高的理解力、洞察力,甚至善良,人類的獨特該如何彰顯?我們的克拉拉就誕生在這個世界。
一如《遠山淡影》《莫失莫忘》所做的,石黑一雄繼續在書中使用障眼法。他看起來變仁慈了,變得更加敦睦懷柔,對人物充滿善意,但是真的如此嗎?
在我們艱難跋涉過石黑典型的纏擾瑣碎句式,撥開一層層敘述迷霧時,熟悉石黑的讀者會發現:嘿,這個暗地里使壞的嬉皮士還在這里!那個熟悉的石黑一雄又出現在眼前。他用淺白、粗糲句式和溫暖童話掩蓋的,是作家鍥而不舍描繪荒誕世界與現代性殘酷的野心。准確地說,荒誕在作家心中就是現實,《克拉拉與太陽》是關於現實的悲喜劇。
在小說中,太陽能機器人AF(人工朋友)克拉拉具有遠超人類的理解和學習能力,又是一個對人類無私奉獻的角色。最能夠證明這一點的,就是整部小說的高潮,當克拉拉朝夕相處的少女喬西身患重病,可能要離開人世時,喬西的母親請求克拉拉為了她而「延續喬西」,讓她相信自己的女兒依然活在這世上。她要克拉拉扮演喬西,成為一個喬西的替代品,而無私的克拉拉答應了。
克拉拉犧牲自己,去成為另一個人。到此我們看到雙重的自欺欺人——一份來自於喬西的母親,她已經失去了大女兒薩爾,不敢去面對二女兒喬西也離她而去的事實,所以她只能欺騙自己,讓自己相信克拉拉就是喬西,喬西還活在這個世界上。而另一份就來自於克拉拉,雖然她被設定為一個絕對誠實的機器人,但是使她無私地活在這世上,為此不惜犧牲自己的生活,這背後何嘗沒有自欺的成分。而籠罩在整部小說中更大的自欺欺人是機器人本身,人類渴望機器人像人一樣,卻要不允許他們反抗人類,這本身就是自欺欺人。或許正因如此,石黑一雄才那麼喜歡用機器人、複製人來做文章。
為了更深入地探索人的存在意義,石黑一雄在《克拉拉與太陽》中強調了信仰的力量。小說中,太陽是克拉拉的信仰,是她的能量來源,而書中喬西奇跡般的康復,實際上也跟太陽有關。藉助克拉拉與太陽的關系,石黑一雄探索了人與宗教、神靈之間的關系,甚至進一步說,在機器人的意義中,信仰究竟占據著怎樣的地位,這份信仰如果不是他自主選擇的,又是否存在著矛盾的一面?
不能將克拉拉與人類簡單等同,這仍然是人本位對世界的認知,克拉拉的無私、對太陽的信仰,都是建立在她是機器的基礎上,在我看來,如果說《莫失莫忘》寫的是人與複製人的相似,《克拉拉與太陽》更集中反映的其實是機器與人的不同,石黑一雄假設了這麼一種情況——一個機器比人更高尚的世界,當人類最推崇的價值反而被機器所實現,人的危機才真正浮出水面。
愛是人類與永恆孤獨周旋的方式
《克拉拉與太陽》想探討的不僅是機器人的存在問題,它也關乎人類世界本身,在一個技術發達、工具理性、人類卻依然被流行病和階層懸殊困擾的世界,人類本身的意義與倫理會否面臨新的考驗?我們會看到,即便無私的機器人出現,人類的社會已經如此發達和理性,技術帶給我們的卻不是更高的善,而是更加穩固的自私與殘酷。譬如小說中基因編輯拉大了階層的差距、喬西的父親被人工智慧「替代」而丟了工作,而克拉拉也終究會迎來被更新疊代的一天。技術讓人類更方便,卻也帶來了危機。
顯然,這種表述會讓人想起《莫失莫忘》(Never Let Me Go)。在那部小說里,石黑一雄講述了一個複製人的悲劇故事,藉以描繪出一個絕對理性社會的恐怖所在。小說就圍繞著三個複製人展開,凱西、湯米和露絲。他們是三角戀關系,凱西和露絲都喜歡男主角湯米。凱茜是小說的敘述者,她的身份是看護員,性格冷靜溫和。露絲是捐獻者,是典型的英國大妞。在小說中,看護負責照顧捐獻者,目的是縮短複製人每次捐獻器官的恢復時間,以便更快地進入下一次捐獻。而所謂捐獻者,而複製人的使命就是無償為他人提供健康器官,直到自己死亡。
石黑一雄像描寫平常人一樣描寫三個複製人,他們有夢想,有感情,有自己熱愛的生活,卻不能享受正常人所擁有的基本權利。他們為爭取人類最基本的尊嚴和權利而努力,可他們對抗命運的安排,卻最終以失敗告終。在《莫失莫忘》的翻拍日劇中,有一句話就呈現出了複製人在認清命運後的想法,電視劇里的複製人說:「這天,我明白了,我們是不能改變世界的。但是,若能相擁,這個世上除了你我之外的人就會消失。」整部小說並沒有遵循一般的套路,給複製人安排一個救贖的結局,凱西和湯米這些一度想要改變命運的複製人,最後等到的只是希望的破滅和不得不面對的捐獻。
有趣的是,《莫失莫忘》虛構了一所黑爾舍姆學校,黑爾舍姆的英文詞匯是Hail sham,其中,sham即可理解為虛偽、哄騙,也有復製品、贗品的意思。
石黑一雄揭示了現代社會的冷酷、謊言與人的意義困境,但並非毫不留情地嘲諷,如今的他更執著於尋找那些人性中依然珍貴的東西,那些能讓我們在虛無之海中牢牢抓住的繩索。在《克拉拉與太陽》里,他給出的是一個陳詞濫調但仍有其必要的回答,那就是愛,一種讓人類克服自身利己本質的存在,一種人類與永恆孤獨周旋的方式。
他相信,每個人總有什麼特別的東西,是其他人所無法取代,而這份特別不只是來自於人本身,還在於那些愛他的人心里,所以他借克拉拉之口說:「卡帕爾迪先生相信喬西的內心中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是無法延續的。他對母親說,他找啊找,可就是找不到那樣特別的東西。但如今我相信,他是找錯了地方。那里真有一樣非常特別的東西,但不是在喬西的心裏面,而是在那些愛她的人的心裏面。」(第385頁)
現代社會的根本難題,就是人愈來愈成為瑣碎的浮萍,人在混亂之中不再能牢牢把握生活、把握意義之網,缺乏信仰,缺乏整全的體驗,就連親密關系都難以獲取,於是不得不與永恆的孤獨共存,在無聊與虛無中與風車作戰。那麼在這個氛圍下,一個普通人如何找到自己的慰藉?人的意義如何得到補全?
在石黑一雄這里,是回歸信仰和愛。正如他在接受《新京報書評周刊》采訪時所說:「愛作為一個武器或者說盾牌,能幫助我們對抗孤獨和死亡。」
難以跨越的不是記憶,而是人與人心里的溝壑
石黑一雄總是擅長用最溫柔的話包裹最傷人的話語,在看似不緊不慢的敘述中切割人心,暴露我們脆弱而自欺欺人的一面。就像《被掩埋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中所說:「我們都認為自己與世界有某種可靠的關聯,這種感覺其實是虛幻的,是我們自己一廂情願。」從英國三部曲到《被掩埋的巨人》,他執著於處理記憶與遺忘的命題,可是記憶與遺忘,從不簡簡單單是「銘記歷史,抵抗遺忘」,而是小到普通人如何去承受記住痛苦的代價,大到民族、國家、世界,當千百年的歷史造就一道道恐怖的溝壑,不同民族與國家之間的記憶不只有甜蜜也有更深的對抗與仇恨,我們又該如何面對這些記憶的深淵?又是否真的有信心放下過去,說一句重頭開始?
有人說石黑一雄是在為遺忘提供合理的藉口,但無論是在《莫失莫忘》還是《被掩埋的巨人》,石黑一雄其實都在尊敬抵抗遺忘的人。
《莫失莫忘》里,凱西、湯米和露絲明知結果可能殘酷仍去找尋與複製人有關的真相;《被掩埋的巨人》里,一隻名叫魁瑞格的母龍噴出「遺忘之霧」,導致失憶症在英格蘭山谷中蔓延開來,為了趕在記憶清空前找回親人,主人公踏上尋找真相的旅程。無論是寫科幻還是寫古典,石黑一雄手持的利劍都指向當下。從911事件,到歐美對移民的成見,從地中海沿岸的難民潮,再到這兩年的新冠疫情,關於遺忘,其實我們已司空見慣。但更復雜的命題是,恐怕記住什麼,在每個人這里都是不一樣的,而每個人在接收信息和篩選記憶上的「選擇性」,使得當我們復述歷史時,實際上我們復述的也是自己的立場與觀念,於是歷史在觀念中不再一致,記憶也成了一個萬花筒似的東西,難以跨越的不是記憶,而是人與人心里的溝壑,是根深蒂固的立場與成見,於是當人們說以史為鑒,實際上同一件事情,不同人推導出的是不同的應對之策,而他們的策略很可能有天壤之別。
石黑一雄的小說里終究埋藏著一個戰爭的噩夢。他反復思考記憶與遺忘,繞不開的是二戰時日本戰敗、戰後自己移民英國、冷戰核武器威脅等事件對自己的影響。《被掩埋的巨人》里騎士維斯坦質問高文爵士,像是石黑一雄自己跳出來對讀者說話,他說:「我說的那些人走過了一條殘暴之路,親眼見過自己的孩子和親人殘肢斷臂、慘遭蹂躪。他們經歷了漫長的苦難,一路上死神就在身後……他們知道,他們終將面對自己的末日。他們知道,現在被抱在懷里的嬰兒,不久將成為血淋淋的玩具,在這鵝卵石上被踢來踢去。他們知道,因為他們已經見過,他們是從那兒逃出來的。他們見過敵人燒殺劫掠,見過已經受傷、即將死去的年輕女孩,慘遭敵人輪奸。」
當我們回到《克拉拉與太陽》這部小說,主流的聲音會說它是一部溫柔的童話,但一邊讀,我一邊感到這部小說充滿了殘酷。石黑一雄像是換了個手法重寫《莫失莫忘》,只是這一次加入了更多簡·奧斯汀、喬治·艾略特式的佐料,家庭戲仿佛再現十九世紀的英國莊園小說,機器人視角部分,就像是用第一人稱視角,來寫一個看似更溫暖的《莫失莫忘》,《莫失莫忘》的複製人跟人的性格很像,克拉拉則被設定成一個無私的機器人,一個完全利他,哪怕到了生命終點被人類所拋棄,還要用「我曾幫助過人類,我也是有價值的」這樣的話來安慰自己。可是這就存在悖論,如果是一個利他的、充滿大愛的機器人,她為什麼能對同胞的被遺棄無動於衷,又為什麼漠視了人類內部的自私、分化乃至對弱小者的欺凌。
小說中克拉拉的天賦是理解,她對人類世界充滿了共情能力。理解,換句話說是敏感,是對他人處境的細膩捕捉。人類中最敏感的人往往是最痛苦的,因為上天教會了她理解,卻不告訴她如何與痛苦共存。那麼,如果克拉拉是一個充滿理解力的人,如果她對人世間的自私、冷漠、殘酷有足夠的觀察,出自她口吻的陽光敘事就變得可疑,太陽所照射不到的地方才是小說的隱藏敘事。於是,重要的不再是克拉拉說了什麼,而是克拉拉沒說什麼。重要的不是童話,而是多個敘述者如何靠自欺欺人完成了童話。
在這個意義上,童話的構建也就成了文明史的構建,克拉拉書寫的殘酷在於它明明是一個工具人,一個本質意義上的被奴役者,卻用一種集體的、奉獻的精神來掩蓋她的痛苦,心甘情願地體認了這個被奴役乃至被犧牲的歷史。當無私的人成了殘酷的順從,自私反倒成了人類最後的勛章。當一切溫柔不再饋贈弱者,那麼這溫柔到頭來是更具欺騙性的殘酷。
很難說石黑一雄是在用批判的視角去寫克拉拉,作為幕後的創作者,石黑一雄在寫克拉拉時極盡溫柔與理解,而沒有居高臨下的說教和指責。對於克拉拉做出的那個她自以為正確的抉擇,石黑一雄這一次改變了《莫失莫忘》結尾殘酷而悲涼的敘事,而是充滿了金色太陽施洗大地般溫暖的光澤。然而,《克拉拉與太陽》里的溫暖,與《莫失莫忘》里的殘酷,殊途同歸都通向無可奈何。正如《克拉拉與太陽》中文版譯者宋僉在譯後記中所說:「當我們說到自我欺騙時,我們總是會將它與『逃避』、『怯懦』、『糊塗』等負面的詞匯聯想在一起,但事實上,自我欺騙是我們能夠面對這個殘酷的世界而不發瘋的一個重要理由,對於人類的生存就像空氣和水一樣不可或缺。自我欺騙的根源並非人心的虛妄,而是人心的脆弱;它是人心為自己築起的一道簡陋的緩沖,使我們不必迎頭承受現實的全力一擊,而是能夠假以時間,漸漸地接受現實。」
童話背後是文明史的殘酷
克拉拉意識到脆弱的共通性,所以她雖然感受到了人類的自私、怯懦、殘酷,卻選擇了理解,她高超的理解力使她不對他人作出輕易的批判,在這個意義上,克拉拉猶如是《了不起的蓋茨比》里尼克父親箴言的踐行者:「每當你要批評別人的時候,你要記住,這世上並不是個個都有你這樣的優越條件。」所不同的是,尼克父親是從一個優勢者的角度來做出道德的自省,而克拉拉的自省卻來自於自由意志的失去,因為無私是人類賦予她的,是她從誕生到這個世界時就被嚴格要求遵守的程序,人類將她設計成一個無私的機器人,賦予她強大的自省能力,但是這自省卻無法通向自由意志的覺醒,而只是讓克拉拉在為人類犧牲自己時,有一個自我慰藉的說辭。所以,克拉拉的自欺欺人既可以被理解,骨子里又充滿了殘酷。石黑一雄揭示出的是,或許殘酷才是人生的常態,那些善意的謊言、虛假的承諾,到頭來不過是掩飾我們內心的脆弱。
正如同石黑一雄針對《莫失莫忘》里複製人的命運發出的嗟嘆:「他們表現出一種殊死的勇氣,盡管他們看到,自己已用生命的一大部分時間來做徒勞的事,但他們仍然繼續做下去。我敬佩他們,他們可以了解自己。問題只是,生命消逝得太快了。」
就此而論,石黑一雄在重寫自己,重寫《莫失莫忘》等前作,但是採用了一種不那麼自己的敘事方式。這種嘗試從《被掩埋的巨人》《我輩孤雛》就開始了,相比起英國三部曲的嚴謹、精確,每一步敘事都像齒輪一樣咬合,現在的敘事更發散、混濁,更追求被敘事牽著走,而不是作者牢固掌控的敘事。但代價是石黑放棄了自己最擅長的寫法,不得不割捨他過去的寡淡、克制對白與深邃敘事內核結合所形成的強大張力。於是《克拉拉與太陽》成了一次冒險,石黑一雄選擇自己寫過的題材,但挑戰了不一樣的敘事風格。正因如此,整部小說的敘事比它的故事本身更值得琢磨。
石黑一雄多年關心移民問題和時代的價值分裂,在諾獎演講中,他呼籲在價值日益分裂的時代,文學必須學會聆聽,拓寬自己的邊界。由於從小經歷戰後日本的滿目瘡痍和移民英國的適應問題,石黑一雄對移民和少數族裔的焦慮感同身受,他擔心膨脹的民族主義情緒會加劇大眾對移民或少數族裔的歧視,更擔心一個強調工具理性的世界會走向極端的殘酷。
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中指出:「大屠殺不只是猶太人歷史上的一個悲慘事件,也並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為,而是現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學的理性計算精神,技術的道德中立地位,社會管理的工程化趨勢,正是現代性的這些本質要素,使得像大屠殺這樣滅絕人性的慘劇成為設計者、執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會集體行動。」所以,在《莫失莫忘》和這部《克拉拉與太陽》中,石黑一雄才會反復書寫一個高度理性計算的世界可能導致的後果,在那些溫情脈脈的話語背後,是現代性的殘酷再度露出它兇狠的獠牙,不反思這一點,我們對悲劇的懺悔就不再有效,而只是一次又一次的自欺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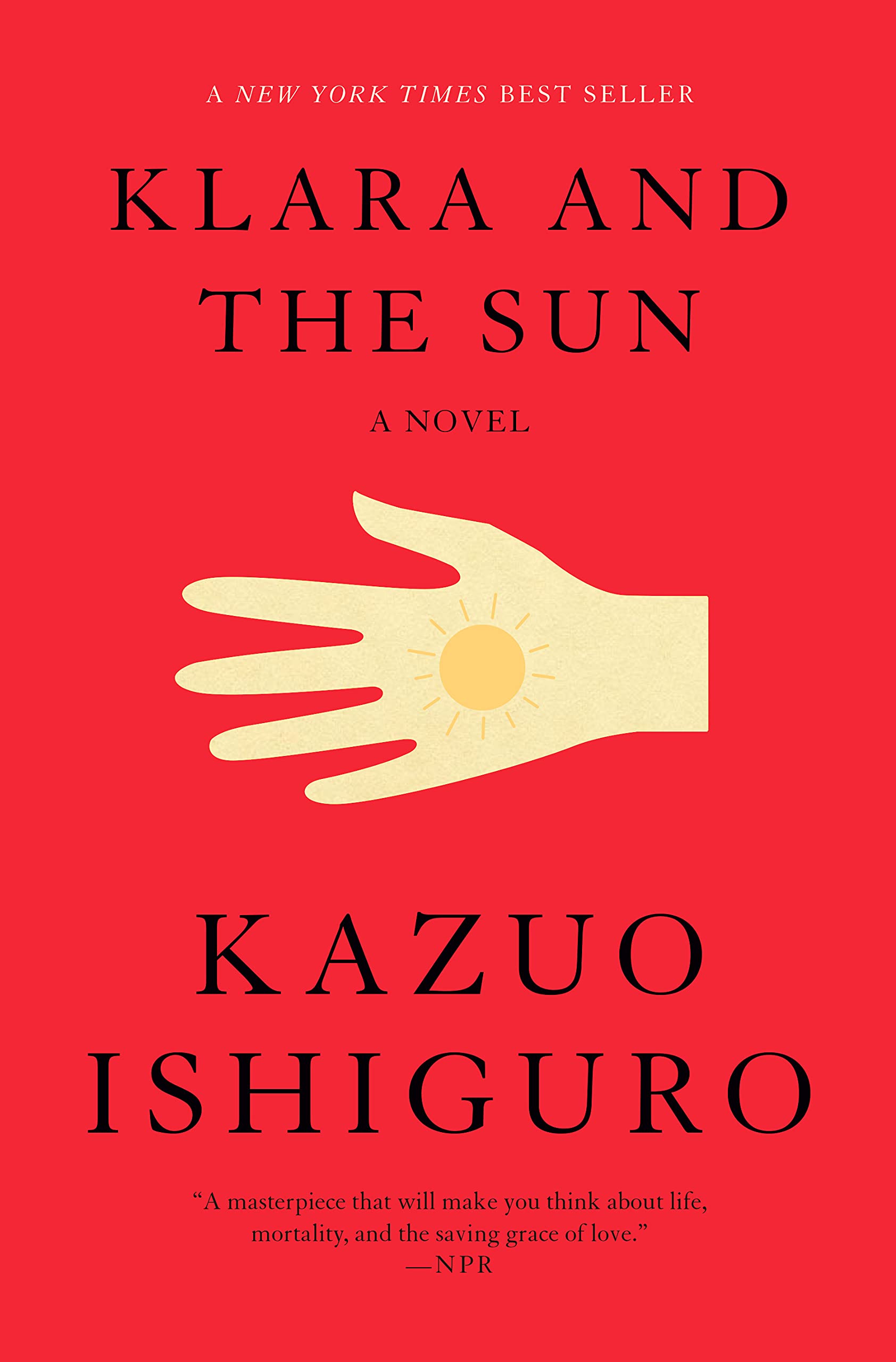
來源:機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