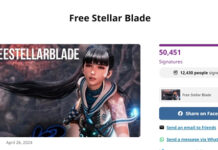到了凌晨兩三點之後,這座城市就和死了一樣,路上不見一輛車,不見一個人。我從公司走出來,只感覺脖子都快累斷了,以至於在走路回家的路上,我必須像個牙疼病人一樣雙手捧著下巴。
這麼走路有個壞處,就是只能看天,看不見路面。我經過市中心的公園時就被路牙絆了一個趔趄,走到中山二路的十字路口時又被一輛單車的地鎖勾住了鞋尖,總之這一路走得我很不好受。
但這麼走路也給了我全新的視野,這就是為什麼我能看見那個抱在路燈杆子上的女人。
女人穿著白色的襯衫和藍色的運動褲,正像個考拉一樣,雙手雙腳都死死抱著路燈杆子。等到力氣上來了,她就向上挪一截,然後繼續喘氣,休息夠了就再挪一截。我不是個運動達人,但我也明白一般人不會這麼爬杆子,由此可見這個女人的運動神經不太發達。
看到她的那一刻,我就站在了原地,像身處升旗儀式一樣朝她行著注目禮。倒不是我覺得這一幕很莊嚴,而是我擔心她是個女鬼,等我朝她露出後脖子,她就要撲過來吸我的精血。
看久了之後,我的脖子開始疼了起來,讓我忍不住「哎呦」地叫喚了一聲。女人聽到這聲「哎呦」,立馬扭過頭來看著我,她的頭發正披在臉上,眼睛透過發絲冷冷地看著我。可沒看多久,她就把頭扭了回去,繼續奮力向上爬。
過了得有十來分鍾,女人才終於爬到了路燈頂上。她跨坐在路燈上,累得氣喘吁吁,我看得脖子生疼,也和她一起喘氣。兩個人就這麼又喘了好久,她才終於開口說話:「你……你看……看什麼看?」
至此我才終於確認,這女人不是個女鬼,是個運動神經不發達的活人。
「你……看什麼看?走你的……路去。」女人看上去不太高興。
「我說,你爬到那上面去幹什麼?」我問道。
「關你什麼事?別來煩我!」
說著,女人從腰間掏出了一捆塑料繩,開始在路燈上打起結來。我這時才明白,她這是要在路燈上上吊。
「誒,你這——」
「你什麼你?說了不要看你還看!老娘要做什麼關你屁事!」見到我似乎還想說些什麼,她又吼了起來:「滾蛋!現在就滾!滾回家去!」
我被她罵得有些發怵,心想別人要死也不關我事,於是我把頭偏開,繼續朝家的方向走去。可還沒走幾步,我身後忽然傳來女人的驚呼聲,我回頭一看,發現她的那捆塑料繩一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女人和我都愣了一會兒,接著她一轉剛剛凶神惡煞的模樣,客氣地對我懇求道:「你先別走,行行好,幫我撿一下繩子吧。」
看著女人愁眉苦臉的模樣,我嘆了口氣,走到路燈下幫她把繩子撿了起來。
「好,你把繩子揉成球丟給我,我在上面接著。」女人俯下身,盡全力朝我伸出了手。
「那不成,」我一隻手抓著繩子,另一隻手扶著腦袋,朝她搖了搖頭,「我這要把繩子給你,我不就成幫凶了嗎?」
「誰看見了?咱們周圍一沒人,二沒攝像頭,你怕什麼?」女人指了指周圍空無一人的街道。
「我,我看見了,」我指了指我自己,「你這要是死了,變成鬼纏著我怎麼辦?」
「我發誓,我變了鬼絕對不纏著你。」
「那也不成,我今天要是幫了你,我這輩子都得睡不好覺。」
「唉……」女人一臉無奈,「那你把繩子放在原地,我自己下去拿。」
「那也不行,這繩子在我手上,我現在無論做什麼都會和你有關了。」
「那你想怎麼樣?你拿著那繩子有什麼用,玩跳繩嗎?你這人怎麼這麼麻煩!」女人開始不耐煩起來。
「你就不能……你先……你跟我說說,你為什麼非得自殺不可。」我想把她勸下來,可話到了嘴邊我卻打起了結巴。
聽到這個問題,女人立馬來氣了,她指著不遠處的一棟公寓樓,問我:「你看到那個還亮著燈的窗口了嗎?」
我轉過身,看見公寓樓的五樓的一個房間亮著黃色的燈光,窗戶後面有兩個模糊的人影。
「我男朋友,現在就在那里,和外面的野女人亂搞!我們倆在一起五年了,我給他做飯洗衣服,陪他看病,陪他考研,他就這麼報答我!」
說著,女人的眼圈紅了起來,她轉過頭去擦了擦眼睛,似乎不想在我這個陌生人面前哭出來。
「那你也沒……沒必要求死嘛,就一個男人而已,爛了就爛了,那什麼……天底下的好男人多了去了,你要想開點啊。」
「你以為這些話別人沒跟我說過嗎?你這些話我都聽爛了!總之我今天就是要死,誰都攔不住!」
「不是……你別這麼沖動,等你以後就會知道,這些都沒什麼大不了的,你再堅持一會兒,想開了就好了。不就是失戀嘛,沒必要跟這兒要死要活的。」
「你算什麼東西!事情沒發生在你身上,你憑什麼在這兒說三道四?!」女人忽然將氣撒在了我身上,「你他媽就是個路人,聽我說了兩句話而已,你覺得你自己很了不起是嗎?!」
「我也不是……你搞錯我意思了……」
「我沒搞錯,我明白你什麼意思!你不就是覺得自己很偉大嗎?啊?以為自己很厲害,靠張嘴皮子就能救人,覺得自己功德無量是吧!把自己當聖人了是吧!我告訴你,你連屁都不是!你要麼把繩子給我,要麼趕緊滾蛋!別讓我再看見你那張臭臉!」
我被女人罵得頭皮發麻,氣血也跟著涌了上來。我將繩子揉成球,狠狠丟到她懷里,對她大罵道:「他媽的!你要死趕緊死!」
說完,我便氣沖沖地繼續朝家的方向大步走去。可剛走出十幾米遠,女人又朝我喊道:「你回來!」
「你他媽還沒罵夠是吧,老子才不受你的氣!」我黑著臉回過頭去,卻看見女人此時滿臉是淚,連眼妝都哭花了。
「你回來!」女人又喊了一遍。
見她這副模樣,我只好再次來到路燈下,一語不發地抬頭看著她。
「你是我死前見到的最後一個人了,我不想在死前做的最後一件事就是吵架。」女人哭喪著臉說道。
「唉……」我又嘆了口氣,「那你想怎麼樣?」
「你跟我說說話吧……說什麼都好。」
我見她這副模樣,心里的氣也消了大半。於是我坐在路燈下,把外套脫下來圍在脖子上作為支撐,然後坐在了路燈旁的人行道上。
「我說,你為什麼非得吊死在這路燈上?」
女人抹了抹眼淚,對我說:「我那男朋友每天四點鍾都會出門跑步,我要他今天一早出來就看見我的屍體掛在路燈上,我要把他嚇得再也硬不起來,沒辦法出去亂搞,而且我做鬼都不放過他!」
「你想讓他再也硬不起來,偷偷給他下點藥不就行了嗎?何必把自己搭進去呢?」
「我不知道……我覺得我自己也有錯,要是……要是我平時對他好一點,他也許就不會出去找別的女人了……」
「你不是說你給他洗衣服做飯,還陪他看病什麼的嗎?這還不夠好?」
「還可以更好。」女人說這話時看上去很認真。
「那要按你這麼說,有人得糖尿病死了,那大白兔奶糖也有錯?有人吃方便麵撐死了,康師傅也有錯?」
「那也不能這麼說……」
「那為什麼到了你這里就可以這麼說?」
女人沉默了一會兒,似乎不知道怎麼反駁,接著她說:「問題不在這里,我覺得我已經活到頭了,再活下去也沒意思。」
「你還有好多東西沒見識過呢,你不去試一試怎麼知道沒意思?」
「我連去試一試的心思都死掉了,怎麼可能還會覺得有意思?」女人搖了搖頭,眼睛里的光似乎都黯淡了下來。
「你想想啊,你還有父母,還有朋友,就算是為了他們你也得活下去啊。」
「我為什麼非得為了別人活下去?」
「那你之前是為了什麼而活著的?」我反問道。
「為了那個狗東西,」女人又指了指那個亮燈的窗口,「我告訴你,如果你這輩子都是為了別人而活著,那你的下場不會比我好到哪去。別人是靠不住的,你只能靠自己,只為自己而活著。」
「那就為了自己活著啊,你這不是有個目標了嗎?」
「是啊,」女人苦著臉笑了笑,「這不就是活到頭了嗎?你要是一直為別人活著,等這個人靠不住了,你就會找下一個,就這麼活到老死病死。跟個乞丐一樣,這個地方討不到錢了,就卷鋪蓋到另一個地方討錢,我不願意這麼活著。」
「那照你這麼說,我就是那個乞丐了。」聽完她的話,我不知為何,覺得心里難受得緊。
「你有想過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嗎?」
「不知道,沒認真想過,」我搖了搖頭,「不過我想過自己該怎麼死。」
「噢?你說說。」女人忽然來了興趣。
「兩年前,我一天晚上突然肚子特別疼,疼得我死去活來,我同租的朋友打了120,把我送去了醫院。一路上,我覺得自己肯定是胃癌,要不就是其他什麼絕症之類的,總之肯定活不長。那時候我就想著,我要在野外找個風景好的山崖,在上面燒一桶熱水,把手腕割開泡在里面,一邊看日落,一邊睡死過去。」
「挺美好。」女人點了點頭。
「可到了醫院,一通檢查之後,醫生告訴我是闌尾炎,然後把我拉進手術室打開肚子一刀就完事了。我那時候還挺失望,因為自己死不成了。」我揉了揉脖子,抬頭看向她,「你剛剛問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說實話,這就是我想要的。」
女人長嘆一口氣,說:「我這輩子花了20多年為了別人活著,為了別人上班賺錢,為了別人吃飯睡覺,活得人不人鬼不鬼,一面牆撞不穿又換一面牆繼續撞。活到現在,我學到的道理就是做人必須為了自己活著,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只有這樣才有出路。」
說著,她扯了扯手中的繩子。
「這就是出路。」
我坐在路燈下,看著她認真地在路燈上一圈又一圈地打結。在她的背後,是這座城市的不見星月的夜空,地面的霓虹燈發射出紅光,將原本漆黑的夜色染成了隱約的朱紅色,仿佛夕陽在傍晚時分降落到了地面上,繼續散發著余暉。遠處順著街道吹來了微涼的夜風,夾雜著一股淡淡的汽油味和柏油味。世界像是暫時睡死了過去,四周的寂靜逐漸向我們逼近,讓我有些喘不上氣。
「好了。」女人將繩圈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我抬頭看向她,發現她留出了一截特別長的繩子用來吊住自己,於是我問她:「你是不是搞錯了?」
「哪里搞錯了?」
「你繩子留得太長了,這樣子你一跳下來,繩子會直接把你脖子拉斷,有點像我現在這樣。」我指了指自己被外套包裹的脖子,做了個掰斷的動作,「我看過電視,你這不叫上吊,叫絞刑,死相沒有上吊那麼嚇人。」
「明白了。」女人點點頭,將繩子又在路燈上纏了好幾圈。
我站起身,問她:「你是想我走,還是留在這兒?」
「你別走,咱倆聊了這麼久,也算一份交情了,你送我一程吧。到時候我變成鬼了,就去給你幫忙,以後要是有誰找你麻煩,我就去把他害死。」女人認真地說道。
「行。」我笑了笑,「那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遺言之類的。」
女人坐在路燈上想了想,對我說:「晚安。」
「晚安。」我朝她點點頭。
她笨拙地在路燈上翻了下去,雙手抓著路燈的橫梁,像是准備做引體向上。接著她用力一閉眼,松開手,整個人就這麼吊在了半空中。她的手一會兒抓住脖子,一會兒又松開在空中胡亂揮舞,她的雙腳也一並不停亂踢,似乎在絕望地尋找一個落腳點。
我看著她瀕死的模樣,只覺得肚子里的腸胃都糾纏在了一起。忽然,她低頭看向我,嘶啞地朝我喊道:「繩子……繩子沒有……幫幫我……抓住……腳……」
我仔細一看,才發現她的活結打得太緊,以至於沒有勒緊她的脖子,讓她痛苦不堪,卻又能勉強呼吸。我猶豫了一會兒,然後一咬牙,奮力爬上路燈杆子,爬到與她的腳齊平的位置,然後縱身一躍,抓住了她的雙腳,與她一並懸在空中。
我們二人的體重終於拉緊了繩子,她的那模糊的呼喊聲戛然而止。我抓著她的腳踝,感受她的掙扎正隨著時間流逝而變得逐漸微弱,到後來只剩下一些斷斷續續的抽搐。我喘著粗氣,渾身止不住地打起戰來,這種死亡的節奏仿佛通過她的腳踝流到了我的身體里,讓我恐懼不已,後背滲出了一大片冷汗。
就在這時,我突然聽見頭頂傳來一聲斷裂的脆響,緊接著我們二人重重地跌在了地面上。她的膝蓋剛好頂住了我的胸口,強烈的沖擊讓我發出一聲悶哼,好像被人揍了一記重拳。我的眼前天旋地轉,肺葉不受控制地抽搐起來,我爬起身來,不停喘氣,過了好久才緩過勁來。
我轉過頭,發現她此時正躺在地上,一邊劇烈地咳嗽,一邊大哭起來。我連忙將她抱起來擁在懷里,她像個找到了救生圈的溺水者一般,緊緊抱著我的腰間,淚水如春雨般落下,沾濕了我的肩頭。她那清亮的哭喊聲在夜晚的街道間迴旋,聽上去干淨又絕望。我感受她在我懷里不停顫抖,宛如一個新生兒。
過了很久,天色開始微微亮了起來,我聽見從遠處傳來了人們的談話聲和汽車的發動聲。一切似乎逐漸活了過來,血液再次湧入了城市的血管里。我拍了拍她的後背,問她:「咱們現在要怎麼辦?」
她沒有回應,腦袋仍靠在我的肩上,她的身體隨著緩慢有力的呼吸,如海浪般起伏著,似乎已經陷入了熟睡。
來源:機核